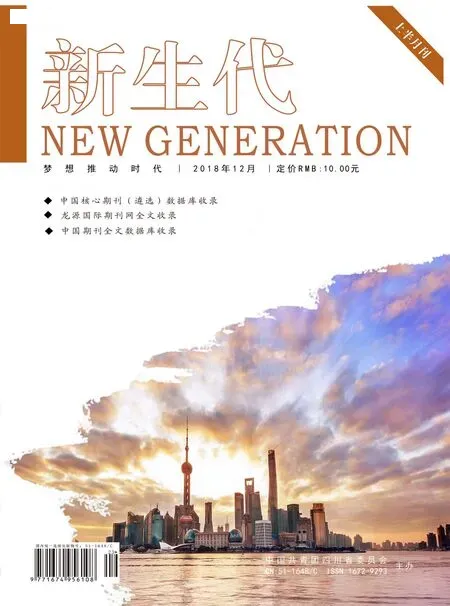瑪麗女王時期的英格蘭宗教改革
徐國珍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陜西西安 710119
一、瑪麗女王的改革措施
瑪麗在倫敦市民的歡呼聲中加冕為王,人民對她的擁戴更多出于她是都鐸正統,并不是她的天主教信仰。英格蘭人重視王位的合理繼承,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期待重新回到羅馬教宗的統治下。瑪麗錯以為人們對她的愛戴是出于對天主教的懷念,實際上,部分民眾不反對瑪麗將教會恢復到亨利八世統治初年的狀況。但現在英格蘭教會獨立于羅馬教廷已成既定事實,人們對外來的新教已經不再那么排斥,甚至還在慢慢接受。莫爾帕觀察到,此時的英格蘭人們不是狂熱的新教徒,但也絕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究瑪麗一朝,樞密院向議會遞交的所有法案都遭遇了很大阻力,尤其是涉及到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來的法律法規。1553年10月,瑪麗召開議會,她授意樞密院向議會遞交關于廢除1532年以來的所有《叛逆法》的議案,這正是為恢復天主教正統信仰和羅馬教皇權威做準備。議案在上院沒有受到很大的壓力,但在下院遭遇到強烈地抵抗。在瑪麗寫給教皇的信中說到:“下院尤其不愿意聽到任何關于廢除國王最高權威的法令的法律,他們懷疑這將把教皇權引入到這個國家,這正是他們害怕的。”下院議員擔心這項法律將會危及他們自亨利八世以來得到了教會財產。在女王的干涉下,議案最后被通過,女王不否認她的旨意在下院受到巨大阻力。大法官加納德說:表決結果是350人同意,80人反對。但實際上,反對的人數可能要遠遠超過這些。總的說來,下議院在關于廢除新教教義上并沒有進行有力抵抗。
1554年3月,第二屆議會召開。鑒于在上次議會中的失敗,瑪麗在上議院中加封6名主教以加強政府在議會中的力量。但不同于上屆議會,這次的反對聲音來自上院。他們反對通過大法官加德納遞交的關于懲處異端、王夫——菲利普在英國的權力以及恢復教會獨立司法權的議案。較于上院,下院態度溫和,尤其是在女王暗示下院恢復達勒姆教區并不會影響到現有的土地財產狀況后,下院欣然以201對120向女王妥協了。
同年11月,教皇任命波爾為教皇使節回到英格蘭談判,恢復羅馬教廷在英國的財產和權威。下議院拒絕無條件承認波爾,他們要求教皇承認自1532年之后教會財產沒收和流轉的合法性,此外應還赦免在財產流轉中的道德罪責。英格蘭宗教會議提議女王和波爾接受此項議案,他們清楚如果堅持恢復教產,不但會招來鄉紳貴族的堅決反對,而且會危及女王陛下的統治秩序。波爾帶來了教皇特許狀,議會撤消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時期頒布的關于反對教皇權威和教皇口令進入英國的法案。11月,英格蘭教會在波爾的帶領下同羅馬教廷和解,波爾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教皇在英格蘭教會中的獨尊地位再次被確立。這屆議會對瑪麗來說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議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她在教產問題上的小心謹慎。過去政府控制的書報審查權現在被重新移交給天主教會,懲治異教徒的法令被恢復,被破壞的雕塑、繡像等又到處出現。在此之后,女王動用她私人財產恢復了4座修道院,并開始迫害新教徒。
1555年,由教皇和主教波爾提議建立的特別宗教法庭成立。宗教法庭由邦納滕斯托爾、加納德等6名高級教士組成負責審訊新教徒和持不用政見者。根據敕令,英國境內的新教教徒將會面臨著或放棄新教信仰、或流放、或關押或處死的處境。上層非教會人士在不觸動他們財產的前提下準備隨時信奉任何宗教,因此免于迫害。盡管社會上層同議員們不反對適當的宗教迫害,但是瑪麗狂熱的血腥鎮壓讓他們時刻憂慮異端法庭將要再次回到英國,而此時,人們對臭名昭著的佛蘭德爾宗教法庭還記憶猶新。
1558年11月,瑪麗女王駕崩,幾小時后主教波爾也相繼去世。英格蘭人并不為此悲傷,他們把它看做一樁小事。而英國直到瑪麗去世前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天主教國家,天主教信仰也沒有在民眾中完全恢復到亨利八世時期的狀況。
二、教產流轉對瑪麗復興天主教的致命打擊
如果說從行政命令著手的宗教改革還停留在表面的話,那國王沒收教產和教產的流轉迫使天主教走上不可挽回的衰敗之路。解散修道院在英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同確立王權至尊一樣。解散修道院被視為同羅馬天主教決裂的必要行動,但實際上這是出于對教會財富的覬覦:國王需要錢,貴族需要土地。宗教改革給都鐸君主劫掠教會和修道院提供了重要契機。國王從教會和修道院獲得了2類收入:一是靈性領域的稅收(Spiritual Revenue),二是沒收修道院土地和財富。靈性稅收主要包括教士首年薪俸和什一稅,先前由英國天主教會上交羅馬教廷,但1533年議會通過法令要求所有教士停止向羅馬教廷交納這筆款子。1534年議會下令,教士首年薪俸和什一稅都轉交給國王,為此設立“首年薪俸額什一稅法庭”。1535到1540年,該法庭獲得14.6萬英鎊。直到瑪麗女王時期為重振教會經濟,君主主動放棄征收教士首年薪俸和什一稅。1555年議會法令宣布,新任教職者不必向政府交納首年薪俸,什一稅交給各教區主教用于教區建設。
英格蘭教會在經過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的一再掠奪之后風光不再,窘困的經濟狀況和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率使得瑪麗女王時期的天主教復興尤為艱難。瑪麗即位后不久就著手全面恢復天主教會。瑪麗要求全面恢復天主教會引起議會的警覺,議會要求只有在教皇赦免世俗教產持有者的道德罪責后,他們才能接受波爾入境。瑪麗從中調節,教皇無奈只能接受議員的要求。1555年冬至1556年,波爾組織由律師和主教組成的智囊團,并構想一個全面恢復天主教會的方案,其中包括宗教法律、教儀、重建天主教鄉村傳教信息網以及培訓天主教士。
波爾計劃將教會恢復到亨利八世初年的狀況,但此時教會一貧如洗,波爾的計劃幾乎寸步難行,恢復教產成為復興天主教會的當務之急。女王在下議院一再受挫讓他意識到復興天主教會只能建立在同現有教產持有人的良好溝通上,但波爾并不擅長同這些教產持有人打交道。波爾在1553和1554年兩次重復,教產持有者若是想要免除教產流轉中的道德罪責,首先要做的就是上繳教產,而教產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產。教皇清楚索回20年前流轉出去的金銀器皿等教會裝飾品希望不大且不具有重要意義,他明白只有在英格蘭恢復教會地產莊園才能真正在英國重建天主教權威。波爾允許俗人將手中的教產出售,但他要求出售的教產只能由沒收前的教區教會接受。教皇對英格蘭現狀不甚了解,他授權波爾做“一切正確且必要的事”。波爾入境后赦免了教會土地和教會其余財產持有者的罪責。由此,教皇失去對教會土地的持有權,土地被緊握在世俗地主手中。波爾不得不接受原本被用來復興天主教會的地產再一次回到世俗地主手中,盡管他們一再表明地產在他們手中是安全的。波爾和議會之間相互詰難,他譴責議員以接受他的入境換取教皇對教產流轉的罪責是一場交易行為,他們歸順天主教會而非出于虔誠的信仰。
波爾從世俗地主那里取回教會地產的希望破滅,他只能寄希望于同他一樣信仰堅定的瑪麗女王。波爾希望女王將由王室收取的宗教稅收轉交給教會。這對瑪麗來說,這不只是贊助教會一筆錢的問題,其中涉及到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時期的宗教政令,她的行動需要經過議會的商討。波爾希望女王將教士首年薪俸和什一稅立即交還給教會,但波爾只考慮到教會窘迫的經濟狀況而忽視瑪麗同樣面臨財政困境。瑪麗政府自愛德華六世去世后,從地方教區收取的靈性稅收一直是少之又少。在都鐸王朝前期開始的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使得大量主教負債累累,其中有18位主教還欠著本應在1552年圣誕節前上繳的928英鎊。瑪麗寬大地處理了這些教士,并延長繳稅期限,主教塞爾比和霍普頓的繳稅年限被延長至5年,主教塞爾比的債務后來被女王免除。教士首年薪俸在波爾同議會商量后,仍然上繳給女王。
很顯然,瑪麗統治期間的任何旨在將君主權力移交羅馬教庭的法令都經過了漫長的商討。波爾在認識到從中央發布的政令在地方上的作用有限,要想徹底恢復教產只能先收集教產的現有資料。愛德華時期多數教士為在解散小教堂過程中多獲得幾份年金對多份檔案資料造假,收集和鑒別檔案資料的漫長過程持續消耗波爾大量時間、精力。瑪麗期望教會能在短期內有較快發展,她決定將教會稅收交還給天主教,下令恢復修道院。然而諷刺的是,女王對教會的慷慨解囊還是建立在出售教產和出租修道院地產的基礎上,她并沒有考慮到教會的長遠發展。女王的自我犧牲并沒有如她期盼的那樣引起世俗人士的附和,多數鄉紳依然緊緊攢住自己的地產。
三、改革時期的教士群體
教會稅收征收范圍的擴大和固定化都嚴重削弱了教士的整體經濟實力,宗教改革后期教士們負債累累。許多教士不能獨立依靠教士圣俸維持體面的生活,更有大量教士依靠家族補貼才能維持生活開支。瑪麗時期,教士在經濟上的困境使得他們在復興天主教問題上一直縮手縮腳,進程緩慢。經濟地位的削弱使得教職不再具有過去的榮光和吸引力,甚至人們開始認為只有紳士出身才能維持體面的教職生活。改革期間的教職任命權被掌握在國王手中,國王可以占有空缺的教職薪俸,同時一旦修道院和主教職位出現空缺,其領地收入也要歸君主所有。都鐸王朝的君主經常拖延教職空缺時間來增加收入。
宗教改革的曲折發展使得教士結婚合法化問題一直沒有定論。盡管亨利已經同羅馬決裂,但他在教士獨身問題上的保守立場仍十分堅定。1535年,王室發布公告:譴責教士結婚并威脅要剝奪已婚教士的圣俸。1536年各主教區主教奉命調查轄區內的教士結婚情況,對已婚者予以逮捕或送交樞密院。亨利八世時期長期對教士結婚的敵視和反對最終明確化,最后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亨利去世。瑪麗時期艾克賽特因結婚被剝奪圣俸的教士超過四分之一。愛德華六世在簽署《四十二條信綱》后的不到一個月內去世,瑪麗女王即位后再次討論教士結婚和已婚教士的問題。1553年10月,議會廢除愛德華時期制定的所有法案,禁止教士結婚,已婚教士或被剝奪圣俸或被開除教籍,此外被要求無條件離婚。政府開除了2000名違背獨身制的教士,其數目相當于國家教職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1554年,桑威治所有的教區牧師和牧師助理都已經結婚,最后沒有教士可以主持宗教儀式。盡管這種例子很少見,但剝奪教職、對教士進行審訊以及讓教士在教徒面前公開懺悔都給民眾帶來了心理上的混亂。大量教職空缺、缺少足夠的教士在各教區鄉村中布道,使得天主教復興只能依靠政令。
四、來自地方的反對
盡管瑪麗的繼位歸于她是都鐸血統和民心所向,但是她在婚姻一事上犯了錯誤。她否決議會提議的兩個英格蘭貴族青年而請求與菲利普締結婚約遭到大部分議員的抗議。瑪麗與西班牙的聯姻違反了當時英國在外交上雖未成定法但是已被默認為外交原則的規定,即商業上最危險的敵人也一定會是政治上的主要敵人。下院議員擔心女王與西班牙締結婚約不僅會使英國徹底回歸天主教世界,而且英國將會有喪失獨立的危險。盡管大法官加德納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也極力反對這次聯姻,他擔心與西班牙締結婚約將會使得英國步入蘇格蘭的后塵。百姓也深知其中利害,懷亞特爵士領兵起義。懷亞特絕口不提他的新教信仰,他們高呼“不要讓英國淪為西班牙的附庸”,他們請求女王同考特尼家族聯姻。次年1月,約600位倫敦居民加入起義隊伍,他們高喊“我們都是英國人”。面對來勢洶洶的起義軍,瑪麗充分展示了她作為君主的才能。瑪麗前往倫敦市政廳發表演說,她請求民眾對她保持忠誠。瑪麗完美的演講同懷亞特因不愿洗劫倫敦而延遲行動使得形勢大變;此外,懷亞特的部下沒能夠在米德蘭、德文和希爾佛德郡成功起義呼應他。臨時組建的皇家軍隊擊垮了不斷減員的起義軍,起義最終失敗。瑪麗將約100名起義者處以極刑,其中包括簡·格雷。
1555年后,瑪麗著手全面復興天主教。議會通過的諸項法令并不意味著天主教在英格蘭徹底壓倒新教,一枝獨秀。許多人皈依天主教只是出于對法律條令的恐懼。在倫敦,天主教神父被嘲諷,宗教儀式也不受歡迎。僅僅頒布法令是遠遠不能使天主教恢復到生機勃勃的狀態。
人們對瑪麗一朝宗教改革的最主要印象停留在殘酷的宗教迫害上。1555年,由教皇和主教波爾提議建立的特別宗教法庭成立。宗教法庭由邦納滕斯托爾、加納德等6名高級教士組成負責審訊那些新教徒和持不用政見者。根據敕令,英國境內的新教教徒將會面臨著或放棄新教信仰、或流放、或關押或處死的處境。在瑪麗一朝的宗教迫害中首當其沖的是在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時期出名的新教主教,其后是一些工匠和農民。被燒死的人大約有273人,這些人中除了21位著名的新教領袖,其余大部分是隨意挑選的,其中還有50多名是可憐的寡婦。這些數據也許被放大了,約翰·蓋伊認為:“懷有偏見的福克斯(John Fox)只要有可能,常常會將同樣的例子重復使用。”據莫爾帕統計,這些受難者中大多是加爾文派和再洗禮派,其中六分之五是倫敦人、東安格利亞人和肯特人。近800名新教徒逃亡大陸的法蘭克福和日內瓦等地,數以百計的新教徒逃亡法國。這些流亡者不僅激烈的反對天主教宣傳,此外還將其出版煽動性的刊物偷偷送回英格蘭,這些都使得瑪麗政府疲于應付。正是在此時,英國的流亡者和日內瓦加爾文派加深了接觸,這對伊麗莎白時期國教的建設產生重要影響。麥格拉斯認為在瑪麗采取的措施中,最不明智的就是1556年當眾燒死克默蘭( 克默蘭在臨刑前先將為瑪麗簽署過文件的右手伸進了火中,他明確地反對羅馬教皇和天主教,并堅定地信仰新教)。瑪麗的血腥鎮壓連神圣羅馬帝國駐英國大使李納德都覺得“太輕率、太野蠻”。他在回復西班牙國王的信中寫道:倫敦人們對于懲處異端所用的嚴苛的法律、殘酷的手段都表示不滿,觀看極刑的市民或哭泣或祈禱上帝給予這些“異教徒”以力量,他們甚至將火刑之后的“異教徒”的遺骨收集起來。一位西班牙的托缽僧當眾批判說:這些血腥的判決完全違背了基督溫和寬宏的精神。
懷亞特爵士的擔心被證實:英國被卷入西班牙與法國的戰爭,淪為了西班牙的附庸。英國在十年前還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獨立國家,但現在不僅成了教皇的臣屬,而且地位相當于西班牙的一個省份。英格蘭的呢絨出口貿易受到西班牙的打擊,教會也因卷入西班牙和羅馬教皇的爭端中備受控制。1558年1月7日,吉斯公爵再度占領加萊,國內輿論嘩然。加萊不僅是貿易港口具有商業價值,也是英國先王對法戰爭勝利的光榮象征。加萊的失守使得人們對于瑪麗抱怨連連,無數英國青年為他國利益殞命異鄉、巨額的財政開銷、反復無常的宗教改革和殘酷的宗教迫害使女王同波爾名譽掃地。瑪麗女王的內外政策給民眾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教會不獨立就意味著英國在內政外交上都將處處受限。正是由此,伊麗莎白繼位后,英國人對天主教不再那么懷念,他們迫切期盼一位真正的英國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