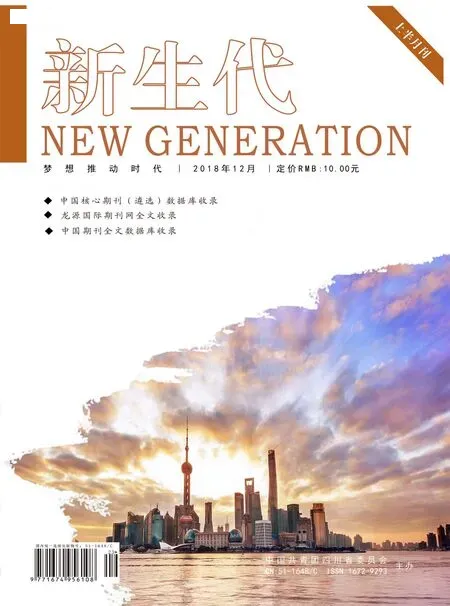《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的悲劇人生探析
吳捷
海南大學(xué) 海南海口 570228
張愛(ài)玲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吸收驚為天人,她是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才情最高的女作家之一。張氏性格當(dāng)中的敏感,冷漠構(gòu)筑了其部分消極的人生觀,世紀(jì)末的哀怨迷離,悲觀總是籠罩于其文本之中,她獨(dú)特的現(xiàn)代觀與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相交消融,描繪了新舊沖突,中西雜交的中國(guó)社會(huì)環(huán)境。人生無(wú)處不荒涼,盛大的狂歡之下如煙花轉(zhuǎn)瞬即逝的寂寞流轉(zhuǎn),多少情事糾紛的曖昧變幻,盡是人生荒涼的底色。在她冷峻的筆下,葛薇龍,這個(gè)原本天真無(wú)邪的少女,最后卻在物欲,愛(ài)與欲念編織的綴網(wǎng)之中逐步沉淪,失去了曾經(jīng)自由獨(dú)立的驕傲,淪落為邊緣化的“可憐人”。女性自身主體地位的淪喪,他者的同化過(guò)程的揭露,也因其冷峻的藝術(shù)描摹而更為真實(shí)深刻。
一、淪落為他者的可憐與可恨
《沉香屑·第一爐香》文本呈現(xiàn)了殖民都市環(huán)境里光怪陸離之亂象,香港,這個(gè)侵染了殖民文化,匯聚了各色群體階層的殖民都市,空氣中彌漫了一種日漸衰落的氣息,伴隨著這種糜爛而來(lái)的,是頹廢的世紀(jì)末文化,最后的貴族之氣行將淹沒(méi),也牽連了本不屬于那個(gè)階層的平常百姓。文本描寫(xiě)了一個(gè)原本天真無(wú)邪的少女在這個(gè)病態(tài)而頹糜的都市里遭受了靈魂的創(chuàng)傷而最終墮落,淪落為他者的悲劇過(guò)程。薇龍離開(kāi)上海,為了完成學(xué)業(yè),奔赴香港的姑母。這個(gè)姑母,平素里熱衷于舞際交際,周旋在所謂上流社會(huì)的奢華簇?fù)碇校翜S在自己的荒糜而物質(zhì)的世界自得其樂(lè)。在同意給予薇龍資助的同時(shí)也企圖將其拉攏入自己的荒淫的亂圈之流。她利用薇龍作為引誘年輕男子的籌碼,構(gòu)筑了充斥著物欲橫流的頹糜之氣的怪誕之圈,一步一步將這原本純真無(wú)邪的少女誘墮入這深坑之中。喬琪喬,風(fēng)流成性,聲名狼藉,這樣的一個(gè)花花公子,卻是薇龍的在劫難逃。侵染了香港這個(gè)衰敗頹糜的殖民都市的迷離多情,生于斯,長(zhǎng)于斯,卻對(duì)一切抱以玩樂(lè)的逢場(chǎng)作戲之態(tài),他出現(xiàn)在薇龍的身邊,戲耍了周遭一切后瀟灑離去,對(duì)于薇龍而言,這樣的出現(xiàn)似乎圓全了內(nèi)心對(duì)愛(ài)情的憧憬與欲戀,但喬琪喬畢竟不是同樣的“愛(ài)情至上”,他深刻明白這繁華奢靡的背后,終究是一場(chǎng)空洞的預(yù)演,所以即使他處處留情究其本質(zhì)也終是無(wú)情的浪子。薇龍面對(duì)著那“可怖”的姑母,那“多情”的喬琪喬,曾竭力讓自己保持清醒,力求潔身自好,但眼前這華美的物質(zhì)與可供念想的情欲之流的橫沖直撞,蒙蔽了原本純真的心靈,沉迷于愛(ài)與欲念編織的綴網(wǎng),遵從自身內(nèi)心的欲望與執(zhí)念鍥而不舍地尋求快樂(lè),避免失落與欲望受阻。只是,癡心錯(cuò)付,喬琪喬不過(guò)是個(gè)自私,玩弄感情的登徒浪子,薇龍?jiān)谶@段感情中逐步喪失了曾經(jīng)自由而獨(dú)立的驕傲,喪失了尊嚴(yán),淪落為邊緣化的“可憐人”。少女無(wú)論出于“自愿”的“渴求”意識(shí),抑或來(lái)自“被動(dòng)”的誘惑,都終究無(wú)法避免一步步沉淪,墮入這二者糾葛的深坑之中,失去了原始的純真,失去了自我。
二、女性主體意識(shí)的淪喪,男權(quán)制下的犧牲品
從古至今,女性總是被束縛于“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范疇中,所謂傳統(tǒng)文化的道德束縛與作為準(zhǔn)則的規(guī)范,這樣的秩序倫常,一味讓女性淪為男權(quán)制下的附庸品,女性被迫臣服于男性,臣服于社會(huì)與家庭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集體壓制必然會(huì)導(dǎo)致女性群體意識(shí)深處的焦慮與抑郁,當(dāng)缺失的欲望沒(méi)有辦法得到滿足,原始的瘋狂陷入對(duì)欲望的無(wú)邊追逐當(dāng)中,“飛蛾撲火”式的沉淪與悲劇必然無(wú)法避免,淪為他者的可憐與可恨也伴隨而來(lái)。
林幸謙在《女性主體的祭奠》中提到,“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中,傾向一再重寫(xiě)女性的壓抑自我作為反控訴的手段,以揭露宗法父權(quán)社會(huì)對(duì)女性的文化壓制”。傳統(tǒng)的女性群體,總是作為“他者”,存在于男權(quán)父權(quán)制內(nèi),是喪失了自身主體地位的邊緣化的“可憐人”。在漫長(zhǎng)的歷史洪流中,女性群體總是處于被消解,被隱匿與壓抑的缺席者,張愛(ài)玲的書(shū)寫(xiě)當(dāng)中,有女性自身不斷抗?fàn)幎罱K爆發(fā)于斯的宣泄之流,當(dāng)然也有抗?fàn)幍慕Y(jié)果最后以失敗告終的,淪為男權(quán)制下的犧牲品的“可憐人”。薇龍?jiān)?jīng)也擁有過(guò)驕傲與獨(dú)立的靈魂,可是這樣的驕傲在遇到喬琪喬之后頃刻瓦解,物欲與情欲的糾葛如同巨大的牢籠,此般幽深禁錮將薇龍的心靈與精神悉數(shù)架空,最后竟走向“自我毀滅”的悲涼如斯。被毀滅的身軀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訴求著那不為人知的憂郁與壓抑,主動(dòng)的“沉淪”,被迫的“異化”,最終無(wú)法避免地走向男權(quán)制下的犧牲軌道,與最初的驕傲,自由漸行漸遠(yuǎn)。林幸謙在《女性主體的祭奠》中提到,“張氏的書(shū)寫(xiě),即是女性荒涼的某種內(nèi)在困境”,如此,薇龍的“他者”處境實(shí)質(zhì)上也是自身的生存困惑,在女性主導(dǎo)意識(shí)層面需有所堅(jiān)持,還是一味迷戀在情與欲念的曖昧流轉(zhuǎn),生命的實(shí)質(zhì)意義到底在哪里,失去了愛(ài)情與物欲,人生終究向何方?薇龍的掙扎也是新舊時(shí)代女性群體的共向掙扎,不在沉默中爆發(fā),便只能走向荒涼頹糜的囫圇困境,在沉默中悲涼地“死”去了。
三、“飛蛾撲火”的悲劇人生
導(dǎo)致這個(gè)曾經(jīng)純真的少女走向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她受縛于“三綱五常”的道德范疇之中,她似乎將古時(shí)女子在家從夫的“愛(ài)”之觀深烙于心,將“愛(ài)”視為根本的生命本真的寄托與渴求,眷戀于心的,依然是無(wú)法逃脫的情與欲念的流轉(zhuǎn)。
在黑格爾的他者理論體系里,我們知道彼此雙方是相互搏斗的關(guān)系,在一場(chǎng)殊死的拼斗之中必然存在強(qiáng)者與弱者。強(qiáng)者勝出,成為了主人,弱者便變成了強(qiáng)者的“他者”。薇龍的“自我意識(shí)”里是存在抗?fàn)幍模魏芜@樣的抗?fàn)幵跓o(wú)形的巨大綴網(wǎng)中是如此蒼白無(wú)力,自身女性意識(shí)的覺(jué)醒,終究在與欲念的抗?fàn)幹行媸。殡S而來(lái)的,是淪喪為男權(quán)制下的犧牲品,最終淪落為邊緣化的悲情者。
愛(ài)情,從某種程度而言,的確是一種可以引導(dǎo)激發(fā)人們向美而生的力量,但對(duì)于依附于男權(quán)制中的女性而言,在情愛(ài)的欲念裹挾撞擊之下,在愛(ài)情這場(chǎng)游戲中喚醒的自我是作為“他者”的對(duì)立存在,作為情人與妻子的確立并非真正自立自主的本我,薇龍?jiān)谶@場(chǎng)游戲中被所謂的愛(ài)情激發(fā)的,實(shí)質(zhì)上是犧牲與奉獻(xiàn)自我多于肯定與完善本我。女子的生存價(jià)值倘若只能依附于男權(quán),依靠愛(ài)與欲念來(lái)引導(dǎo)和充實(shí),于所謂的愛(ài)情中尋求自身生命的本質(zhì)意義,那么通過(guò)依賴丈夫或者情人進(jìn)而確立自身價(jià)值意向看似是女子必然的歸宿,但這種選擇的隱性潛藏之下,確是女性最根本的悲劇實(shí)質(zhì)。從古至今,多少的女子陷入這場(chǎng)不計(jì)成本的負(fù)重中失去了自身,失去了所有,這一幕幕極具毀滅意義的悲劇深淵真實(shí)地觸目驚心。薇龍將內(nèi)心至高無(wú)上的愛(ài)情和靈與魂深刻撞擊的欲念快感視作人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標(biāo)之時(shí),她便將所有的熱情與希望付諸在心愛(ài)的喬琪喬身上,明知最終的結(jié)果不能真正遂心如意,明知對(duì)方是一個(gè)花心越軌的登徒浪子,明明這份感情從一開(kāi)始就不是真正對(duì)等,仿佛為了成全她內(nèi)心的欲念之流而設(shè)立的如牢籠般的幽深禁錮,她還是義無(wú)返顧地墮入其中,飛蛾撲火式的愛(ài)情終究導(dǎo)致了薇龍的悲劇人生,曾經(jīng)的純真,歷盡荒糜的腐朽,綻放的情念,如轉(zhuǎn)瞬即逝的煙火,最終,消散,虛無(wú),變得毫無(wú)意義。
張愛(ài)玲性格當(dāng)中的敏感,冷漠構(gòu)筑了其部分消極的人生觀,世紀(jì)末的哀怨迷離、悲觀總是籠罩于其文本之中,書(shū)寫(xiě)不知明日復(fù)明日,只問(wèn)今朝欲樂(lè)的男女情事之際,張愛(ài)玲并沒(méi)有陷入哀怨愁情的傷感里,她總是冷眼以待,筆尖客觀而冷峻,深入探尋女性群體的微觀內(nèi)心宇宙。薇龍對(duì)物質(zhì)的迷戀,對(duì)愛(ài)與欲念的沉淪都盡現(xiàn)于張氏冷峻的思考之中了,薇龍?jiān)谧陨砼灾黧w的邊緣化的過(guò)程當(dāng)中是伴隨激烈的內(nèi)心斗爭(zhēng)的,她曾經(jīng)希望逃離這頹靡奢華的牢籠,逃離情與欲念的糾葛,只是這樣的掙扎在無(wú)形的巨大綴網(wǎng)中如此無(wú)力,情與欲何處歸宿之人生困惑與心靈層面的物欲侵染的精神危機(jī),對(duì)薇龍而言,乃是性靈深處的在劫難逃,于是,命運(yùn)早已注定,最后喪失了女性自身的主體地位,淪落為“他者”的可憐與可恨的悲劇人生也早已注定。
- 新生代的其它文章
- The improvement of camp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 關(guān)于雄安新區(qū)公共文化服務(wù)共享共治的對(duì)策建議
- 課堂寫(xiě)字小卡片 開(kāi)辟書(shū)寫(xiě)新天地
——小學(xué)寫(xiě)字教學(xué)“學(xué)習(xí)卡片”的應(yīng)用研究 - 世界命運(yùn)共同體下的中日命運(yùn)共同體構(gòu)想
- 基于山區(qū)支教引領(lǐng)青少年延安紅色文化思政教育與傳承的探索
- 瑪麗女王時(shí)期的英格蘭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