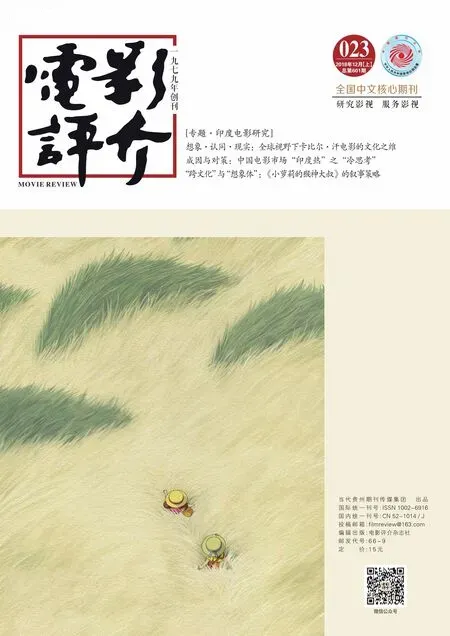電影臺(tái)詞的翻譯策略與文化認(rèn)同
在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的對(duì)外傳播大戰(zhàn)略下,影視作品作為大眾文化之一,自然成為了跨文化交流的生力軍。本文從文化認(rèn)同的視角出發(fā),以中國(guó)幾部具有廣泛影響和觀眾口碑的電影為參考藍(lán)本,分析其臺(tái)詞翻譯的策略和效果對(duì)電影的影響,以及目的語(yǔ)群體對(duì)電影所傳達(dá)的中國(guó)文化的接受度與認(rèn)同度。中國(guó)電影作為展現(xiàn)其民族意識(shí)和文化信息的媒介,在傳播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促進(jìn)跨文化交流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中國(guó)藝術(shù)“走出去的過(guò)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價(jià)值觀和文化的接軌”,電影字幕的翻譯是其中一個(gè)不容小覷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它極大地影響著目標(biāo)語(yǔ)受眾群體對(duì)電影故事內(nèi)容和主旨的理解,以及對(duì)電影所傳達(dá)的文化和價(jià)值的認(rèn)同。
一、中國(guó)電影臺(tái)詞的文化審美
錢紹昌先生指出,影視語(yǔ)言的特點(diǎn)在于其“聆聽(tīng)性、綜合性、瞬時(shí)性、通俗性和無(wú)注性”,許多經(jīng)典影片的臺(tái)詞在精雕細(xì)琢之后,語(yǔ)言尤其精煉利落卻又文采卓然,或通俗簡(jiǎn)樸描畫人生百態(tài),或意味雋永彰顯文化內(nèi)涵。總體而言,那些在海外觀眾中贊譽(yù)頗高、接受度好的中國(guó)電影除了作品本身的主題、質(zhì)量符合受眾的期待之外,中國(guó)特色的電影臺(tái)詞和有效的翻譯也功不可沒(méi),尤其是當(dāng)臺(tái)詞中具有典型中國(guó)文化特色的詩(shī)詞歌賦、典故成諺和其他文化負(fù)載詞的時(shí)候,電影臺(tái)詞的翻譯便顯得尤為重要。如電影《金陵十三釵》中的“商女不知亡國(guó)恨”源自李商隱的《泊秦淮》;電影《紅高粱》中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出自李白的長(zhǎng)詩(shī);《臥虎藏龍》中玉嬌龍吟誦的“瀟灑人間一劍仙,青冥寶劍勝龍泉……皇途霸業(yè)談笑中,不勝人生一場(chǎng)醉!”此詩(shī)也極其瀟灑逍遙,正好配合電影的意境傳播。這些詩(shī)詞的引用強(qiáng)化了對(duì)人物性格和身份的塑造,刻畫出極具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的人物形象。
電影臺(tái)詞中還常常運(yùn)用用典、化典、成語(yǔ)、俗語(yǔ)等方式,增強(qiáng)語(yǔ)言的傳播效果。如電影《赤壁》中“強(qiáng)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曹操自封為丞相,挾天子以令諸侯”“助紂為虐”等臺(tái)詞,運(yùn)用化典的方式來(lái)展現(xiàn)影片中角色的境遇和關(guān)系,提示了劇情發(fā)展的方向。
電影臺(tái)詞中還有反映歷史發(fā)展、社會(huì)制度、民俗風(fēng)情、生態(tài)地域等特征的文化負(fù)載詞。如電影《金陵十三釵》中的“閻王爺、釣魚巷、頭牌、二流子”;《英雄》中涉及中國(guó)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的“氣血攻心,膈俞穴入、步廊穴出”等詞語(yǔ);《臥虎藏龍》中反映中國(guó)社會(huì)倫理制度的稱呼“卑職、師娘、師傅”,表示官職的“翰林”等。這些電影臺(tái)詞中所蘊(yùn)含的中國(guó)文化內(nèi)涵和美學(xué)特征,向觀眾投射了某種特定的中國(guó)意象,而目的語(yǔ)觀眾在接收臺(tái)詞的同時(shí),實(shí)際上也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接受和認(rèn)同的過(guò)程。
二、歸化翻譯:同質(zhì)中的文化認(rèn)同
由于文本表述形式與展現(xiàn)手段的獨(dú)特性,電影臺(tái)詞翻譯的過(guò)程被認(rèn)為是一種跨語(yǔ)言、跨文化和跨學(xué)科的過(guò)程。在將中國(guó)電影向外譯介和傳播的過(guò)程中,電影臺(tái)詞的翻譯要考慮到目的語(yǔ)觀眾對(duì)語(yǔ)言、文化和審美的接受需求,不單只向觀眾傳遞影片的故事情節(jié),更應(yīng)有助于觀眾從中了解和接受本土文化。因此,通過(guò)歸化和異化的翻譯策略,對(duì)影片中具有典型中國(guó)文化特色的臺(tái)詞進(jìn)行翻譯,是國(guó)產(chǎn)影片實(shí)現(xiàn)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
歸化,通常指譯者在翻譯時(shí)采用一種透明而流暢的譯文,從而使得原語(yǔ)文本對(duì)于讀者的陌生感(strangeness)降至最低。就電影臺(tái)詞的英譯而言,可以說(shuō)是用“符合英語(yǔ)民族的語(yǔ)言習(xí)慣、思維習(xí)慣,來(lái)講述中國(guó)故事、宣傳中國(guó)文化,用譯入語(yǔ)文化傳統(tǒng)來(lái)替代或描述中國(guó)特有文化的表達(dá)法”,因此更容易為目的語(yǔ)觀眾所理解接受并產(chǎn)生文化認(rèn)同。
(一)語(yǔ)言層面
中西方語(yǔ)言層面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語(yǔ)音、語(yǔ)形、語(yǔ)義、語(yǔ)法的差異上,就電影臺(tái)詞的歸化翻譯而言,主要集中在語(yǔ)義的處理上。首先電影臺(tái)詞中一些稱呼和官職采用了歸化翻譯策略,如張公公(Mister Zhang),大王/丞相(His Majesty),劉豫州(Lord Mayor Liu)等,用英語(yǔ)中的相關(guān)對(duì)等語(yǔ)進(jìn)行意譯,可以讓目的語(yǔ)觀眾與影片中的相應(yīng)官職直接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便于他們了解角色的身份和地位。雖然觀眾對(duì)于漢語(yǔ)中“劉豫州”一詞的歷史背景并不清楚,但這種譯文并不影響他們對(duì)劉備身份的了解與傳播。
此外,在句子語(yǔ)義的翻譯中,歸化也是比較常見(jiàn)的。電影《紅高粱》中的“有會(huì)出氣兒的沒(méi)有”,表達(dá)了受人冷落的不滿與憤懣,意譯為“Is there anyone awake”。反問(wèn)句式雖也能表現(xiàn)出被無(wú)視的不滿,但用“awake”替代“會(huì)出氣兒的”,總的來(lái)說(shuō)語(yǔ)氣上的強(qiáng)烈程度削弱了,難以讓觀眾與人物角色一樣感同身受。電影《臥虎藏龍》出現(xiàn)了一系列“不敢當(dāng)、過(guò)獎(jiǎng)了、獻(xiàn)丑了、哪里話、哪里哪里、折煞我了、承讓承讓”等詞語(yǔ),在中國(guó)文化中表示謙恭、禮貌的語(yǔ)句,顯然這與西方文化強(qiáng)調(diào)的個(gè)人價(jià)值觀有很大不同。因此,譯者為了適應(yīng)西方的交際習(xí)慣和實(shí)現(xiàn)字幕的交際功能,一般會(huì)采用歸化的策略而翻譯成“Thank you,you are welcome, that’s OK”等語(yǔ)句來(lái)進(jìn)行統(tǒng)一表達(dá)。當(dāng)然,有時(shí)為了加強(qiáng)觀眾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會(huì)省譯一些與故事關(guān)聯(lián)性較弱且不影響觀眾理解的信息,如電影《赤壁》中的臺(tái)詞“這不叫如虎添翼這叫如虎添璞”“諸位不必多禮”在翻譯時(shí)分別省譯了“這不叫如虎添翼”和“不必多禮”的部分,這是為了西方觀眾更好接受傳播的因素。
(二)語(yǔ)境層面
在電影臺(tái)詞英譯中的語(yǔ)境層面,主要涉及臺(tái)詞的上下文語(yǔ)境、影片中的情景語(yǔ)境和中國(guó)文化語(yǔ)境。上下文語(yǔ)境和情景語(yǔ)境,與電影臺(tái)詞的效果關(guān)聯(lián)較大,對(duì)影片氣氛的形成和故事情節(jié)的推動(dòng)有重要影響。有時(shí)同一個(gè)臺(tái)詞在影片中多次出現(xiàn),但出現(xiàn)的具體語(yǔ)境會(huì)發(fā)生變化,因此在翻譯的時(shí)候也要酌情考慮而區(qū)別處理。
比較典型的如電影《英雄》中的“我們?cè)僖膊粫?huì)浪跡江湖了”,翻譯成“No more drifting, no more roaming”,翻譯語(yǔ)句所構(gòu)成的排比結(jié)構(gòu)整齊,語(yǔ)句凝練。“江湖”一詞在該片中出現(xiàn)了三次,在中文語(yǔ)境中常指?jìng)b士行走世間,縱橫四方,有特定的文化內(nèi)涵,而在英語(yǔ)中沒(méi)有相應(yīng)的對(duì)等語(yǔ)。譯者結(jié)合電影不同的情境和語(yǔ)境,在另兩處分別譯為“l(fā)iving a carefree life”和“drift”,給人一種瀟灑自在和漂泊無(wú)定的感覺(jué)。
有些臺(tái)詞的翻譯則是置身于整體的中國(guó)文化大語(yǔ)境之下,因此在翻譯時(shí)要考慮的是中西方文化語(yǔ)境的接受適應(yīng)度。如影片《金陵十三釵》中“閻王爺在哭你呢”、《我不是藥神》中“人就沒(méi)了”、《霸王別姬》中菊仙所說(shuō)的“早就入土”,都是對(duì)死亡直接或委婉的表述,在結(jié)合臺(tái)詞的上下文語(yǔ)境和英語(yǔ)國(guó)家的文化語(yǔ)境下,也都相應(yīng)地譯成了“The death weeping for you”“He will be gone”“be six feet under”,如此翻譯不僅能體現(xiàn)語(yǔ)句的時(shí)態(tài)特點(diǎn),還能表現(xiàn)人物的語(yǔ)氣心情,同時(shí)還巧妙的結(jié)合了所要表達(dá)的文化內(nèi)涵。
(三)文化層面
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共性和文化的同質(zhì)性,也使得文化的翻譯成為可能。而在電影的臺(tái)詞翻譯中,文化因素既是影片吸引觀眾的魅力所在,也是翻譯難點(diǎn)。“歸化翻譯”是最貼近譯語(yǔ)文化的對(duì)等語(yǔ),它能傳譯臺(tái)詞中的文化因子,以降低中國(guó)文化對(duì)目的語(yǔ)讀者的陌生感,使他們能夠理解、接受并欣賞中國(guó)文化。
一種翻譯方法是采用“意譯”的方法,盡量使用英語(yǔ)文化中相同或相似的表達(dá)來(lái)翻譯。影片《我不是藥神》中,有些與宗教相關(guān)的臺(tái)詞在翻譯時(shí)就盡量弱化了佛教文化。如“黃泉(afterlife)”“救人一命勝造七級(jí)浮屠(There is greater merit in saving one life than in building a seven-tier pagoda)”“你不入地獄誰(shuí)入地獄(You cannot escape your destiny.It’s a dirty job, but someone got to do it)”的翻譯,這也是通過(guò)歸化翻譯來(lái)順應(yīng)大多數(shù)英語(yǔ)國(guó)家觀眾不同的宗教信仰,避免宗教文化沖突。
此外常見(jiàn)的還有成語(yǔ)俗語(yǔ)的翻譯,如電影《紅高粱》中的“見(jiàn)錢眼開(kāi)(money-grubber)、眉來(lái)眼去(flirting 調(diào)情)”;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比猴還精”翻譯成英語(yǔ)文化中的“as sly as a fox”;《英雄》中“大音希聲之境”意譯為“a supreme state”等,都傾向于用簡(jiǎn)潔、切近的語(yǔ)言來(lái)翻譯原語(yǔ)的意思,傳達(dá)原語(yǔ)的文化,再現(xiàn)原語(yǔ)的意境。
另一種常見(jiàn)的翻譯方法就是“省譯”。中西方文化的異質(zhì)性較大,為了盡量減少目的語(yǔ)觀眾的理解困難,增強(qiáng)觀影的體驗(yàn)效果,保證文化層面的有效交流,采用“省譯”犧牲原臺(tái)詞中文化內(nèi)涵較強(qiáng)的表達(dá)也是可以接受的。如電影《英雄》中“三教九流,人來(lái)人往”一句采用了減譯的方法,放棄了“三教九流”原本的文化色彩,翻譯成“Here, you’ll find all sorts of characters”。
采用歸化策略來(lái)翻譯電影的臺(tái)詞,是基于文化本身存在的共性,這種翻譯策略在電影臺(tái)詞或字幕的翻譯中也是普遍適用的。電影向外傳播的目的和歸化翻譯策略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用最貼近、自然、流暢的語(yǔ)言來(lái)傳達(dá)影片的故事和文化,引發(fā)觀眾的共鳴和認(rèn)同,電影和翻譯實(shí)現(xiàn)跨文化交流的共同目的才真正得以實(shí)現(xiàn)。
三、異化翻譯:異質(zhì)中的文化融合
“異化”,是指譯者在翻譯時(shí)故意保留原語(yǔ)文本當(dāng)中的某些異質(zhì)性(foreignness),以此打破譯入語(yǔ)的種種規(guī)范,主要指在詞匯層面上或目的語(yǔ)文本的局部,采用以原語(yǔ)或原語(yǔ)文化為取向的表達(dá)方式。在電影臺(tái)詞翻譯中,使用異化策略旨在保留原臺(tái)詞的文化內(nèi)涵和特色,以這種“異質(zhì)性”給觀眾帶來(lái)異域風(fēng)情的新鮮感和吸引力。我們可以從符際翻譯、語(yǔ)內(nèi)翻譯和語(yǔ)際翻譯這三個(gè)方面進(jìn)行簡(jiǎn)要解讀。
電影的“符際翻譯”主要涉及臺(tái)詞的口語(yǔ)表達(dá)、文字字幕、電影畫面、背景聲音等,其各個(gè)方面的關(guān)聯(lián)配合和互文參照可共同表達(dá)影片信息,展現(xiàn)影片效果。《我不是藥神》中有一個(gè)場(chǎng)景是程勇在回店時(shí)看到店門上被房東貼上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交租開(kāi)門!!”而同時(shí)字幕上顯示了這張圖片內(nèi)容的英譯“Rent for the key”,這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將圖片轉(zhuǎn)換成文字的符際翻譯。影片在翻譯時(shí)省去了原語(yǔ)當(dāng)中的兩個(gè)感嘆號(hào),削弱了房東催租的急迫心情,如果用大寫字母稍作修改“RENT for the KEY”表現(xiàn)力會(huì)更強(qiáng)。
大多數(shù)影片對(duì)于片中出現(xiàn)帶有中文的畫面或無(wú)臺(tái)詞圖像,都是選擇零翻譯的。雖然對(duì)國(guó)內(nèi)觀眾而言并不影響對(duì)劇情的理解,但這種符際翻譯的缺失可能會(huì)對(duì)國(guó)外觀眾造成困惑。而這部影片畫面中多次出現(xiàn)程勇的店名“王子印度神油店”,假藥販子張長(zhǎng)林在舞臺(tái)上方做宣傳時(shí)懸掛“熱烈歡迎醫(yī)學(xué)院國(guó)際著名專家張長(zhǎng)林院士蒞臨指導(dǎo)”等虛假信息,影片就沒(méi)有進(jìn)行圖片文字和字幕英譯之間的轉(zhuǎn)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目的語(yǔ)觀眾對(duì)背景信息的了解,另一方面這種純粹出現(xiàn)的中國(guó)漢字,同時(shí)也能激發(fā)觀眾一定的東方文化聯(lián)想。這部影片中還展現(xiàn)了臺(tái)詞的“語(yǔ)內(nèi)翻譯”和“語(yǔ)際翻譯”同步進(jìn)行的現(xiàn)象。影片開(kāi)頭程勇給其生病的父親喂粥時(shí),二人是用上海方言對(duì)話的,字幕展現(xiàn)時(shí)用普通話轉(zhuǎn)換了二人的對(duì)話內(nèi)容。上海話和普通話是屬于同一文化體系的漢語(yǔ),二者之間的語(yǔ)言轉(zhuǎn)換可歸于語(yǔ)內(nèi)翻譯;與此同時(shí)再根據(jù)這種語(yǔ)內(nèi)翻譯將漢語(yǔ)臺(tái)詞轉(zhuǎn)譯成英語(yǔ),即完成語(yǔ)際翻譯過(guò)程。當(dāng)然這種語(yǔ)內(nèi)翻譯對(duì)大部分目的語(yǔ)觀眾的影響較小,因?yàn)闊o(wú)論上海話還是普通話,對(duì)他們而言都屬于難以理解的異質(zhì)信息。
在跨文化對(duì)外傳播過(guò)程中,“語(yǔ)際翻譯”的效果和作用則是影片臺(tái)詞翻譯的重中之重,異化翻譯策略在對(duì)文化“異質(zhì)性”和“陌生感”的保留方面也有度的考量。“語(yǔ)際翻譯”中異化策略常用于人名、地名、書名、朝代名等專有名詞和一些普通名詞,而且很多時(shí)候還與歸化翻譯相結(jié)合。如某些電影中出現(xiàn)的詞牌名“《秦淮景》(The Qin Huai View)”,人名“掌柜李大頭(Datou Li),羅漢大哥(LUO Han Brother)”,地名“十八里坡(Slope Shibali)”,普通名詞“風(fēng)水(Fengshui),包子(Baozi)”等,在譯文中都保留了中國(guó)文化特色,能給目的語(yǔ)觀眾以耳目一新的感覺(jué)。
結(jié)語(yǔ)
電影臺(tái)詞的翻譯作為跨文化交流的紐帶和橋梁,涉及了口語(yǔ)臺(tái)詞、文字符號(hào)、圖像畫面、聲音色彩等諸多因素的傳譯,具有跨語(yǔ)言、跨學(xué)科、跨文化的交際功能。歸化策略和異化策略的靈活使用,能夠有的放矢地對(duì)影片臺(tái)詞進(jìn)行最有效的翻譯,最大程度的傳達(dá)影片的內(nèi)容和相關(guān)的文化,引發(fā)觀眾對(duì)兩種文化同質(zhì)性的欣賞和認(rèn)同,異質(zhì)性的接納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