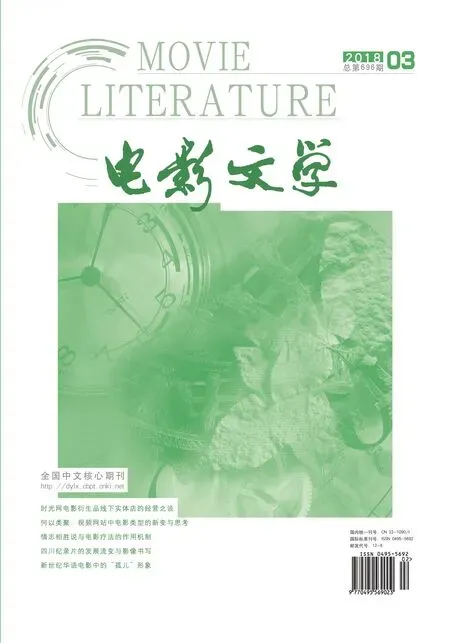品牌策略:陜西文學與西部電影改編
徐 翔
(西安培華學院 人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5)
縱觀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會發現電影與文學的合作由來已久,并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20世紀30年代,便有文學名著被改編成電影,如茅盾的《春蠶》,及至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呈現一種井噴的姿態,如魯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鋪子》、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等。“文學除了能夠為電影化的移植提供作品之外,它還能夠為真正的銀幕創作提供豐富多樣的題材和形式:神話和傳奇、主題、情境、體裁、風格、美學觀念,尤其是語言風格、人物心理和讀者心理等方面的寶貴經驗。”而電影這一現代傳播方式也可以促進文學作品的流傳,電影和文學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微妙的互動關系,一種“意義明確但卻若即若離、似遠似近的糾纏甚至是折磨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和電影以各自不同的表現形式都對此做出了回應,陜西當代文壇的諸多作品便成了西部電影的改編對象。浸潤于陜西厚重的黃土文化土壤中的陜西文學給西部電影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而陜西文學也借助西部電影這一平臺在全國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兩者互生互長,結出了繁碩的果實。如何使陜西文學與西部電影這兩個既有品牌雙贏互惠,實現品牌共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一、作為品牌的陜西文學和西部電影
品牌是一種無形資產,卻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品牌具有差異性和可識別性,是某一商品區別于同類競爭品牌的重要標志。在商業化時代,品牌體現了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程度,消費者對一個產品的認知程度越高,該產品就越易形成品牌,從而具有品牌優勢。陜西文學和西部電影在各自的領域成就卓越,已經形成了一種品牌優勢。
稍加留心就會發現,當下的文壇充斥著品牌,80后創作、網絡小說、青春寫作,還是主流文壇,品牌已成為現今文學界一個不能被忽視的現象。如湖南作家群、河南作家群;《收獲》《鐘山》《當代》等刊物的名刊鍛造;“布老虎”等暢銷叢書的出版策劃;“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文學獎項的評定等,不同文學品牌的建設增強了文學的多元化和市場競爭力。陜西文學便是既有的、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品牌。陜西素有“文學重鎮”之稱,新中國成立初,柳青、王汶石、杜鵬程等作家憑借其創作在當時的文壇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之后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讓陜軍這面旗幟在文壇高高飄揚,甚至引起了令人矚目的“陜軍東征”現象;陜西文壇的后起之秀如高建群、紅柯、葉廣芩等同樣創作頗豐,陜西作家在文學創作上形成了獨有的特色和優勢,陜西文學成為當代文壇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也成為一個得到業界和市場認可的品牌。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形成品牌是其產業化發展的有效策略。唯美的畫面、凄楚的愛情是韓國電影的品牌特色;功夫片則是中國香港電影的品牌特色,內地電影也有自己的品牌,如馮小剛的賀歲片。事實上,西部電影早已形成品牌。“西部電影”這一概念是電影評論家鐘惦棐先生于1984年提出的,他在觀看完由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人生》之后,提出了“開拓新型的‘西部片’”這一理念,這一觀念在電影界也引起了強烈反響。于是,以西安電影制片廠為代表的諸多電影廠和充滿創新意識的第四代、第五代導演紛紛把自己的藝術關注點投向了西部這片廣袤神奇的土地。僅僅幾年之間,便推出了一批充滿西部風情的電影佳作,如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等。這些影片在中國影壇引起了轟動,也引起了國際影壇的注目。西部電影成為溝通中國和世界的一座橋梁,更成為一個具有極高知名度的電影品牌。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引發了電影體制的變革,加之好萊塢商業大片對中國影壇的沖擊,西部電影也受到波及,處于低谷狀態。到了2000年之后,中國電影漸漸擺脫頹勢,西部電影也重新煥發了活力,《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無人區》《白鹿原》等影片的問世為西部電影再次贏得殊榮,觀眾也再次領略了西部電影恒久的藝術魅力,經歷了時間的洗禮,這一品牌也更具價值。
二、品牌共融:陜西文學與西部電影的雙贏
文學與電影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親緣關系,文學作品一向是電影改編的首選,西部電影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優秀文學作品也情有獨鐘。作為“文壇重鎮”的陜西,為西部電影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陜西人張子良是著名的電影編劇,電影《黃土地》《一個和八個》的劇本就出自其手;作家楊爭光和葉廣芩則是跨界文學創作和電影創作;更為重要的是陜西文學為西部電影改編貢獻了一系列佳作。賈平凹的小說《雞窩洼人家》《臘月·正月》《五魁》《高興》分別被改編成影片《野山》《鄉民》《五魁》《高興》,路遙的《人生》和陳忠實的《白鹿原》分別被改編成同名影片。可以說,陜西當代文壇佳作頻出對西部電影的繁榮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樣,西部電影也對陜西文學的繁榮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以下將從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
(一)陜西文學對西部電影的藝術助動
張藝謀曾在一次頒獎典禮上說:“看中國電影繁榮與否,首先要看中國文學繁榮與否。中國有好電影,首先要感謝作家們的好小說為電影提供了再創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這些小說,中國電影的大部分都不會存在。”
陜西是文化大省,“秦中自古帝王州”,歷史上這里涌現了太多的帝王將相和名士大儒,多少文豪曾在這里揮毫潑墨。僅就當代文壇而言,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葉廣芩等人便構成了一幅星光燦爛的群星圖,《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曾經獲得過文學界的重量級獎項“茅盾文學獎”,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自然而然成為電影改編的首選。西部電影之所以成為品牌,是因為其蘊含的西部風情。陜西文學本身所蘊含的原生態的西部風情和人文底蘊對西部電影的思想內蘊和極具特色的影像風格有著重要的建構作用。
陜西文學往往對陜西乃至西部的地理風貌有著形象的描繪。陜北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原、關中肥沃的千里平原,這些極富西部風情的自然景觀對西部電影創作有重要的影響,同時也使西部電影極具辨識性。西部電影鏡頭下的巍峨群山、沙漠戈壁、黃土高原便是西部電影的標簽,這些景觀便構成了西部電影沉郁厚重粗獷的影片基調。電影《人生》的開頭便使用大量空鏡頭對黃土高原進行了表現,鏡頭下的高原、嶙峋的黃土溝壑極具西部風情。陜西文學中極具西部風情的不僅有自然景觀,更多的是極具地方特色的民風民俗,民風民俗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它依靠習慣勢力、傳襲力量和心理信仰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和意識,世代相習”。而陜西由于獨特的地理條件,由高原到平原再到山區,便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民俗,陜北有腰鼓、剪紙、信天游;關中則有皮影、秦腔;陜南則有灶火、哭嫁等。這些民俗不僅進入了創作領域,也進入了西部電影中,民間的衣食住行和婚喪嫁娶在西部電影中被大量地展現,大大增加了電影的觀賞性。更為重要的是,陜西文學源自黃土的厚重感和民族性,大大豐富了西部電影的人文底蘊。可以說,西部電影不僅從陜西文學中借鑒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更從文學作品中汲取了深厚的人文底蘊,而具有人文底蘊是優秀的電影所不可或缺的,“在電影里, 人們從形象中獲得思想, 在文學里, 人們從思想中獲得形象”。通過對優秀的陜西文學作品的改編,西部電影不但獲得了形象,也獲得了思想,更贏得了觀眾和市場。
陜西文學為西部電影創作提供了大量優秀素材,同時陜西文學本身所具備的厚重的人文底蘊,加之其品牌的影響力可以從多方面推動西部電影的發展。
(二)西部電影對陜西文學的傳播價值
當下的時代是新媒體時代,傳播媒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印刷傳播逐漸被電子傳播取代,甚至連人們的閱讀也由傳統的紙質閱讀發展為電子書籍和網絡文學的閱讀,這種傳播方式和閱讀方式的變化對傳統文學的生存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在20世紀,文學作品主要還是依靠印刷媒介進行傳播,傳播效果和影響事實上大大高于電子媒介傳播,但進入到21世紀,科技迅速發展,電子傳播媒介成為主流,包括電影、電視、網絡等形式。文學作品如果還僅僅依靠印刷傳播,將會大大降低其傳播力度和影響力,這會導致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并不會被大眾所認知,因此,文學迫切需要轉型。在21世紀,電影作為一種電子傳播形式,一方面屬于大眾傳媒,其傳播力度和影響力是巨大的;另一方面,電影也是一種藝術,和文學一樣,具有敘事的能力。因此,文學可以借助電影這一現代大眾傳媒方式實現再傳播。
以賈平凹的小說《高興》為例,小說不失為一部優秀的小說,非常接地氣,反映了城市化過程中小人物的生存本相。小說于2005年出版,但出版之后也僅僅在文學界和文學愛好者圈子里引起關注,社會大眾對此關注并不多,很多人也只是知道賈平凹出版了一本新作而已。2009年,小說《高興》被導演阿甘改編成同名影片,并且搶占了當年的賀歲檔,電影在宣傳方面很成功,充分借助了賈平凹的“名人效應”以及人們對賈平凹作品的心理期待,電影的成功也再次引起了人們對小說的關注,這是文學借助電影實現再傳播的成功例子。再以電影《白鹿原》的上映為例,電影從立項到開拍波折重重,因此也一直得到大眾傳媒的關注,上映之后迅速引起了討論熱潮。客觀地講,電影的改編并不算非常成功,因此也招致許多批評的聲音,但無論是贊譽還是批評,電影成為一個焦點,引得很多人去看電影或者去閱讀原著。事實上,隨著電影的火熱上映,《白鹿原》原著也再次火爆起來,各家出版社以各種版本形式,爭相出版。各大電商網站上,《白鹿原》也一度出現脫銷。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借電影上映的熱度,推出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紀念版”,這一版本增補了作者的創作手記以及一些珍貴的照片和手稿照片。老讀者買書為收藏,新讀者買書為“補課”,除了原著的熱銷,還有電影衍生品“白鹿原影視基地”的建立。可以說,電影的播出激起了人們的閱讀欲望,對原著《白鹿原》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而相關電影衍生品的出現,更是實現了文學的產業化。當然,這并不是說凡是觀看影片的人都會去閱讀原著,但電影是一種“泛文學”形式,即便觀眾只關注電影,對電影的欣賞也是對于文學的另一種形式的“解讀”,在潛在層面依然可以增加文學的影響力。
在當下產業化發展的大趨勢下,陜西文學和西部電影都在尋找產業化發展的新路徑,如何讓這兩個既有的品牌緊密契合,實現文學和電影的雙贏,既是西部電影人所努力探尋的,也是陜西當代作家們所認真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