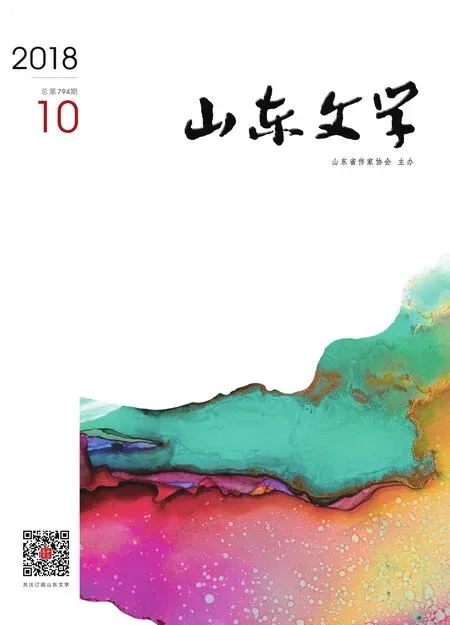道別記
楊 奇
我得到的都是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摘自《等風來》
1
這初冬午后的陽光亮是亮,熱度卻是大打折扣,不然那些走在光里的人怎么會把身上的衣服裹得緊緊的?這亮光打在窗前光禿的樹枝上,大部分落到地上的草叢里。草尖發黃了,頂著一層黃色的落葉,顯出幾分破敗。黎落英不懂那些惜春傷秋的詞句,但見這種情景心里不免悲涼,忍不住嘆息了一聲。
徐雅子的聲音就是在黎落英這一聲嘆息之后傳過來的:如果從這里跳下去,頭著地的話還行,分分鐘的事,如果腳著地的話,死不了還得弄個終身殘疾,可就得不償失了。
黎落英打了個寒噤,扭過頭錯愕地問徐雅子:你說啥?
徐雅子將一只耳機從耳朵上扯下來,眼睛離開膝蓋上的平板電腦,望著黎落英說:其實這個想法我早就有了,只是還沒付諸實施罷了。
你?黎落英蹙了下眉頭,正要開口,徐雅子朝她伸出手做了個“打住”的手勢說:別勸我。你別忘了,你不是我媽,我們不過是病友而已。
黎落英被噎住了,許久才回過神來,然后嘆了口氣說:好吧,我不勸你,我勸我自己。
這就對了嘛。徐雅子拍了拍手里的平板電腦,一副很滿意的樣子,繼續說:你不能死,你得好好活著。
黎落英心情突然好了許多,來到這里十幾天,徐雅子可從來沒對她說過這樣的話,甚至都沒露過這種歡快的表情。她的臉一直陰著,表面蕩漾著一層白氣,給人一種很不好的感覺。而現在,這層白氣被窗口射進來的亮光覆蓋了,變得金燦燦的。
那你呢?黎落英笑了笑。
我嘛?徐雅子沉思了一下說,我跟你不一樣,我了無牽掛。
這話說的。黎落英搖搖頭說,誰在這個世界上都不是單蹦個,怎么可能無牽掛……
怎么又扯回我身上來了?徐雅子不高興地打斷黎落英的話,臉上那層金光也瞬間消失了。
黎落英自知無趣,便不再說話了。徐雅子說得沒錯,不過是病友而已,自己有什么資格管人家?
這時候徐雅子又說,其實你的病比我輕多了,也好治,你現在主要是心病,就是放不下的東西太多,放下了你的病就好了,這是我從書上看的,你可以試試。
怎么試?黎落英一臉的疑惑。她總是不能第一時間聽懂徐雅子的話,這讓她很苦惱。
比如跟那些你牽掛著的人道個別啊啥的,具體我就說不上來了。徐雅子搖搖頭,將那只摘下的耳機重新塞進耳朵里。
道個別?黎落英一邊重復著徐雅子的話一邊默默地折身回到自己床上,待她躺下的時候,徐雅子已經哼起了歌。黎落英現在知道了,那首歌的名字叫《等風來》,是最近剛上映的一個電影的插曲。她以前從沒聽過這首歌,可現在也能跟著哼哼了。
2
也不知道這個徐雅子有什么魔力,只要她說出什么話來,黎落英就覺得特別有道理,心服口服,她甚至因此而覺得自己活得太失敗了,很多事情,尤其當今社會一些最時尚前沿的東西,自己簡直一竅不通,那些從她嘴里說出來的電影明星啦、流行歌曲啦、新上映的電影啦她更是聞所未聞。還有就是關于這個“乳腺癌”,按她的說法竟然分好幾個等級,有的等級能治好,有的等級會死人,還有哪些明星得上了治好了,而哪些人卻死在了上面。她以前只知道這是女人常得的一種癌,得了就會要命——遲一天早一天的吧。
當然對于徐雅子的話她也并非完全贊成的,還是比如這個“乳腺癌”吧,按她的說法,自己得的這個就屬于最低的等級,只要動手術切一下,根本沒有生命危險。她徐雅子得的卻是最高級的,根本沒有手術的價值了,除了等死基本無事可做了。她就不這么認為,她有她們小區的韓姐為證。
韓姐是小區里的“高級人物”,這是黎落英下的定義,要模樣有模樣,要出身有出身,要家世有家世,老公是市政府某個要害部門的一把手,她是市文化局的退休干部,能歌善舞,經常出現在各類演出的舞臺上,是小城里響當當的人物,可幾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就被查出了乳腺癌。不過她很樂觀,黎落英覺得這是表面上的,見面還是嘻嘻哈哈的,給人解釋說醫生說了病能治好,只要挨一刀就跟正常人沒什么兩樣了,她甚至還給人普及起了“乳腺癌”的相關知識。其實一開始黎落英跟小區里的絕大多數人一樣是相信韓姐的話的,可轉年后不久她的病就復發了,還轉移了,結果新的年沒過人就沒了。所以當徐雅子說她的病能治好的時候,黎落英是無論如何不相信了,她甚至還想拿韓姐的例子駁斥她,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她覺得那樣做太殘酷了。
在跟徐雅子同處一室的這一個多月里,雖然談不上對她有多了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打心里越來越喜歡她了。不過她一直努力地控制著喜歡的程度,不讓它發展壯大,因為她已經逐漸摸清了徐雅子性格的兩大特點:敏感、喜怒無常,她必須謹慎對之,否則恐怕連病友都做不成了。而現在好像突然出現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徐雅子不僅主動跟自己聊天,還向自己提建議,她突然有種雨過天晴要見彩虹的感覺……
呀呵,心情不錯啊,竟然哼起歌來了?隨著粗重的關門聲,丈夫梁金生的聲音隨之而來。
要不是梁金生說,黎落英還真沒注意自己啥時候跟著徐雅子哼起了歌。被打斷后,她依舊閉著眼睛,身體沒動,沒做出任何回應,這在以前是絕無可能的。確切地說,在這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里,丈夫是她的天,是她的全部,對他她只有言聽計從,甚至頂禮膜拜。她從來都認為,這場婚姻,丈夫賠了,自己賺了。賺了就得知足,就得拿東西來去償還,比如尊嚴。可是這個想法在不久前,確切地說是在認識徐雅子之后發生了變化。那是她跟徐雅子認識后的第一次長談,其實也就十幾二十分鐘吧,徐雅子對她說了一番關于女人要如何生活的話,歸根到底就是一個意思,要為自己活。徐雅子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她得病就與這個有關系。聽著徐雅子的話,黎落英感覺面前有個什么無形的東西突然坍塌了,她看到了一個跟過去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知道你也不想生病,可也不要這樣氣鼓鼓的嘛,我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我知道這些年我對你態度不好……
丈夫又開始絮叨這番話。這番話現在就好像變成了一份講話材料,一直掛在他嘴邊,需要了就拉出來重復一遍。黎落英實在聽不下去了,就打斷他說,我沒生氣。黎落英本想口氣硬一點兒,但聲音出來后還是軟綿綿的,就好像不受她控制一樣。
丈夫愣了一下,噗嗤一笑說,沒生氣就好嘛。然后就打開保溫桶,用勺子舀起一勺湯,吹了吹,朝黎落英嘴邊遞過來。
黎落英遲疑了一下,還是張開嘴把湯接住吞了下去,然后起身抓住勺子說:我自己來。
丈夫沒有堅持,雙手解放后一屁股坐在床邊拍打著腰說,這一天到晚把我忙的,渾身都疼。
心頭掠過一絲心疼,但轉瞬即逝。黎落英繼續喝湯,并發出比較大的聲響,以此來掩蓋心里的局促。
“食不發聲”是早些年丈夫給她立下的規矩。其實她從小以來從沒想過吃飯會有什么規矩,直到嫁給丈夫之后她才發現自己吃飯的方式,使勁咀嚼、粗聲喝湯等等,簡直是肆無忌憚。其實她生活的那個小山村里的人大都是這樣的,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丈夫吃飯的時候姿勢正,小口嘬,這讓她無地自容,自覺性加上丈夫的白眼,慢慢地她也學會了“食不發聲”。當然丈夫的規矩還有很多,比如笑不露齒、輕拿輕放、物歸原地等等,她都慢慢學會了,倒是后來丈夫隨著年齡的增長把這些規矩逐漸拋之腦后,變得越來越粗魯了。有時候她就恍惚,覺得丈夫跟自己發生了乾坤大挪移。
看到黎落英沒任何回應,丈夫臉上掠過一絲失望,搖了搖頭,又嘆了口氣說,親家說了,醫院環境太差了,還是先不讓孫子來了。
黎落英頓了一下,說,不來就不來吧,兒子都不是自己的了,別說孫子了。
其實她也想嘆一口氣的,但被她使勁咽了回去。她覺得此時此刻那一聲嘆息就像一把鈍刀,沒什么殺傷力也沒什么存在的意義了。
丈夫抬起臉,訕笑著說,沒事,你還有我呢。
丈夫的笑容明顯有些討好的意思,當然也夾雜著一些尷尬和凄涼,里面有讓黎落英感覺到同病相憐的東西,也有讓她失望甚至憤怒的東西。
她又喝了幾口湯,將保溫桶放到了床頭柜上。丈夫抬著頭看了看里面,大聲說,你還沒吃肉呢?
黎落英搖搖頭說,沒胃口。
丈夫正要開口,那個男人推門進來了。男人臉上帶著微笑,很有禮貌地跟丈夫點了點頭,丈夫也跟他點點頭,臉上的肌肉卻僵住了。
丈夫站起身,局促地看了看四周,突然發現救命稻草似的提起腳邊的暖水瓶說,我去打熱水。丈夫出去了,黎落英知道暖水瓶是滿著的,她知道丈夫也是清楚的,只是都不愿意說出來。
3
黎落英閉上眼睛。丈夫把尷尬丟給了自己,她得把自己變成一團空氣。
男人小聲地跟徐雅子說話,然后是打開保溫桶的聲音,再接下來就是男人吹湯和徐雅子喝湯的聲音。兩人都不多言,配合默契,像一對尋常父女那樣。
男人的真實身份是丈夫先看穿的,那應該是黎落英住院的第九天上,男人第二次來。那時候黎落英跟徐雅子已經成了可以隨意交流的熟人,黎落英已經從心里開始喜歡這個安靜漂亮的姑娘。男人要走,徐雅子出去送他。兩人走后,丈夫突然給她使了個眼色,問道,知道他倆什么關系嗎?
黎落英不明所以地朝門口看了看說,能是什么關系?父女唄。
等她回過頭來時,卻看到了丈夫猥瑣的表情,她立刻恍然。但她并不想接受這個答案,有些憤怒地說,別在這里胡說八道。
你看他看那姑娘時候的眼神,色瞇瞇的,哪像個父親?丈夫胸有成竹地說。
她本想用“這種事情也就你能看得出來”來搶白丈夫,但想一想還是算了,這會讓她回想起當年丈夫那段讓她不堪回首的出軌往事,倒不是她害怕去回憶,而是覺得沒必要了。
戳破了徐雅子的秘密,黎落英倒生出幾分愧疚感,就好像自己做錯了什么,以致接下來一段時間跟徐雅子說話都有些不自然。徐雅子到底還是感覺出來了,于是在幾天之后,也就是在另一個男人來過之后,徐雅子告訴了她一切。
原來這第二個醉醺醺臟兮兮的中年男人才是徐雅子的父親,他游手好閑身無分文,他來醫院不是關心徐雅子的病情,而是來跟她要錢的。臨走時他翻走了徐雅子外套里所有的錢,還搶走了她的手機。
徐雅子的住院費、衣服、手機等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第一個男人提供的,他是個有錢的有婦之夫,他跟徐雅子是通過某個網上交友軟件認識的,他們的關系已經維持了快兩年了。他們每周見一次面,徐雅子住院以后依然是這個頻率,每次她都要跟他出去。他來之前都會在醫院附近的賓館開好房。男人離開前都會給徐雅子留下錢或者她需要的其他東西。說起來,這個男人對徐雅子真是好,既有父親那樣的好,也有男人那樣的好。黎落英因此從心里對男人有了好感,以致丈夫想說他壞話的時候她都會橫加制止。
那次長談之后,黎落英跟徐雅子的關系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她甚至將她攬進懷里哽咽著說,你要不嫌棄的話,就做我的干女兒吧。
徐雅子卻冷靜地推開她說,不必了,我們還是做病友吧,感情對我來說都是負擔。
盡管極為失落,黎落英還是盡量微笑著點了點頭。
那天下午,兩人還破天荒地討論起了彼此的病情。徐雅子還極爽快地解開病號服的紐扣,指著自己的兩個乳房對她說,你別看它跟正常人沒什么兩樣,其實里面就是兩塊朽木,朽木知道吧,一拍就碎的那種。
黎落英飛快地掀起自己的病號服,她連紐扣都來不及解,她怕自己動作慢了眼淚會不爭氣地流下來,然后說,我這才是生病的,你看你的,嬌嬌嫩嫩的,一點兒都不像有病的。
徐雅子低下頭望著自己的乳房好大一會兒,像是在欣賞,也像是在回味黎落英的話,然后喃喃地說,可不嘛,連醫生也奇怪,它們一點也不像有病的。說完之后她抬起頭看了黎落英的乳房一眼,隨即咯咯地笑起來,邊笑邊說,其實你那也不是因為生病,是因為年齡大了,萎縮了,哈哈……
黎落英望著徐雅子那兩個嬌嫩的甚至閃著光澤的乳房,最終還是視線模糊了。
后來,徐雅子還向她談起了新上映的一部叫做《等風來》的電影,她說電影她不喜歡看,但喜歡里面的歌,并把其中的兩句歌詞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給她聽。小學文化的黎落英向來對文字遲鈍,但卻神奇地將那兩句只聽了一遍的歌詞牢牢地記在了心里——
我得到的都是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黎落英的思緒被男人突如其來的手機鈴聲打斷了,男人看了看手機屏幕,很警覺地走進洗手間里。男人的聲音忽高忽低十分錯亂,但黎落英大體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而徐雅子則保持著剛才的姿勢默默地喝湯,好像對男人的聲音充耳不聞。不出所料,男人出來后表情變得極為慌亂,也或者是焦慮甚至是恐懼。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地低聲對徐雅子說,家里有事,我得走了。
對了,近期我可能不來了,你照顧好自己。轉身的時候男人又補充了一句。
徐雅子“嗯”了一聲,繼續喝湯。但男人出門后,黎落英看到徐雅子的身體一下塌陷了下去,手里的湯都灑在了被子上。
男人一出門,黎落英像是要追趕他似的,急忙爬下床穿好鞋子,快速地出了病房。
你干嘛跟著我?在下樓梯的拐角處,男人突然停住腳步轉過身。
黎落英急忙快速地剎住腳,但由于慣性使然,她的身體還是做出了朝前沖的樣子,幾乎要撞到男人的后背了。
你不能就這么走了……黎落英忍著心里的慌亂說。
那又怎么樣?男人很不友好地反問道,還好只是不友好,并沒有其他什么。
我是說,你得再來,像以前那樣,要不你會……害了她的。黎落英慌不擇言,好在把意思都表達了出來。
男人深吸了口氣,旋即抖出一個笑臉,說,我知道你,你對她很好,她還說要認你做干媽呢,我不在的日子就請你照顧一下她吧。
可是……黎落英才說出兩個字,男人已經消失了。
黎落英突然覺得恍惚得厲害,她的身體搖晃了一下,被旁邊一個人扶住了,那人關切地問:大姐,你沒事吧?
黎落英對對方報之以感激一笑,說,我沒事。她回轉身體,朝病房走去。
再走回來,腿卻變得格外地沉,“灌了鉛”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不光是腿沉,頭也昏沉,連帶著眼神也昏昏的。樓道迎面墻上是幾個女明星裸著上身倡議保護乳房的公益海報,原本上面的人都笑翩翩的,但現在黎落英覺得她們笑得有些詭異,或者說根本不是在笑,而是在哭。
迎面走來一個護士,帶著職業的警覺性問她,黎姐你不舒服嗎?
黎落英知道一個肯定回答會帶來多大的麻煩,急忙笑著朝她搖搖頭說,沒事沒事,很正常。護士松了口氣說,你的手術安排在后天,得注意休息。黎落英急忙應了一聲。護士走了,黎落英的腦子清醒了許多,心情也松快了不少,應該與那一笑也有關系吧。
走到病房門口,黎落英的心又提了起來。她從門玻璃上朝里看了看,徐雅子正閉著眼躺在病床上,耳朵上塞著耳機,一根手指有節奏地敲打著肚子上的平板電腦。她的狀態要比自己想象的好,黎落英把提著的心放下來,推開了門。
黎落英沒有去病床,而是走到衣柜跟前,快速地換下病號服,穿好外套。盡管她把動作做得極快極輕,但在轉身的時候還是聽到了徐雅子的話。
祝你好運!徐雅子歪過頭,微笑著望著她。
黎落英心頭一熱,但她沒讓想哭的情緒醞釀成功,而是同樣微笑著望著徐雅子說,想吃啥,我給你買回來。
麻辣燙吧。徐雅子做了個鬼臉。
黎落英本想說“換一個吧,醫生不讓吃”,但想了想還是做了個“OK”的手勢說,沒問題。
4
站在醫院外面的街邊上,黎落英的大腦跟眼前熙攘的人流車流一樣,飛速地運行著,她在尋找可以道別的人。很快她就發現了,自己的人生實在過于簡單了,真正值得去道別或者說是說說心里話的人并不多,不過這樣也好,簡單、不累,人生至此,不就求它倆嗎?于是她裹緊外套,一頭鉆進了人流中。
黎落英打了一輩子工,跳了一輩子槽,要數干得最長的就是這金都賓館了,而黎落英的城市人生就是從這金都賓館開始的。當年金都賓館屬于政府招待所,來這里吃飯的都是政府機關干部。黎落英經本家親戚介紹來這里當服務員,因為長相出眾被來這里吃飯的梁金生看上了。誰(包括她自己)也沒想到在政府當秘書的大學畢業生會跟一個酒店服務員開花結果,可是人生有時候就是這么奇妙,最后她還真成了梁太太。當然結婚后梁金生就讓她辭了這份工作,還不是因為面子問題。
人生不僅奇妙,有時候還是很無情的,誰都沒想到一直順風順水正值旺年的梁金生會突然走下坡路,幾次工作變遷之后,他竟然從市政府辦公室調進了一個閑職部門,前進的仕途戛然而止。加上孩子越來越大各種開銷越來越大,日子一下拮據起來。黎落英也只好終止了在家相夫教子的安穩日子,出來找工作。因為啥也不會,她只好再次進入了賓館服務行業。而此時金都賓館已經改制成了私人企業,生意紅火,但是她不想回去,梁金生也不讓(還是因為面子問題)。好在街上賓館酒店多了起來,她就去應聘。為了日子好起來,她是抱著“另敲鑼鼓重開戲”的決心去的。結果幾年下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她竟然跳槽成了慣性(其實這也是這個行業的通病),把整個小城的賓館餐廳幾乎都干了個遍。兒子上大學那年,她(包括梁金生)終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決定去一直敬而遠之的金都酒店應聘。梁金生拉下臉皮找過去的老關系疏通了一下,她成功地進入了酒店后廚當了一名面食工。不得不說,金都酒店才是她應待的地方,她一呆就是七年。這七年來,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困難和煩惱在這里一樣也不少,但是黎落英成熟了(其實就是圓滑了),再加上骨子里對金都酒店的感情,忍一忍就都過來了。七年下來,她把酒店當成了第二個家,而酒店對她也是有感情的,住院期間,酒店領導還特意送去了花籃和慰問金,這表明她是有組織的人,這讓她著實感到了溫暖,所以她才把金都酒店當成了告別儀式的第一站。
沒錯,當黎落英站在金都酒店高聳入云的大樓前面的時候,心頭真升起一種帶著溫度的莊重感,當然其中還夾雜著無限的悲涼意,她知道這一別就永遠不會回來了。
盡管帶著口罩,門口的保安小羅一眼就認出了她,上前來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黎落英摸著小羅被寒風吹裂的手,差點掉下淚來。小羅反倒安慰起了她,說以她開朗的性格不可能得病,肯定是醫院誤診,還勸她趕快出院回來工作。
看來自己得病的事全賓館都知道了,這樣一來她反而輕松了,原本打算走后門的,她改變了決定,就在前門大廳里光明正大地走進去。于是她摘掉口罩,昂首挺胸,遇見熟人就打招呼,想跟她寒暄的就停下來多說兩句。這一路下來她驀然發現,自己在賓館里還是蠻受歡迎的,而且還頗有些地位,尤其是那些入職不久的年輕人,甚至對她點頭哈腰,這讓她身體里凝固了很久的血逐漸有了流動的感覺,等她走到后門出口的時候,她甚至都覺得后背開始冒熱氣了。
門開著,馬麗紅正背對著她揉面,雙肩一聳一聳的,不知道的還以為她在哭。黎落英這輩子遇到的對手不多,馬麗紅算一個;她打心眼里討厭(甚至說痛恨)的人也不多,馬麗紅是唯一一個。馬麗紅比她稍早一點來這里工作,跟她同一個工種——面食工,手藝跟她也不相上下,都比其他面食工強好幾倍,于是兩人的競爭就此拉開帷幕,這一爭就是七年多。七年以來一直是馬麗紅占上風,她受領導的表揚最多,出的差錯最少,也在領班的競爭中將黎落英徹底打敗,所以雖然黎落英表面對她和氣,其實心底里恨透了她。馬麗紅自然深諳此點,背后沒少對她使刀子,去領導那里告黑狀,拉攏同事孤立她。當然她黎落英也不是吃素的,散布馬麗紅(馬麗紅是離異單身)跟廚師長的緋聞、將一截紗布塞進馬麗紅負責的蒸包里等等都是她干的,看到馬麗紅為此被廚師長的老婆揪住頭發打得滿地找牙、因為顧客投訴而被扣掉了半個月的工資等等,她簡直睡覺都能笑出聲。但是馬麗紅是何等精明,她知道這都是她在背后搞鬼,卻對她更加親熱,黎落英知道她是在醞釀更大的陰謀,只是她還沒來得及施展,黎落英就住院了。
黎落英本已經下定了決心帶著善意走這一圈的,但是當看到馬麗紅背影的時候,她才發現這善意對誰都行,除了她馬麗紅。自己得病跟她馬麗紅也有關系,是她讓自己在工作中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快樂,現在她統治了整個面食部,睡覺一定會笑出聲來的。想到這里,她感覺身上的熱氣倏然消失了,恨不得撲上去朝她后背上一頓猛捶。
馬麗紅突然轉過身,呆了有那么幾秒鐘的時間,然后猛的朝黎落英撲過來,將她一把摟進懷里,頭趴在她肩上抽抽嗒嗒地哭了起來。黎落英有些發懵,她為什么這么熱情?為什么哭?之前她一直在哭還是新哭的?在接下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里,黎落英找到了答案。這幾十分鐘的時間里,馬麗紅抽抽嗒嗒說的都是以前從未對她說的話,都是只有女人(確切地說是體己人)之間才會說的話。最終她明白了馬麗紅的意思,她是說她身邊不能沒有她黎落英,她跟她爭是因為心里比她黎落英還苦,黎落英有老公孩子,生活比她幸福,她最受不了這些,所以才處處難為她的。她甚至還說得病的應該是她馬麗紅。
從金都賓館出來的時候,黎落英心里感到幾分慶幸,慶幸得病的不是馬麗紅,否則她可能早從那扇窗戶里跳下去了。同時她望著賓館直入云霄的尖頂,突然有了一種想再回來的奇妙的沖動感——
可是,我還能再回來嗎?
5
市化肥廠家屬區,這是黎落英要告別的第二站。這里已經破敗得不成樣子,泥濘的巷道,歪斜的院墻,裂紋纏身的房屋,要知道當年這里的繁華程度可是市中心都無可匹敵的。那時候化肥廠是市里的納稅大戶,養活著幾千號人,一天到晚機器轟鳴,大卡車絡繹不絕,這里有自己的商場、酒店、賓館甚至電影院和舞廳。不光這里的人,就是梁金生和他那些頭頭腦腦們也沒少來這里尋歡作樂。當年就是在黎落英的攛掇下,梁金生利用關系把她弟弟安排進了化肥廠工作,原本以為端上了鐵飯碗就一輩子無憂了,可仿佛就在一夜之間,化肥廠倒閉,弟弟下崗,一切都沒有了,連帶著整個家庭都變成了大風中的蜘蛛網搖搖欲碎。前兩天弟弟剛給她打過電話,說他老婆已經向法院提交了離婚申請書。現在黎落英都不敢來了,來一次一個樣,一次比一次不堪,她害怕有一天來了會發現這個家已經不存在了,想要在心里留個念想都不成。
但是今天不同,她是來道別的,與它在不在沒有多大關系,哪怕它人去房空或者變成一片廢墟,她只需要站在廢墟上來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就可以了。當然情況并不能惡化得那么快,衰敗歸衰敗,廢棄的廠房還在(好像還有個別車間在堅持生產),破敗的家屬區還在(即便拆除也得需要漫長的時間吧),路上還能碰到有人從某個胡同口鉆出來,甚至還有某個商販的叫賣聲從某個角落里傳出來。黎落英亂跳的心逐漸穩了下來。
走到弟弟家門口,她沒有立刻推門進去,而是先聽了聽里面的動靜。有說話聲,她暗自松了口氣,再聽,是弟媳的聲音,聽不清說什么,也沒有人回應她,像是在自言自語,但這聲音卻給了她一些底氣。推開門,看到的也是她全然沒料到的景象。
年近八旬的患了失語癥的老媽正半躺在門前被陽光覆蓋的竹椅上,雙目緊閉,一動不動,儼然一尊雕塑,當然這尊雕塑不是全然不動的,或者說是毫無生氣的,她在動,她有生氣,動的是她后面的一雙手,那生氣也與她有關系,那是弟媳正在有節奏地為老母親捶打著雙肩,那自言自語聲也是從她的唇邊發出來的,那絮絮之聲應該是在訴說某些往事,但不細聽的話倒像是在低吟淺唱……
黎落英眼窩一熱,轉身便離開了。從破敗的家屬區出來后,黎落英特的回頭看了一眼,她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話:破敗或許是一種永恒之美。她不知道這話合不合邏輯,也不知道跟徐雅子那句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6
這是一座在整個小城里數一數二的高檔小區,這是黎落英要告別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在這里有山有水有亭臺樓閣,還有什么書畫一條街、旅游紀念品一條街、小吃一條街等等,建筑都是仿古式的四合院式獨棟別墅。明明是個住宅區,卻被掛上了“3A景區”的牌子,而且還有一個很古怪的說法叫“旅游地產”。這里當時開始大興土木的時候,黎落英是嗤之以鼻的,她覺得小城就這么點人,而且大都居有定所了,這里嘩啦一下蓋了這么多房子,賣價還死貴,不賠本才怪呢。可是后來她就傻眼了,據說這里的房子還沒等開盤就被瘋搶一空。當時梁金生還懟她:你覺得都像你一樣沒錢?
黎落英沒把這話往心里去,有錢沒錢的這些年不都一樣過來了?更何況自己家又不是沒房子住,那些別墅再好跟自己也沒關系。可她萬萬沒想到,自己有一天還真跟這里扯上了關系,而且還成了她一塊天大的心病,確切地說,她生病的根兒就在這里呢,因為這里住著她的親家。
她的男親家是小城里響當當的人物,當年也曾跟梁金生一樣在政府機關上班,后來辭職下海。接下來他的履歷跟那個年代所有辭職下海的人差不多,搏擊風浪勇立潮頭,賺了個盆滿鍋滿,據說這個旅游地產項目就有他的股份。雖然同居一城,但是對黎落英和梁金生來說親家都是遙不可及的人物,他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會跟他攀上親戚,直到有一天上大學的兒子領著親家的女兒進了門,他們才知道,原來兩個人從高中時候就談起了戀愛,而且兩人都已經下定了非對方不娶不嫁的決心。
黎落英和梁金生自然沒意見,他們是怕人家姑娘家有意見。好在兒子與姑娘郎才女貌蠻般配,親家滿意。兒子與姑娘大學畢業后雙雙進了親家的公司上班,然后是結婚生子,一切順風順水。等到一切塵埃落定后,黎落英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足以懊悔終生的錯誤。
兒子結婚對方沒要房子,反而送了一套,她暗暗松了口氣,并不禁有些沾沾自喜,覺得自己終究沒成勞碌命,結果發現便宜了一套房子卻把兒子搭進去了。兒子一家跟親家樓前樓后地住著,結婚之后就很少回家來了,來一趟就像串門,放下東西就走,而自己去一趟兒子家更像是走親戚,站不是坐也不是。尤其是有了孫子之后,姥姥姥爺圍著轉,自己成了局外人,橫豎插不上手了。孫子著實可愛,可就是不跟自己親,來家一趟不是嫌臟就是嫌冷嫌熱吵著要走,黎落英的病就是在這個時候坐下的。突然感覺整個世界啥都不是自己的,未來還看不到希望,整天郁郁寡歡,能不得病嗎?
等站在兒子家門前的時候,黎落英想好了,啥也不說,就是看看孫子,看完了就走,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可沒想到的是,兒子家沒人。她只好硬著頭皮去親家家里,結果也大門緊鎖。立在地上,抬頭看著遠處即將垂落的太陽,她竟一時沒了主意。沒有人,那這個別怎么道呢?她有些計劃被打亂的無措感,但也沒有辦法,那就只好先把那件事往后拖一拖了。她臨時決定回家一趟,有了這個想法后她倒有些自責起來:再怎么說,那里可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地方,道別的話也得有它一份吧?
7
黎落英萬萬沒想到,家里竟然四敞大開熱熱鬧鬧地搞裝修。一開始黎落英以為自己走錯了,可怎么會錯呢?這扇門她合著眼都能摸進來。更讓她感覺不可思議的是,裝修工人不是別人,而是兒子媳婦和親家兩口子。他們全副武裝忙得不亦樂乎。
你們……這是在干嘛?黎落英有些恍惚,她不確定這是不是跟自己的病情有關系。
兒子從凳子上跳下來,撕下口罩,先給黎落英一個大擁抱,接著問道,媽您怎么回來了?我爸呢?
快說,你們在干嘛?黎落英有些怒不可遏,他們四個人都在笑,她感覺自己是他們原來的一塊笑料。
兒子止住笑,深吸了口氣說,既然您看到了,我們就不瞞您了,我們想把家里好好收拾一下,讓它來個大變樣,等你出院后給你來個大驚喜,這可是醫生幫我們出的主意呢。而且醫生還說了,裝修工不能請別人,要我們親自動手……
你爸知道嗎?黎落英打斷兒子的話,不等兒子回答,她自言自語地說,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保密工作竟做得這么好,可真夠狡猾的……
從家里出來,走下那段雨雪天經常讓她摔跤的下坡道,黎落英突然捂住肚子,扯開嗓子大笑起來。
8
醫院里完全一副如常的模樣,匆忙的醫護人員,沉默的病人,內心焦灼但盡力克制的病人家屬,以及淡粉色的主色調和空氣里彌漫的淡淡的消毒水味道,總之沒有什么反常。但一路走著的時候,黎落英卻產生了一種陌生甚至奇特的感覺——感覺自己不是這里的病人,而是一個來探望病人的家屬,只需稍待片刻就會離開,她手里提著的麻辣燙飯盒似乎更加證明了這一點。要知道以前她可從來沒這種感覺,她甚至一度因為遙遙無期的出院時間而放棄了離開的打算。
黎落英推開病房門,眼前的情景著實把她嚇了一跳:徐雅子正站在窗戶跟前,半個身體探出了窗外。黎落英把手里的麻辣燙丟在地上,尖叫一聲沖了上去,一把抱住徐雅子,跟她一起滾到了地上。黎落英大口喘著粗氣,徐雅子的身體在她懷里微微地抖動著,但她嘴里卻發出一串尖細而瑣碎的笑聲……
這時候梁金生端著飯盒走進來,看到地上的兩人大吃一驚:你們咋了這是?
徐雅子止住笑,捂著肚子說,她以為我要從那里跳下去呢!
一聽這話梁金生咧嘴笑了,說,那怎么可能?剛才我們聊了半天,開心得很,雅子說了,從今天開始就認你當干媽,認我當干爸,我們有了個女兒,高興嗎?
這還用說!黎落英一把把徐雅子摟進了懷里,又嘆了口氣說,只是那麻辣燙吃不了了,媽再去給你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