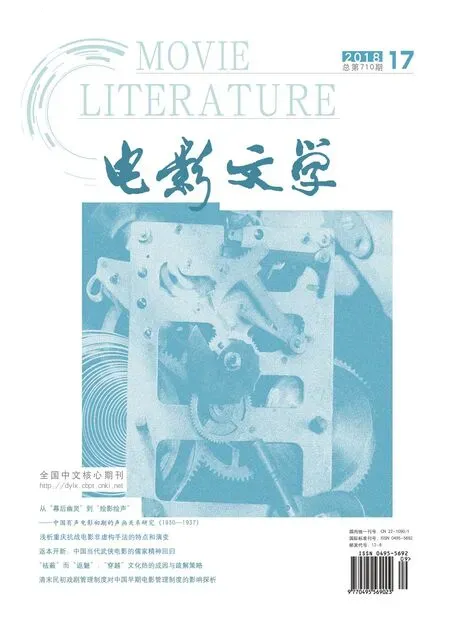女性主義批判視野下的印度女性電影
段善策 劉憶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中韓新媒體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女性主義理論
女性主義(Feminism)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紀的法國,又稱女權主義、婦女解放、性別平權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和社會實踐,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興起。其基本觀點認為現代社會史建立在以男性為核心的父權(patriarchal)體系之上。女性主義者因此相信,必須從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權力關系與性意識(gender conscious)的角度剖析男女不等的社會實質。在視覺藝術(visual arts)領域,女性主義關注女性被呈現(representation)的方式及其意涵。70年代這股風潮也波及男性占主導的電影工業(yè)領域。女性主義批評家開始關注銀幕上的女性形象塑造,揭示影像中包裝男尊女卑觀念的語言、符號及其運作機制。莫莉·海絲克(Molly Haskell)在1974年就指出好萊塢電影習慣把女性刻畫成男性欲望投射的對象。翌年,受波伏娃的女權主義開山之作《第二性》的啟發(fā),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中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揭示主流電影菲勒斯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的敘事無意識。在她看來,女性角色作為“他者”(other)臣服于帶有欲望和控制意味的男性的凝視(gaze)之下,從而滿足觀眾潛在的窺視欲念(voyeuristic phantasy)。而影院獨特的觀看環(huán)境更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窺視快感。穆爾維的研究揭示了女性刻板印象形成背后的社會心理結構,即整個社會都浸淫在潛意識父權意識形態(tài)的氛圍之中。世界電影批評由此進入后結構主義階段,《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也奠定了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經典范式。
二、“印度電影熱”背后的性別癥候
近年的中國電影市場掀起了一股印度電影熱潮。《摔跤吧!爸爸》更以近13億票房位列2017年度票房第七,甚至超過了馮小剛的《芳華》和約翰尼·德普的《加勒比海盜5》,風頭一時無二,堪稱當年票房的最大黑馬。影片中所反映出來的印度農村的女性歧視問題也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2018年上映的《神秘巨星》《蘿莉與猴神大叔》同樣是以女性為主角的社會問題片。在女性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的輿論語境中,這類主打女性話題的商業(yè)電影自然受到主流文化的青睞和追捧。盡管如此,嚴格來說這類影片并不能被稱之為女性主義電影;相反,女性、女性主義是被當作故事賣點(淚點)來設計的。尤其是雷同的勵志橋段,對于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而言,無疑是一種打雞血式的人權宣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主義”標簽使得這類電影成為流行文化的硬通貨,但寶萊塢電影工業(yè)本質上仍然受男權話語宰制。譬如,《摔跤吧!爸爸》中的女主角即便被很多人認為是印度新女性的代言人,但實際上她是在由印度男星阿米爾汗飾演的冠軍父親的影響和教導下才取得成功的。這位擅于創(chuàng)造奇跡的父親同時還是女兒的精神導師和專業(yè)教練。在這些電影里,與其說彰顯了女性的主體性和自由意志,毋寧說再一次論證了女性是等待救贖的客體的合理性。
在印度,女性地位低下是難以回避的社會沉疴。湯森路透基金會的新聞機構TrustLaw的數據顯示,在全球100多個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印度婦女的待遇排名倒數第一。極不友好的性/別(sex/gender)環(huán)境不但成為印度女性自我發(fā)展的最大障礙,而且成為印度民主政治和現代化進程的一大掣肘。《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曾評價“印度向來自詡為民主國家,也曾一度被美國譽為民主制度的典范。但是民主并未改善印度女性的生存現狀”。印度導演馬尼什·賈(Manish Jha)執(zhí)導的《沒有女人的國家》揭露了重男輕女思想在印度農村的流行,導致童婚、強奸、亂倫現象泛濫的殘酷現狀,震驚世界。印度當代最重要的女性電影導演蒂帕·梅塔(Deepa Mehta)在其著名的《水》《火》《土》三部曲中對印度底層女性的命運投以深刻關注。“‘阿普三部曲’里展示的生活方式多少年來不曾改變,這才是印度社會的現實。”印度電影教母米拉·奈爾(Mira Nair)執(zhí)導的撕破印度中產階級的家庭神話的《季風婚宴》,斬獲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導演本人也由此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印度女性導演。盡管如此,女性電影的命運正如其展現對象的遭遇,時常受到來自審查制度和傳統觀念的壓制和非議。
三、印度女性電影的創(chuàng)作景觀
(一)“他者同情”:男性導演的聲援
印度電影的歷史大部分是由男性書寫,女性題材也是如此。當代印度社會,隨著女性職業(yè)群體逐步增多,穩(wěn)定的收入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使得女性成為大眾藝術、文娛產品的主要消費對象。女性電影的創(chuàng)作也在市場的需求下迅速繁榮,《印式英語》《靈魂拳擊手》等“女人戲”紛紛出爐。印度女性電影可以分為男性導演的“他者同情”和女性導演的“自我控訴”兩類。其中,前者又包括寶萊塢商業(yè)大片中的偽女權電影,以及相對客觀地反映女性困境的社會問題片兩種。偽女權電影譬如《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寶萊塢生死戀》等。這類貼著人文關懷標簽的故事,充斥販賣溫情、賺取眼淚的煽情情節(jié),以此滿足中產階級觀眾虛偽廉價的道德優(yōu)越感。
盡管社會問題片仍然從男性視角出發(fā),但一改偽女權電影占領道德制高點的粗魯和傲慢,敘事立場和態(tài)度相對客觀公正得多。這類影片中,除了前文提及的《沒有女人的國家》這種嚴厲抨擊重男輕女思想愚昧、野蠻的控訴題材,還有一些與商業(yè)元素結合,側重于表現女性在生理心理方面與男性的不同之處。譬如《女皇》,這部由男性導演執(zhí)導的影片是少數獲得印度倡導女權者認可的作品之一。一方面,導演在人設上給予女主角足夠的理解和同情,人物的性格弧光比較完整;另一方面,導演也沒有將男性角色設定為“救贖”的主體,相反,主要男性角色是以相對負面的形象示人。類似的作品有《無女之土》《情系板球》《粉紅幫》等。
(二)“自我書寫”:女性導演的控訴
“他者同情”畢竟只是隔靴搔癢,女性導演的“自我書寫”才是印度女性心聲的代言人。在復雜的政治宗教語境下,印度女性影人一直不懈地為爭取平等獨立的地位而努力,電影成為她們?yōu)槿后w發(fā)聲的有力工具。米拉·奈爾憑借《你好,孟買》獲得198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這是印度影史上首位獲得成功的女性導演,標志著寶萊塢電影“女性主義”的覺醒。2000年,米拉·奈爾大膽顛覆寶萊塢保守的家庭觀念拍攝了家庭倫理片《季風婚宴》,一舉奪得第58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新概念電影由此而生,如今我們所見到的印度女性導演拍攝的電影大多傳承其衣缽。有別于男性視野中的刻板印象,女性導演鏡頭下的印度女性呈現出更加多元復雜的性別建構,既有傳統犧牲型,如《三十六歲正美麗》;也有覺醒受難型,如《三十六條路》《15號林蔭路》《月亮河》;還有獨立解放型,如《火》《肉體深處》《炙熱》等。雖然這類電影屢遭封殺,票房也不如男星主演的商業(yè)動作片賣座,但女性導演所宣揚的這股“解放風潮”愈演愈烈,近幾年眾多呼吁女性站起來的電影也開始走向世界。
(三)“夾縫中生存”:逼仄的話語空間
在印度,女性電影的話語空間可以用“夾縫中生存”來形容,其中,蒂帕·梅塔的遭遇頗具代表性。她導演的“元素三部曲”——《火》《土》《水》的命運可謂是一波三折。1988年《火》甫一上映便引發(fā)社會騷亂。影片中導演用很多象征隱喻手法表達自己對于印度社會種種剝削女性的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態(tài)度。女主角的姓名就影射了導演對種姓制度的強烈抨擊。“火”在印度神話中象征著管理女性分娩和主持家庭的神,女主逃離時打翻火爐影射神話故事里“席達以火試身”的場景。片尾的取景被導演別出心裁設置在三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融合的蘇菲圣地,寄寓著印度各派宗教團體應該拋開成見、團結一心的導演愿望。導演借助該片揭露印度婚姻制度上對女性的種種禁錮和陋習,呼吁政府和社會能正視這一切。同時,女性有權利自主選擇,決定伴侶的性別,擁有受教育權和就業(yè)權。因此,她的這部電影既批判了印度教對女性的剝削,也表達出對男權社會強烈的不滿和憤怒。
該片第一次播出后,受到印度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嚴重抵制,導致該片在政府禁播10年后到1998年才得以順利播出,然而片中象征婆羅門的女主名字卻因不能一統民心被改。然而同年12月,這部影片卻引發(fā)了印度一系列的社會中暴動和政治問題。濕婆軍攻打影院,民族恐怖分子突襲影院觀眾,電影被撤回重審。蒂帕·梅塔導演聯合眾多寶萊塢明星和大牌制片人請愿法院,請愿持續(xù)了兩年。無獨有偶,“元素三部曲”的另外兩部也經歷了類似的遭遇。導演及其團隊因作品題材涉及批判宗教及其對女性的壓迫,導致劇組不斷被騷擾、突襲,前后拍了五年才殺青。這樣的例子在印度女性題材創(chuàng)作中習以為常,那些試圖打破傳統壁壘的女性導演不得不面臨牢獄、官司、威脅、暗殺的危險,但是她們仍然沒有放棄為印度女性發(fā)聲的努力。可以看到,男性在目前的印度電影工業(yè)體系中依然占據支配地位,盡管業(yè)界也涌現出了不少優(yōu)秀的女性導演,但是整體而言,銀幕內外的性別平等之路仍然任重而道遠。
四、印度女性電影的藝術價值
無處不在的男權意識形態(tài)下,印度主流電影里的女性主要負責制造勞拉穆爾維所謂的“色情快感”。作為一種“性符號”,女性的價值來源于其美貌、身材以及對男性絕對的服從。女性無法在敘事結構中“敘述”真正屬于自己的故事和觀點。印度女性電影試圖通過鏡頭位置的反轉向這種局面宣戰(zhàn)——女性由被凝視的“客體”變成具有獨立人格和自我意識的主體,從而令影像文本形式拋開“為男人創(chuàng)作”的定式。靈活多變的女性敘事手法和故事呈現也給予了女主極大的自由表現空間。女性電影豐富和革新了印度電影語言,拓展了鏡頭的關注視野,提升了影像的藝術價值。
在全球化語境下,女性電影在印度電影對外展示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成為一張名片。女性導演在歌舞、婚宴、傳統宗教等元素的鑲嵌中巧妙地把創(chuàng)作扎根于全球化語境,在汲取女性視角敘事策略時又堅守現實主義風格,在群組式人物影像中又展現印度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鏡頭語言如探世百態(tài)的萬花筒一般融合了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并在學習世界影像表達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女性敘事的典范。通過印度女性電影這扇窗口,全球觀眾看到了一個各方面都富含“混雜性”的真實印度。
注釋:
① 票房數據來源藝恩電影智庫,http://www.cbooo.cn/year?year=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