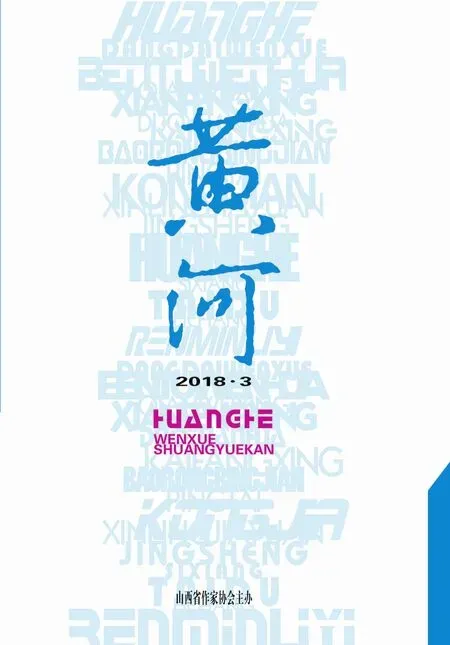西歐往西
賈耀中
一、隔壁老王王爾德
有些事情的是與非,罪與非罪,根本不在事情本身。百年前王爾德在浪漫多情的巴黎公開宣稱自己已經(jīng)出柜時,立刻從眾人仰望的星空垂直落地,摔成狗屎。其實王爾德還是王爾德,這攔不住一個個高尚的人們掩鼻而過,走遠了扭頭再吐口唾沫。就像我小時候教室里誰放了屁一樣,明明有響無臭,無辜的小女生們個個掩了嘴鼻,裝出與屁不伍呆萌純潔的可愛模樣,這與政客們無意歸了一類。
百年后,自己祖國愛爾蘭的女總理領著同性伴侶四處風光,這個反差叫冤死的王爾德不知是該生一生氣,還是高一高興?三言兩語焉能說清,王爾德索性從躺了百年的棺材里坐起來,大聲宣講自己對同性戀的看法:同性也罷,異性也罷,人類的性趣只在兩個人的歡愉,豈可囿于性別乎?又豈可以多數(shù)人的聲勢浩大而詆毀少數(shù),踐踏平等乎?當然,激動之后,他也會與他的崇拜者繼續(xù)探討他那些偉大的戲劇作品里深刻的人生況味。或者講講童話,比如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快樂王子》,因為小王子的命運和他的命運確有相似的悲劇性,最后都是從高位上轟然倒塌。
我說的棺材里的情景,是巴黎人別出心裁給王爾德雕刻的塑像,然后給人的鮮明想象。
這種有趣調(diào)侃的雕塑在他的家鄉(xiāng)都柏林也有一處,就在他家門前的梅里昂公園。那王爾德且是風華正茂,事業(yè)和人生處在頂峰,他八叉著一雙長腿,懶洋洋地斜躺在一塊巨石之上,綠上衣,花點黑褲,斜嘴浮眼,毫不掩飾自己的自浮自夸與不屑之相。他不屑路人旅人?還是他眼前的另外兩座小雕塑?左側(cè)的那個斷臂之人,據(jù)說是指向他的雙性戀身份,他當然不屑。那么右側(cè)的那位挺著大肚,全身赤裸,神情憂郁的年輕婦女呢,她的所以憂郁與他的所以不屑,又是為何?因為不懂像座上的英文,更無知情的本地人指點,它成了我一路捉摸不透的謎團。
后來搞明白的譯文如下:
只有無聊的人才能把早餐吃出花樣來
大多數(shù)人都是別人
每當人們贊同我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肯定哪兒錯了
教養(yǎng)良好的人處處和他人過不去,
智慧的人處處和自己過不去
沒有什么事比輕率更天真的了
一個憤世嫉俗的人,
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而不知它的價值
生活不復雜,我們復雜。生活很簡單,
簡單的事情就是正確的事情
這是兩面碑座上的譯文,還有四句看不清,都是王爾德戲劇里的經(jīng)典臺詞。可那個漂亮的年輕女人是誰?她懷著誰的孩子?她為什么在試圖扭后頭去看一下后面的那個人時滿臉的憂傷?
碑的第三個面上也有文字,沒有拍下來。我想它的文字應該是這樣的:瞧!我背后的那位,就是隔壁老王。
二、士兵,你翻翻身!
帕特里克島上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是愛爾蘭和都柏靈的靈魂。嗡嗡的管風琴發(fā)出渾厚的樂音,從教堂的每一個窗口溢出,安撫著每一顆虔誠的心。柔和的燭光,優(yōu)美深隧的券頂,唱詩班深情的和聲,讓懺悔和禱告無比神圣。數(shù)百年來,這里一直為禱告者敞開大門。這里是愛爾蘭歷史的縮影,寫滿最激勵人心的故事。人們通過每日禮拜和誦唱,表達著對神靈的尊崇與敬畏。
是哪些最激勵人心的故事?
是帕特里克因為在附近的一口古井洗禮而轉(zhuǎn)變皈依于耶穌基督,由此使愛爾蘭成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是自1191年圣帕特里克教堂建成以來,音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由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和基督大教堂唱詩班參加了著名的清唱劇《彌賽亞》的首演?是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最著名的大主教斯威夫特寫下的傳世名著《格列佛游記》?
當然是的。
還有2014年,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百周年,教堂里樹起一棵紀念樹,光禿禿的樹干寓意戰(zhàn)爭摧毀一切。游客可以在樹旁留言,寄語戰(zhàn)爭受害者。
在教堂的一角,懸掛著十多面有點破爛的米字旗。教堂的訪客指南上寫道:“此處展示的旗幟是為了紀念前英國陸軍愛爾蘭軍團。這些團旗隨著時間的逝去而慢慢褪色,默默緬懷著所有曾在旗下浴血奮戰(zhàn)的將士們。士兵不死,只是悄然隱去。”
不止這一處。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最高處,矗立著一座城堡,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城堡的一所石頭房子,盛放著幾十本厚重的書,書里一行一行,密密麻麻記載著歷史上隨日不落帝國四處征戰(zhàn)的戰(zhàn)死者將士名單,姓名,籍貫,及戰(zhàn)死之地。他們介紹:蘇格蘭士兵天性彪悍勇敢,一貫擔任英軍先鋒部隊的角色,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這些英勇的蘇格蘭將士,就像帕特里克教堂里的將士一樣,沒有死亡,只是悄然隱去。是的,他們真誠地想,士兵不死,只是悄然隱去,或隱于教堂,或隱于書冊,神圣而且安祥。
佛教反對以任何名義殺生。基督教反對殺戮,但是鼓勵反抗。
真正的反抗,為自由,為平等,士兵倒下了,卻在后來者的心中悄然永駐。
前英國陸軍愛爾蘭軍團的將士們,彪悍的蘇格蘭將士們,你們,是這樣的嗎?
這個屬于英國的愛爾蘭軍團,成立于1801年—1921年間,長達120年。這是大不列顛海陸軍團東征西伐,在全世界四處侵略殖民的百多年,也正是日不落帝國如日中天的百多年。英國人無比自豪的維多利亞時代,就屬于這百多年之中 (香港至今還有維多利亞灣)。他們打贏了一個又一個殖民戰(zhàn)役,比如,1840年對華的那次,1856年的又一次,他們叫兩次中英戰(zhàn)爭,我們叫兩次鴉片戰(zhàn)爭。就是從這兩場戰(zhàn)爭開始,中國人從此成為東亞病夫,中國因此失去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充滿恥辱的泥灘。這兩場戰(zhàn)爭,可愛的愛爾蘭軍團,沖鋒陷陣的蘇格蘭將士,你們,參加了嗎?
或者你們也許沒參加,那么,對澳洲土著,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殺戮,美國獨立戰(zhàn)爭,印度抵抗運動,也沒有參加嗎?
士兵!此刻有一個中國人就站在你面前。你翻翻身!因為,你實在無法永遠悄然下去,安心隱去,不管是在神圣的教堂,還是在城堡里的書冊。
我想,哪怕是中國,真正的英雄,只能是自由的戰(zhàn)士,而絕不應成為自己和別國歷史上人民的敵人。
三、黑啤泡在音樂里
黑啤與音樂,愛爾蘭有這兩樣就夠了。愛爾蘭凱爾特人的祖先老早就喜歡在歐陸上四處游蕩。兩千多年來,他們沿著萊茵河,阿爾卑斯山,也沿著歐洲大陸的西海岸,一路與人打著架,仗著勇武好斗的脾性,搶了不少地盤。
向西渡過英吉利海峽,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就是他們的了。再向西渡過圣喬治海峽,愛爾蘭也是他們的了。天空泡在云朵里,云朵泡在雨水里,沒有暴雨,沒有狂風,沒有酷暑與嚴寒,小雨絲天天都在下,平緩起伏的大地鋪滿三葉草和鼠尾草,碧綠而柔軟。當他們登上愛爾蘭島的時候,彪悍粗獷的凱爾特人,放下了高亢的甚至帶著血醒味的風笛,抱起像三葉草一樣柔軟的豎琴,游唱在廣闊的愛爾蘭草原上:
哦,當琴聲呼喚
幽谷成排
當夏日已盡,玫瑰難懷。你
你天涯遠引,而我
在此長埋
當草原盡夏,當雪地
長白,任睛空萬里
任四處陰霾。哦!
我如此愛你,等你徘徊
哦!說你愛我,你將前來
縱逝者如斯,死者初裁
在荒墳冢上
請把我找到,找到
尋我遺骸
你俯身向前
訴說情愛
愛爾蘭人的血液,從此就這樣深情地隨著音樂流淌。二百五十年前,GDS,也就是健力士黑啤成立的時候,公司選擇了豎琴作為黑啤的廠標,讓酒精泡在音樂里。七十年前,當愛爾蘭宣布獨立的時候,也選擇了豎琴作為國徽,讓整個國家泡在音樂里。全世界的啤酒泡沫向上膨脹的時候,唯獨GDS黑啤,那層細細的奶油似的泡沫,像瀑布,沿著酒杯的內(nèi)壁,曲曲繞繞,向下涌落,就像優(yōu)美的音樂,永遠向里,向著內(nèi)心,滲入。
GDS公司真是具有一種音樂一樣的氣質(zhì)。音樂是自由的,就像人的天性渴望自由一樣。有些地方的人不怎么自由的時候,這個地方的音樂也常常會被綁架,做無病而吟無心而頌的事情。但在愛爾蘭,在GDS公司,自由已深入骨髓,無人能改變。世界各國的游人旅人商人政界領袖前來參觀黑啤奇妙的生產(chǎn)過程的時候,所有的圖像只有公司二百五十年來工人們的歷史,種植大麥和啤酒花的農(nóng)民們的歷史,沒有總統(tǒng),主席,總理,首相,沒有尊貴的女王,沒有明星,當然也沒有激動的心情和熱烈的掌聲。一種人不需要另一種人的光環(huán)來照耀,人人都是自已的太陽。這是一個企業(yè),一個社會,一杯黑啤和一部音樂應有的環(huán)境。
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夜晚因為GDS黑啤和音樂,變得如此美妙。似乎每個人都會歌唱,每個人都會操弄一件樂器。在利菲河畔的酒吧里,人們飲著黑啤,操一件提琴,黑管,圓號,當然還有豎琴,湊成一支樂隊,演奏巴赫,舒伯特,貝多芬。黑啤讓每一個毛孔膨脹,音樂讓每一個毛孔收縮。就像墨西哥灣曖流和拉布拉多寒流在北大西洋交匯踫撞,海面霧生云騰,飄啊飄啊,從洋面到歐陸,細雨紛紛,碧綠漫浸,是綢巾掠過,妙手撫過,不覺間,身體與心靈一起寧靜,那是凱爾特人叮鈴鈴的一串豎琴。
四、想起了可憐的司馬遷
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老城帶給人的震撼撲面而來。根本無法想象一條街,一座城竟然幾百年來原封未動,根本無法想象所有成排的樓房與所有高聳入云的教堂全部是石頭建筑,根本無法想象石頭外墻由歲月的包漿給人的歷史厚重與滄桑質(zhì)感,早已勝過所有的現(xiàn)代設計和美學裝飾。一件古董不可能有這么大,可它就是古董。現(xiàn)實世界不可能這么魔幻,可它就是魔幻。
古城在西面的一處高地,最高處的城堡,是最早的“愛丁堡”。在高地之下的東邊,還是古城。未曾俯瞰時,遠遠望見東邊一座教堂的尖頂,黑黢黢的,鏤空,拿大朵的白云做背景,構成漂亮的剪影。站在城堡俯瞰,才發(fā)覺整座教堂全部呈現(xiàn)黑色,在一片乳黃的石頭建筑群中,醒目,巍峨,玲瓏。等我們趕到教堂下面仰望,才知道“教堂”不是教堂,而是一座歌特式的,全部用黑色火山巖建成的紀念碑。
紀念碑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紀念碑的主角叫司各特。司各特以蘇格蘭,英格蘭和整個歐洲為背景,寫下二十多部歷史小說,成為整個蘇格蘭引以為豪的文學與歷史巨匠。他是蘇格蘭的司馬遷。二百多年前,司各特逝世后,蘇格蘭人給自己的司馬遷修建了這座堪比教堂的紀念碑。紀念碑的正中,是寬袍大袖仍在思考的司各特雕像。
歐州不缺紀念碑,更不缺雕像,可是做成司各特這樣高聳入云的紀念碑式的雕像,卻是獨一無二的。
這是愛丁堡的又一種震撼。無異,它給了文學家史學家乃至所有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一種崇高的地位!
就文學與史學成果來講,我根本沒有能力讓司馬遷與司各特做個比較,但至少在中國,司馬遷是非常偉大的。
可是,司馬遷的雕像在哪里?司馬遷的老家陜西韓城,有一座司馬遷公園,那里有司馬遷的生平介紹,十二本紀園,也有司馬遷的全身雕像:手捧一卷竹簡,正在凝眸眺望……
這是韓城新修的四星級景點,門票費八十元。什么味道?
偉大的司馬遷,你為何凝眸?在眺望什么?
莫非,是我手中的八十元錢?
因為司馬遷還可以賺錢,韓城的司馬遷像塑起來了。另一些地方,文化名人們也是一個賽著一個被打扮得金光燦燦,司馬光,吳承恩,曹雪芹,乃至潘金蓮,西門慶的雕像,紛紛塑了起來。
文化什么時候無關于精神,更無關于靈魂?人們拜孔子,其為升學,拜菩薩,其為消災降福,拜一個又一個的神靈,關公,老子,扶蘇,蒙恬,介子推,給我兒子,給我官,給我升學高中,給我錢,給我消災免難,就像在市場上一樣討價還價,爺呀,香表布施我可全給你了,我的心愿爺可千萬千萬幫我圓呀……
這也是一種震撼。不是因為偉大,而是因為可憐。
五、詩人之傷
以牛頓和霍金作為標桿的劍橋大學,能有一塊刻有徐志摩詩句的碑石,足見徐志摩非同一般。
《再別康橋》是中國人至今普遍喜歡的為數(shù)不多的現(xiàn)代詩之一,淡淡的哀怨,回憶,離愁和美好傷感的意境,正可以搔著少男少女的癢處,留下深不可忘的記憶。
于是在英國能夠停留幾日的中國人,年輕的和曾經(jīng)年輕過的,都多多少少有想去劍橋的欲望,在那所大學城里,目睹一下那條有著金柳和青荇,彩虹和星輝,揉碎了的柔波和夏蟲般的康橋的康河。那天下午,撐著長篙的木船在水里劃行。不是傍晚,沒有夕照,不是晚上,沒有星輝。卻可以在五六座形態(tài)各異的古橋中間,準確地找到康橋。“康橋!”撐篙的白人學生像每個一說漢語就舌頭短的外國人一樣,含渾地又給眾人一個提醒:“徐志摩!”人們有點神往,仰著頭,從石砌的拱橋下,徐志摩的康橋下,悠然穿過。
康橋是劍橋的別稱,并不是一座橋。既然人們在心目中把它想象成一座橋,劍橋也索性將錯就錯,把徐志摩就讀的國王學院旁邊的這座石橋,稱做康橋。
回到岸上,循著八百多年前的古道,穿過國王學院,找到了那塊石碑。不到一米高的石頭給削了一面,安放在康橋一側(cè)的草地上,刻著《再別康橋》的首尾兩句: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云彩
這是徐志摩一九二八年一生中第三次來到劍橋后,回國寫下的詩句。一九二八年的徐志摩,當初留學英國給予他的民主理想,已被現(xiàn)實打磨得不甚清晰了。自己居住的那塊古老土地對民主與自由的消蝕,其實比他想象的要強大許多。他的哀傷與離愁,更多是理想的不再那么翹首可期,形象具體。一九二二年他第一次告別康橋,寫下了《康橋再會吧》,充滿澎湃的激情。僅僅隔了六年,澎湃的激情悄然化作無奈的凄婉。真是沒有耐心,軍閥們混戰(zhàn)著,混戰(zhàn)著,總有打不下去的一天,總得有人站出來,以鮮血和累累白骨的名義,以監(jiān)獄和無休止的控制的名義,說自由!自由!好多人沒有堅持下來。有人堅持了,卻是個幌子。你也完全可以以自由的名義招賢納士招污納垢,反正說得好聽一點就行了。以后怎樣那是以后,以后也可以說是說,做是做。他一個詩人,不過才三十來歲,哪能懂得這些。
與他寫作時的心緒相反,多少年后追慕他的國人,卻把詩的主題與意境,一門心思放在他與林徽因美好卻失敗了的愛情之上。比之于一撥一撥后來者嘻鬧無聊的八卦,徐志摩能夠輕輕地來,悄悄地去,他還是一個遠較后人更為清醒的人。一個詩人。
六、你殺人的姿勢太美了
我出門去找昨晚路過的約克大教堂,頂多一二里的距離,回時卻怎么也找不見剛剛離開的酒店。人真是笨。然而每天從我的家鄉(xiāng),從八九千公里之外,我所在讀書會的書友,卻準確地把朗讀《白鹿原》的聲音,送入我的耳中。那么遠,穿過那么多的山,海,高原,河谷,那么多國家,繞過那么多不相干的白人黑人波斯人印度人,然后一絲不差,送入我的耳孔。太奇妙了!
我聽見小娥說,大呀……我知道小娥的后背,正在汩汩流血……
在大英博物館,有幾組展示戰(zhàn)爭場面的古希臘浮雕,壯士的劍高高舉起,竟然向一位線條渾圓臉孔漂亮的女士砍去……耳邊又響起那悲涼的一聲:大呀……仿佛大英博物館多了一孔來自陜西的窯洞。
在白鹿村東頭的那孔窯洞里,鹿三乘著夜色鉆進被他從家里趕走的兒媳的家里。兒媳婦小娥光溜溜的,他肯定一輩子也沒見過這么震人魂魄的身體和白凈的膚色。他讓她爬到炕上去,趁她低頭的空隙,無法直視他的空隙,舉起屠刀,善良耿直的鹿三,實施了一次卑怯的暗殺。小娥沒有喊疼。小娥扭過頭說:大呀……
世上所有的迷惑不解,就在這一聲悲涼的嘆息里。
眼前也在殺人。希臘的雕塑,英勇的武士們骨骼隱隱,腹部緊繃,胸肌突起,騎馬的和投槍的,持盾的和揮劍的,所有的姿勢都協(xié)調(diào)、有力、健美。武士殺向武士,武士殺向女士。女士哪怕已然倒下,神情卻坦然剛毅,沒有悲涼,沒有對戰(zhàn)爭的詛咒,似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情不自禁地暗暗贊許:你這殺人的姿勢也太美了!
戰(zhàn)爭無論多么殘酷血腥,那悲壯的場面始終充滿詩情畫意,充溢對男性陽剛之美無節(jié)制的渲染與對女性溫柔敦厚含蓄之美的深情崇尚。這是古希臘在其《荷馬詩史》中貫穿始終的審美意趣。為領土而戰(zhàn),為財富和女人而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體驗崇高和悲壯的美感。那位阿喀琉斯,就是腳后跟一刺就會流血至死的那位英雄,就沉迷于此。他拒絕了可以安居樂業(yè),可期高壽的人生,情愿選擇這種血腥的,注定是英年早逝的道路。個人的無上榮光高于生命,酒神般的狂歡高于寧靜。殺戮便是殺戮,無須鹿三似的,隱蔽的,躡手躡腳的,壓低了頭顱毫無美感的卑怯。
真想問問鹿三:即使小娥該殺,你為何不能白天去殺,明明白白去殺,磊磊落落去殺,姿態(tài)昂揚去殺,非要趁夜去暗殺?
恐怕不能。妻子肯定不會同意,東家也就是族長肯定也不會同意,鹿子霖起碼在表面上也不會同意。別人的不同意就是你的不同意,你只是宗法社會里,一顆嵌在別人墻上的石子,作為個人,你經(jīng)常什么也不是。既然不能自我張揚,只好壓抑,只好逼仄。
古希臘的審美是個性的,以個人利益為上,以冒險為榮。沒有比戰(zhàn)爭更冒險的了。于是戰(zhàn)爭也就崇高起來,描繪戰(zhàn)爭的雕塑充滿美感。極致的審美導致極致的放縱,最終走向自私與殘酷。英國和老歐洲的對外擴張,不可避免會受到這種戰(zhàn)爭美學的影響。可否調(diào)過頭來面向東方,和含蓄內(nèi)斂、文質(zhì)彬彬的中國作個比較?不僅僅只有鹿三,只要對人性的打壓對思想的禁錮還不是那么張狂,束縛與懦弱之外,戰(zhàn)爭之外,別一份人性的光輝要遠比希臘美學漂亮許多。
比如唐:岑夫子,丹丘生,將近酒,杯莫停……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不也暢快?
比如宋: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何等暢快!
七、英國這個老地主
英國老了,是說英國這個地主老了,老地主了。
畢竟是地主,底子還很厚實。從曼徹斯特到貝爾法斯特,到愛丁堡,到約克,到倫敦,分不清哪座房子是富人,哪座房子是窮人。紅磚,灰瓦,大坡頂,二層小樓,小花園,門前汽車二三輛,家家房形與大小幾乎一樣。在中國,我們一般把這樣的房子叫做別墅。即使在城市,幾乎都住在這樣的紅磚或石砌的小樓里。在路過紐卡斯爾市的時候,沿著河谷兩岸,綠草與綠樹之中,漫坡遍野的紅磚灰瓦別墅,幾千幢幾萬幢連成斜斜的一片又一片。很少的幾幢白色樓房,看起來孤獨而且突兀。在城市之外的農(nóng)村,起起伏伏的原野之上,偶爾有幾幢白墻灰瓦的小樓,安靜地佇立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比城市的房子更漂亮。
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分不清。
想起來了,他們頂多算是些小地主。真正的地主是英國女王。白金漢宮是她家的,溫莎城堡是她家的,倫敦商業(yè)區(qū)的那一片石砌的五六層宮殿似的樓房,是她家的。這只是女王財產(chǎn)在倫敦的一部分,在英國的更小一部分。還有那些貴族,公侯伯子男,就是我們在電影電視里看到的那些莊園,漫漫幾百畝,幾千畝,綠草如毯,石頭筑的城堡穩(wěn)重,巍峨,雕刻華美,內(nèi)部裝飾無比豪奢,都是這些貴N代的地主們的私有財產(chǎn)。
地主的生活依然悠閑。在任何一個地方,鄉(xiāng)村,高速路服務區(qū),商場里的休息區(qū),街道旁,商店外,那些肥碩的英國佬們,三個兩個,或干脆一個人,品不完的咖啡,喝不完的紅茶,吃不夠的油炸薯條,烤腸烤肉,且非常講究:紅茶里沏上牛奶,然后捏著精致的小湯匙,輕輕伸進湯里,不須踫著杯壁,以免弄出不雅的響聲,然后,從六點鐘方向開始,按順時針方向,輕輕攪動……攪出一份生活的優(yōu)雅。
更應該關注卻常常不被人注意的是,不論任何地方,即使是在高速路服務區(qū),從衣著打扮到神情氣質(zhì),安安靜靜在此喝咖啡的人,都一樣地自信灑脫,衣著樸素大方,根本分不清誰是卡車司機,誰是小車車主。白領與藍領,享受的是一樣的工資待遇和一樣的尊嚴,養(yǎng)成了一樣的氣質(zhì)風度。真是令人羨慕!
地主的生活依然豐富多彩。我們在國內(nèi)看電視的時候,就覺得老歐洲人怎么那么會玩好玩啊?搬石頭,背媳婦,滾泥灘,甩枕頭,抖面粉,扔柿子,更不用說那些高大上的足球網(wǎng)球了。在這兒看英國人的電視,又知道他們?nèi)粘5耐娣ǜ啵∩恚瑘@藝,設計,音樂,繪畫,寫詩,寫回憶錄,如何燒木炭做燒烤,在樹林里做鳥窩,以及旅行冒險等等。悠閑中包含著太多的豐富,參與中孕育了澎湃的激情。
這地主的范兒,透著一股渾身舒坦的韻味。至于整個英國人的生存環(huán)境,我都想問一聲上帝:為什么如此不公?為什么英國人可以冬無嚴寒,夏無酷暑?為什么英國的土地上沒有干旱,沒有狂風暴雨,幾乎每天都會淋著些毛毛小雨?你都不用平田整地,不用建造耗費大量工錢的水利設施,不用擔心水土流失。綠草茵茵的國土上,沒有一寸土地是裸露的。所有這一切,為什么英國人可以,西歐人可以,我們不可以?為什么你可以有墨西哥灣暖流,我們就不能來個墨東灣或什么灣暖流?
我?guī)缀跸嘈牛税雅Q蜈s到自己的牧場就行了,等著喝奶吃肉就行。英國人的悠閑有英國人的道理,就如同中國人的勤奮也有諸多歷史、地理和文化的道理一樣。不同的是,在中國活成地主,也恐怕活不成英國地主那番愜意的模樣。
然而,這個地主畢竟老了。從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開始,都二百多年了,地主的悠閑日子過得太長,就會慣下一身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壞毛病。想當初,曼徹斯特的綿毛紡織業(yè),在世界上遙遙領先,而今可憐到蹤影全無。想當初,以生產(chǎn)出泰坦尼克號豪華郵輪聞名于世的貝爾法斯特造船業(yè),如今早已風光不再。想當初,設計精美雅致的路虎,賓利,勞斯萊斯,阿斯頓馬丁,美洲虎等汽車品牌,如今紛紛被德國、印度和中國收購。英國生產(chǎn)的非常舒適漂亮的出租車,被中國吉利注資控股,是唯一還能夠留在英國批量生產(chǎn)的車型。威爾士的礦產(chǎn)業(yè)全部倒閉,全國的鋼鐵工業(yè)岌岌可危,鋼鐵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二十萬工人,銳減到現(xiàn)在的不足兩萬人。他們把鋼鐵工業(yè)和許多制造業(yè)的危機,歸結到中國身上。
政府和平民都感受到沉重的壓力。尊貴的丘吉爾莊園要靠門票來維護龐大開支。醫(yī)療仍然免費。小學中學教育也還免費,然而大學不再全部免費。工作的機會受到東歐人的挑戰(zhàn)。日不落帝國,早已不再如日中天。這個老地主,確實有點老了。
在殖民擴張時,他曾帶給當?shù)厝嗣駸o盡的苦難。殖民之后,卻也留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這些民主國家的發(fā)達繁榮。現(xiàn)在,英國的金融業(yè)至少與曼哈頓一樣,共執(zhí)世界牛耳。許多的高科技公司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的紳士風度受世人景仰。他的閑適、優(yōu)雅、寬厚的人民,非常可愛。英國又是那么美。英國這個老地主,如果就此不再衰落,如果能和大家,比方說和經(jīng)濟欣欣向榮的中國,英國與中國,英國與世界,一起地主,真是最好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