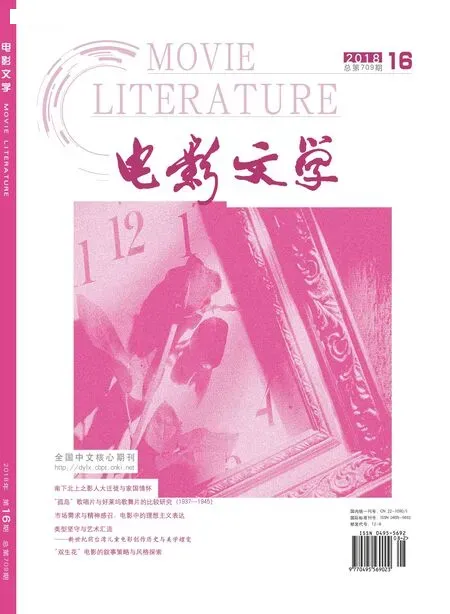國產(chǎn)動畫電影與受眾心理
戴曉玲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上海 200060;同濟大學 上海國際設計創(chuàng)新研究院,上海 200060)
動畫電影是影視藝術中重要的形式之一,也被認為是最具前途的電影類型之一。在當下,動畫電影擁有著龐大的消費市場,豐富多彩的題材和不斷給予人驚喜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國產(chǎn)動畫電影走過了近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一度取得令世界矚目的輝煌成就,盡管中間經(jīng)歷了一段藝術的失落期,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中國文化格局發(fā)生改變,國產(chǎn)動畫電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時期,也尋找到了新的發(fā)展方向,開辟了可觀的市場。在這個過程中,電影與受眾的心理不斷互相影響,產(chǎn)生著積極的交互作用,電影根據(jù)受眾心理來選擇自己的藝術表現(xiàn)視角,也可以對受眾的心理有著一種前瞻性的影響。
一、陌生化需求
從審美的角度來說,動畫電影能直接滿足受眾在視聽上陌生化的心理需求。受眾之所以接觸藝術,正是要進入到審美活動中,尋求被藝術加工和處理過后的對象,藝術中的事物往往不是對現(xiàn)實事物的照搬,而是以別致新穎讓受眾注意和喜愛。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指出的:“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的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電影藝術本身就對觀眾有著一定的間離效果,即如布萊希特所說的,一種疏遠人類與熟知的日常生活的感受,而動畫電影在這方面更是別具優(yōu)勢,動畫創(chuàng)作的自由性能讓主創(chuàng)最大限度地對事物進行陌生化處理,使受眾產(chǎn)生吃驚、費解乃至沉思和對事物的再認識等心理活動。
例如在《小門神》(2016)中,原本被貼在門上的門神竟然能夠下凡,和凡人一起生活,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門神神荼和郁壘之所以會來到人間,是因為神仙們也面臨著凡人的“再就業(yè)”苦惱。由于社會的發(fā)展改變了大量的民間傳統(tǒng)信仰,如灶王爺、財神爺?shù)壬裣芍饾u失去了自己的“崗位”,門神郁壘正是因為不甘心而決定去釋放年獸,讓老百姓意識到自己還需要門神的保護。而神荼則是默默地來到小鎮(zhèn)上唯一還貼著門神的小英餛飩店中,一邊在店里打工一邊等待郁壘的消息。這樣一來,兩個都有著下崗危機的門神就成為能夠吸引觀眾眼球,激發(fā)觀眾審美想象的新異事物。而正是由于這種事物的不斷涌現(xiàn),受眾才不會拘泥于思維定式,其審美水平和審美趣味才有得到提高的可能。與之類似的還有如《豆福傳》(2017)、《阿唐奇遇》(2017)等。
如果說,《小門神》還僅僅是將觀眾本已熟悉的事物進行變異,那么《龍之谷:破曉奇兵》(2014)、《行星綠谷》(2015)、《大魚海棠》(2016)等電影,則索性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反常”的世界,觀眾能在種種奇思妙想的設定中獲得享受。以《大魚海棠》為例,電影表示世界上存在一個和現(xiàn)實世界平行的空間,那里生活著一群介于人和神之間的,掌管世間萬物和人類靈魂的“其他人”。主人公椿就是“其他人”中的一員,她的家族成員也都擁有各種法力。在一次化為海豚來人間游歷時,椿結識了一個人類男孩,而對方卻為救自己而死,椿于是決定將男孩的靈魂,從一條小魚養(yǎng)成大魚,以實現(xiàn)對方的復生。在電影中,種種新異的概念,驚心動魄的、有著視覺沖擊力的場景,給受眾以新鮮感、陌生感的人際關系,都打破了受眾記憶之中的認知結構,超出了受眾的思維慣性,影像和心理圖式之間有著一種尖銳而良性的沖突。毫無疑問,未來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也將繼續(xù)創(chuàng)新,讓故事散發(fā)著想象的奇異光彩,以避免觀眾感到索然無味。
二、狂歡心理
從社會美學的整體狀態(tài)上來看,一種由崇高、詩性向著時尚、狂歡轉變的審美心理普遍存在,現(xiàn)代大眾更為主動地尋求娛樂需要的滿足,表現(xiàn)得更為狂熱、復雜和期待生理上的享受。巴赫金曾經(jīng)對狂歡下過這樣的定義,狂歡即“把一切高級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zhì)——肉體層面、大地層面和身體層面”。這在觀眾對動畫電影的欣賞中完全體現(xiàn)了出來。在動畫電影中,觀眾進入到了一個立體、活潑、多彩的夢境中,現(xiàn)實生活中令人苦惱、困惑的事物與觀眾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觀眾將注意力和情感寄托在主人公的身上。而在動畫電影中,主人公的目標、人物對美好事物的尋找追索,往往都能夠實現(xiàn)。這對于受眾來說是一種替代性滿足,觀眾能從主人公的得償夙愿中獲得快感。
在早期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代表作《大鬧天宮》(1961)中,我們就不難看到這種對受眾狂歡心理的滿足。孫悟空出生于石頭之中,在花果山水簾洞稱王,有著喜愛自由自在的天性,他上天入地挑戰(zhàn)神界原有的秩序,狂歡就在孫悟空對規(guī)則的逐一破壞中形成。孫悟空大鬧龍宮,逼得玉帝封其弼馬溫,隨后反下天庭,斗敗天兵天將,自封齊天大圣,這都是能讓受眾放聲大笑的狂歡景觀。天庭的等級和邏輯因為孫悟空這一闖入者和褻瀆者而被顛覆,權勢者對孫悟空感到無可奈何,限制常人行動的教條、虔誠、恐懼等在孫悟空面前幾乎不起作用,并且暴力在電影中具有重要地位。孫悟空與二郎神、托塔天王以及各類蝦兵蟹將之間的斗爭全部以暴力對打的方式呈現(xiàn),這更是加強了電影的宣泄釋放功能。與之類似的還有《哪吒鬧海》(1979)、《魁拔之十萬火急》(2011)等具有奇幻色彩的動畫電影。這些電影無不具有夸張的人物形象,打破現(xiàn)實既定框架,緊張刺激、讓人熱血沸騰的劇情,符合了受眾對精神解放的追求。
此外,童真性可以說是動畫電影的一大特色。大量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取材于古代神話或童話故事,而在原創(chuàng)的故事中,動物或無生命物也往往被以擬人化的方式,賦予人類的情感和生活體驗,用以演繹一種和人類生活相關,但被理想化了的故事。這種正是心理學家皮亞杰指出的,童真心理中的“泛靈化”意識。例如在《青蛙王國》(2013)中,活潑善良的青蛙有蛙國,而死對頭蛇則有蛇國,兩國因為蛇國國王的尾巴曾被蛙國國王斬斷而勢不兩立,因此青蛙在舉辦四年一度的,將以公主嫁給最終獲勝的勇士的運動會時,蛇國伺機搗亂,而蛙國公主則離家出走參加運動會,與閃電蛙不打不相識。現(xiàn)實和虛擬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在看到動物也可以擁有人類的感情、情緒等時,觀眾獲得了一種猶如重返童年的情感體驗。與之類似的還有《無敵乒乓兔》(2016)、《媽媽咪鴨》(2018)。在《媽媽咪鴨》中,大雁也會和人類一樣害怕結婚,也會有好勝心理而想脫離集體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在陰差陽錯地成為兩只小鴨子的“奶爸”,千里迢迢地護送小鴨子,并把小鴨子從烤鴨店解救出來后,大雁大鵬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變得更為有責任感,也得到了雁群的原諒。這樣妙趣橫生、引人發(fā)笑的設定都滿足了觀眾的狂歡心理,觀眾仿佛回歸童年澄明、遠離世俗攪擾的狀態(tài),并且能從主人公不斷倒霉,但又能絕處逢生的遭際中一再感到詼諧、幽默。
三、自尊心理
如果說,早年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還有著較強的教化意義,即使是充滿娛樂性的作品,也難免讓人感受到居高臨下的說教意味,那么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產(chǎn)動畫電影越來越注重受眾心理,其中就包括了對受眾自尊心理的注意。
(一)弱者與對抗快感
在當代社會中,大部分的觀眾都承受著生活的壓力,有著來自職場、校園或家庭的對立者,人和自己的對立者之間的矛盾和糾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人們顯然無法公然、徹底地反抗自己的對立者。而國產(chǎn)動畫電影則提供給受眾一個發(fā)泄的出口,電影總是會在敘事中設置一個對立關系,主人公往往在這一關系中一開始處于弱勢地位,但主人公并沒有因此而放棄抵抗,最后,弱者總能取得勝利。這正滿足了觀眾的叛逆心理,讓觀眾從主人公的對抗中獲得快感。例如在《寶蓮燈》(1999)中,因為舅舅二郎神把母親三圣母鎮(zhèn)壓在了華山之下,主人公沉香和二郎神之間的關系無疑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而就法力等而言,失去了寶蓮燈的三圣母尚且不是二郎神的對手,擁有一半凡人血統(tǒng)的沉香無疑更難以和二郎神對抗。打敗二郎神,點亮寶蓮燈,迎回母親,成為貫穿全片的沉香的目標。絕大部分的觀眾會在觀影過程中進行情感轉移,將自己無意識地融入居于弱勢和受害者,并且代表了正義一方的沉香,或是沉香身邊的好朋友身上,衷心地希望沉香抗爭成功。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與強勢、邪惡勢力——二郎神抗爭的就不再只是沉香,也包括了觀眾。最終沉香擊敗了舅舅,劈開了華山,這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叛逆、對抗心理,讓觀眾獲得了一次能力得到認可、勇氣得到表現(xiàn)的機會,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機會或沒有勇氣得到的自尊在動畫電影中得到了實現(xiàn)。
(二)英雄與自我實現(xiàn)
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xiàn)需求是居于最高層的。所謂自我實現(xiàn),體現(xiàn)在人能夠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潛能,在社會中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而作為最高需求,也就意味著人們實現(xiàn)它的難度是最大的。早在動畫電影誕生前的千百年,人類就在藝術形式中表現(xiàn)出了對“英雄”的迫切需要和熱情崇拜,這其實正是因為大部分人無法完成自我實現(xiàn),于是將這種心理轉移到了英雄的身上。動畫電影也不例外,從孫悟空、哪吒到沉香,國產(chǎn)動畫電影不斷推出一個個有著真善美化身意味的英雄,讓受眾為他們的不公遭遇而憤懣不平,為他們的大顯神威而拍手稱快,為他們的揚眉吐氣而欣喜狂歡。而近年來,在研究了受眾心理后,國產(chǎn)動畫電影開始向著美國類型片靠攏,一是選擇“英雄成長”的敘事模式,一是塑造有缺陷/怪癖的英雄,進一步地拉近受眾和英雄之間的距離。例如在《大護法之黑花生》(2017)中,大護法就是一個有缺陷的英雄,他潛入危機重重的花生村尋找失蹤的太子,本來憑借自己的法杖而擁有強大的能力,但是卻在被脅迫的太子違心的刺激下,丟掉了自己的法杖,以至于身受重傷,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護法依然拖著傷重的身體去保護太子,追殺兇手吉安和羅單兵,在得回法杖后,大護法恢復了自己身手利落、快意恩仇的英雄形象。觀眾無疑大多無法擁有大護法的高超武藝,和進入血雨腥風江湖冒險的經(jīng)歷,但在跟隨大護法一路前行的過程中,觀眾的心理得到了滿足。
把握受眾的心理,對于提高動畫電影的品質(zhì),加快其在“視覺轉向”時代的發(fā)展速度,是有著重要意義的。綜觀早期經(jīng)典的,以及近年來獲得良好口碑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基本上都能在傳遞主創(chuàng)的思想的同時,滿足受眾的陌生審美需求、狂歡心理和自尊心理,從而得到受眾的認同和接受。可以預見到的是,在未來,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社會生活的日益豐富,國產(chǎn)動畫電影也將日益精細、花樣百出,但在精研作為消費者的受眾的心理,為受眾提供娛樂、價值認同和情感共鳴方面,電影將是始終如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