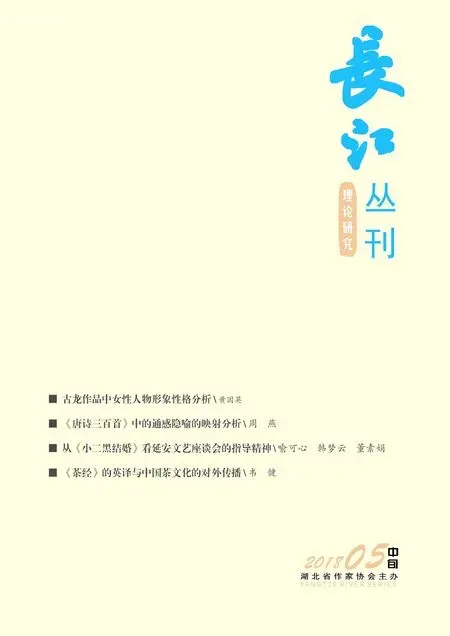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的現狀及未來展望
■/
縱觀2017年,幾款綜藝節目在網絡上的討論量激增,而一個新詞匯——慢綜藝,也悄然出現在網絡上。慢綜藝作為綜藝節目的一種新形式漸漸進入到觀眾的視野中。
一、慢綜藝的含義及特點
(一)慢綜藝的含義
近年來我國電視綜藝節目更注重體現文化品位和知識內涵。具有中國特色的電視綜藝文化特質逐漸顯現。模式創新注重家庭觀念、工藝元素,總體風格體現為溫情與和諧。慢綜藝暫時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定義,簡單的來說就是,不設定復雜游戲環節,不設定節目人物性格角色,而是將明星放在相對寬松的環境下,使其展現出最自然狀態的節目。而作為慢綜藝的代表作品,不論是文化類的《朗讀者》《見字如面》,還是戶外生活服務類的《向往的生活》《中餐廳》都廣受好評,被觀眾評價為綜藝界的一股清流。
(二)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的特點
1、輕松愜意
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相對于戶外競技類快綜藝區別明顯。節目整體風格淳樸、場景布置簡約、畫面風格大方簡潔、戶外場景的選擇以自然風光為主,減少過多的人為布置營造出自然和諧的場景氛圍。明星在自然和諧的場景氛圍中表現出自己真實的一面,通過明星的真實生活狀態表現出明星光鮮亮麗的外表下的另一面,大眾化平民化的明星也更具有親和力,更能給觀眾以一種生活場景、生活狀態、人物性格的代入感,使觀眾對節目產生認同感,對節目最直觀的感受是真實,給予觀眾舒適的觀看感受。
2、主線簡單明確
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沒有豪華精致的場景布置,沒有復雜算計的游戲規則,節目主線簡單目的明確。少了嘩眾取寵,多了溫暖感受,不盲目迎合觀眾的獵奇心理,不靠明星之間的相互揭短、撕逼增加收視率,而是走溫情路線,對觀眾進行一種思維引導,使得身處“快”時代的我們心境能夠“慢”一點,再“慢”一點。
二、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受歡迎的原因
(一)迎合現代人心理
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之所以能夠大受歡迎,與現代人的生活環境壓力大、生活方式節奏快這一基本現狀是分不開的。現代人工作繁忙、加班現象嚴重,能夠正常的享受周末假期已經很不容易,能夠有小假期去旅游的機會更是屈指可數,各種加班,各種瑣事占用了我們太多的時間,感受風光優美的田園生活,欣賞巍峨壯麗的高山峻嶺似乎都成了人們向往卻無法實現的生活。
(二)快綜藝扎推觀眾審美疲勞
競技類快綜藝扎推使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也是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在2017年伊始便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2016年《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等競技類快綜藝的熱播,使各大電視臺、各網絡媒體平臺競相推出了十數檔戶外競技類快綜藝,相似的游戲規則,各種明星的輪番轟炸,競技類快綜藝存在的競爭性,更是讓各種網絡話題罵戰愈演愈烈,觀眾對換湯不換藥的競技類快綜藝產生了審美疲勞,對網絡罵戰產生了厭惡感,因而對競技類快綜藝也產生了抵觸情緒。
(三)與競技類快綜藝區別明顯
競技類快綜藝扎堆后,各大電視臺為了尋求突破相繼推出了幾款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節目主要有《向往的生活》《中餐廳》和《親愛的客棧》,這三檔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都有自己的獨特的亮點,而在著重突出節目亮點、保持節目特色的同時,也無一例外的都關注到了現代人渴望獨立,渴望個性,渴望自由的真實心理及迫切需求,節目中都有著大篇幅的人與人交流內心的片段以獲取與觀眾之間的共鳴。也努力的將場景情景常態化、生活化,使觀眾與明星一起在不同文化的沖擊以及意外事件的累積中發現自我。
1、生活形態更加真實
《向往的生活》以三個主持人為主要構成部分,是基于一種中國傳統的三口之家的生活形態,三個人的分工給觀眾的感覺更像是一家三口為了柴米油鹽辛勞,拉近了節目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明星在節目中開玩笑、發脾氣、發牢騷等行為都使得明星所體現的人物性格更加的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明星形象更加親民化,給觀眾一種“原來明星跟我們一樣”的親近感,而狗、羊、雞等動物的加入除了增加了節目真實感之外,還增加了人與動物交流相處時的喜劇效果,也使節目更具有可看性。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代快節奏生活給現代人帶來的神經緊張、壓力大的沉重心態。
2、傳播文化意義豐富
《中餐廳》則是由趙薇、黃曉明、周冬雨、張亮、靳夢佳5位青春合伙人通過20天時間在泰國象島經營一家中餐廳,每期邀請特殊的嘉賓作為幫工出現,與青春合伙人們一起做出令人驕傲的中國味道。《中餐廳》跳出了傳統的單一的綜藝桎梏,從美食的角度切入,接地氣式的貼近人們的生活,講述人生的酸甜苦辣的同時也展現出明星的平凡的一面,滿足觀眾所追求的共鳴。第五期中泰國明星Mike攜友人一同來到中餐廳,《中餐廳》的合伙人們與三位泰國藝人進行了友好交流,在做節目的同時也增進了中泰兩國友誼,節目中黃曉明還送給了中餐廳顧客中國結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禮品,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3、綜藝框架模式新突破
《親愛的客棧》邀請了兩對明星夫妻或情侶作為常駐嘉賓,用20天時間在具有濃郁人文特色的瀘沽湖經營一家客棧,遠離城市喧囂,享受慢節奏生活。節目打破了現有的綜藝框架。明星嘉賓們真實的經營一間民宿,明星先自主分工,所有的房間和配套服務由老板定價,放大戲劇點。等待飛行嘉賓的到來后,解鎖民宿有趣的生活內容,舉行民宿大聯歡。
三、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存在的問題
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的流行,讓我們看到了電視綜藝為了引導大眾而非迎合大眾而做出的改變。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一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其實最早出現的慢綜藝并不是今年帶動慢綜藝風潮的《向往的生活》、《中餐廳》等節目,而是買了韓國綜藝節目版權引進中國的東方衛視的《花樣》系列以及湖南衛視播了三季的《花兒與少年》。這兩個電視節目一經推出就飽受爭議,尤其是湖南衛視播放的《花兒與少年》,每周更新后,網絡討論量數據高達數十億,有時甚至能夠到上百億,但是如此高的討論量背后,這檔節目的口碑卻并不理想。
(一)刻意剪輯虛化真實性
節目的剪輯也是影響觀眾觀看感受的重要因素,電視臺為了提高收視率對節目素材進行了誤導觀眾的剪輯。將經過刻意剪輯的預告片花放在正片尾處以提高熱度,預告片花內容多具有爆炸性或爭議性信息,這不光誤導了觀眾,也對明星個人心理健康或人身安全造成了影響。其中一部分問題是由于電視臺為了迎合大眾的心理對播出的節目進行了剪輯,將拍攝的素材根據收視熱潮以及觀眾所好奇的點進行有選擇的凸顯。通過刻意剪輯放大明星在旅途之中遭遇問題時所產生的矛盾與分歧,以此來提高節目的網絡討論量及熱度,間接的提高收視率。而這兩個系列的綜藝節目也因為刻意剪輯博人眼球突出明星之間的矛盾沖突,放棄了韓國TVN電視臺原版花樣系列中所體現的節目理念,在國內的口碑也與原版節目在韓國所收到的贊譽無法相比。《親愛的客棧》在微博熱搜榜上“陳翔哭了”“闞清子紀凌塵吵架”等話題熱度不減,在宣傳推廣方面也違背了慢綜藝的初衷。
(二)制作模式缺乏創新
國內綜藝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制作模式缺乏創新。此前我國的綜藝制作模式通常為國外首創綜藝大熱——引進版權回國翻拍——國內電視臺跟風照搬,而現在我國制作綜藝有了一個新名詞——借鑒式創新,借鑒其他國家綜藝的成功經驗與自己的一些制作想法融合,創作出一檔新的節目,這樣的節目不再購買國外的版權,并在宣傳時套上了原創的帽子,但是據網友的評論來看,這個借鑒的比例卻是相當大的。《向往的生活》被指出與韓國綜藝節目《三時三餐》不管是人物臺詞,劇本情節,物品擺放,甚至物資擁有程度都幾近雷同。而《中餐廳》則被指借鑒了韓國同類型綜藝節目《尹食堂》。《中餐廳》是一檔明星在泰國開為期20天的中餐飯館,旨在宣揚中國美食與中國文化,《尹食堂》是綜藝明星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開韓式料理店,希望能夠借此推廣韓國美食的一檔節目,借鑒痕跡十分明顯。《親愛的客棧》則是與韓國綜藝節目《孝利家民宿》內容形式十分形似。
四、戶外生活服務類慢綜藝發展的趨勢
(一)節目剪輯日趨成熟
慢綜藝的熱播,也讓娛樂圈的制作人們看到了商機。各大電視臺紛紛跟風制作,但更多的卻是以掙錢為目的的依靠噱頭博人眼球吸引廣告商的路子。刻意的剪輯使節目制作并非在節目本身而是在宣傳推廣等方面施以重力,比如《親愛的客棧》靠明星的個人私事制造熱點話題,帶動節目熱度,在這之后以民宿類為題材的綜藝也如雨后春筍般紛紛被推出,節目內容類型相似,宣傳炒作方式也使觀眾不喜,但綜藝市場會漸漸淘汰毫無特色依靠眼球而不是口碑生存的節目的。《向往的生活》《中餐廳》等綜藝節目在角色元素、細節元素和文化元素等方面都有值得贊賞的地方,能讓觀眾在看節目的同時感受到濃厚的人文情懷。現行的慢綜藝還處于探索階段之際,相信隨著競技性“快綜藝”帶來的審美疲勞,放松自然的“慢綜藝”將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變革綜藝趨向獨立創新
借鑒式創新類綜藝節目的產生造成了國內綜藝資源的浪費,制作綜藝的高投入、高耗費卻收獲了低口碑、低收視,這對于國內綜藝的健康發展十分不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原創綜藝人的積極性。借鑒得了表面借鑒不了精神,慢綜藝模式化的借鑒方式只會使所有綜藝趨同化。而沒有緊張感、沒有笑點,煽情氣味極濃,使得受眾容易產生逆反心理。這樣的“慢綜藝”節目顯然是無法營造“快綜藝”的節目環節與趣味。中國社會發展速度快,市場廣闊,慢綜藝的獨立創新之路,應該立足于中國觀眾的視角上,開拓具有特定需求的觀眾群體,融合中國觀眾的接受習慣及欣賞品味。在這個短頻快速食文化的浮躁年代,真實的人物情感溫情理性的文化內涵更能贏得觀眾的共鳴,且相對于國外引進的綜藝來說,又多了一份本土文化的熟悉感與親切感。
在競技類快綜藝大熱的大格局下,首開國內慢綜藝先河,這已經是一個值得稱贊的舉措,可能沒有許多的驚喜和創意創新,也并不完美,有許多的問題確需解決,但敢于嘗試第一步,就已經成功了一半。眾多大熱綜藝被指抄襲的同時也反映出了國內綜藝缺乏創新的事實,以及國內民眾對于原創綜藝的渴望和對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綜藝節目的迫切需求,國內慢綜藝的發展與創新雖然緩慢但卻在漸漸注入新鮮的思想與血液,因此慢綜藝的未來仍舊值得我們的期待。
:
[1]歐陽宏生,舒三友.論電視綜藝節目模式創新[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165~170.
[2]競技真人秀當道的時代,慢綜藝還能逆襲嗎?[EB/OL].2017-03-09.
[3]鄧彩菊.從節目元素分析慢綜藝節目成功的原因——以《向往的生活》為例[J].北方文學,2017(08):110.
[4]劉杰.快時代的“慢綜藝”節目現況分析與未來發展建議[J].傳媒論壇,2017,3(1):14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