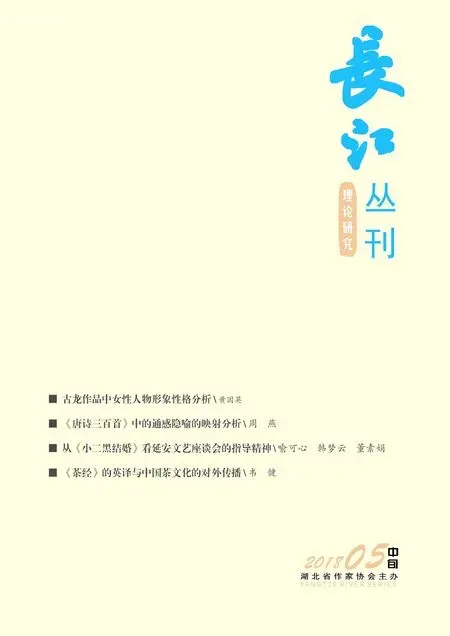淺析網絡服務提供者因網絡用戶侵權的侵權責任
■/
《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第二、三款對網絡用戶利用網絡實施侵權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兩種法定情況下分擔的侵權責任進行了規定,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這兩款規定一定程度上傾向于保護被侵權人的利益,是法律制度的讓步,加重了網絡服務提供的侵權責任。本文試圖通過對網絡服務者侵權責任的理論框架的梳理,探討網絡服務提供者因網絡用戶侵權的侵權責任應當如何分擔,才能更合理有效地保護各方主體的合法權益。本文所探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特指網絡服務提供者因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侵權的侵權責任。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及其侵權行為概述
隨著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網絡已經悄無聲息地鉆進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網絡服務提供者作為一個現代新詞匯,我們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它的概念,從而進一步界定其提供的服務的性質,也是本文探討網絡服務者侵權責任的起點。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
從廣義上來說,網絡服務提供者就是指通過網絡技術提供各種服務的主體。通過對服務的類型化去界定何謂網絡服務提供者,實則是科學技術性的界定。而本文旨在通過對法律條文的解讀去認定法律上的網絡服務者的定義。
“網絡服務提供者”這個概念首次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之中,該解釋同時也使用了“提供內容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這個概念。由此可以認為“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的概念從屬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法》中直接使用“網絡服務提供者”一詞,雖沒有明確定義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但不難從法律條文的釋義。從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來看,網絡服務者本身就能提供相關服務,如直接向網絡用戶提供信息或產品,可以稱之為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第二、三款規定來看,網絡服務提供者作為平臺為網絡用戶提供服務,換言之網絡服務提供者成為傳播的中介,為網絡用戶提供平臺服務,如網絡用戶通過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渠道傳遞信息、搜索信息或者儲存信息,可以稱之為技術服務提供者。網絡服務類型復雜多樣,而不變的是其服務的特性。因此筆者認為,無須再細化“網絡接入或自動傳輸服務提供者”、“網絡空間提供者”或是“傳輸通道服務者”等類型,僅需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的屬性,即區分是自身性內容服務還是媒介性技術服務。
因此,本文所論述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是基于《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第二、三款之上,則本文所使用“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狹義地指起媒介作用的網絡技術服務提供者。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
認定侵權行為的類型和形態是確定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第一步,也只有網絡服務者實際存在侵權行為的前提下,網絡服務提供者才有承擔侵權責任的正當性依據。因此,需結合侵權法相關理論,正確判斷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
1、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判定
從上述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可知,網絡服務提供者是為民事主體提供平臺或渠道的一種媒介,它同《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七條中的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一樣,他們所實施的行為是一種中介行為,相對于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所實施的行為,可以明確區分前者的行為是中立的,而后者的行為是直接的。當網絡用戶的行為變成直接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侵權行為時,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行為的性質是不變的,仍然是中立的,此時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根本談不上是一種侵權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如何判定為侵權行為,僅能框定在法律規定的兩種情形下。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被侵權人通知后和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時,其行為可能構成侵權。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判定的依據就是法律明確作出的規制。換言之,法律賦予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以安全保障義務,同樣地,判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侵權所依據的兩種法定情形可以稱之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維護網絡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網絡服務提供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從而認定其行為是侵權行為。
2、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性質
在理解這種侵權行為的性質時,有的學者從法律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連帶責任,反推論證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本末倒置的論證方式。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的性質是否是共同侵權當然應當以明確共同侵權行為的概念和本質起點。而關于共同侵權行為的概念在理論上頗有爭議,若“按照《侵權責任法》第八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共同侵權應當解釋為有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行為”,那么顯然網絡服務提供者沒有主觀上的幫助意思,網絡服務者提供平臺的客觀支持不能曲解為是法律上的主觀幫助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不是共同侵權;若“共同侵權行為在廣義上除了典型的主觀關聯共同侵權行為之外,還包括客觀關聯共同侵權行為”,那么則可以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網絡用戶各自的每一個行為都針對同一個被侵權人,且損害結果無法分割,構成客觀的共同侵權行為,然而筆者不贊同由此證成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性質屬于共同侵權,反之“法律將網絡服務提供者為用戶侵權提供的‘平臺’上的‘幫助’解讀為構成共同侵權與法律對其他‘幫助’現象的解讀存在嚴重的價值取向上的不均衡”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
因此,筆者認為擱置這種爭議,從作為與不作為的角度去認識網絡服務提供侵權行為的性質,更有利于確定侵權人責任的范圍及其分擔。假設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是主動作為,無論其是否與網絡用戶有共謀,如網絡用戶發布的信息侵害他人的著作權,而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推動該信息至頭條,這種主動作為的侵權行為可以于第三十六條第一款中進行規制,與本文探究的第二、三款中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不契合,因此假設不成立。那么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性質應當是一種不作為。法律賦予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以安全保障義務,同樣地,判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侵權所依據的兩種法定情形可以稱之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維護網絡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因第三人侵權而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不作為侵權,而網絡服務提供者同樣因網絡用戶這一第三人侵權而為采取必要措施的不作為侵權。因此,類比論成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性質是不作為。
綜上,從侵權行為類型上判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屬于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同時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形態具有不作為的性質。那么我們在研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時,就應當充分考慮其侵權行為的不作為性質。換言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就不是“dutyofact”,而應當是“dutyofcare”。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和責任形態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關于侵權責任規則原則的研究已有頗多優秀的成果,筆者贊同王利明、楊立新教授的“三元歸責原則體系說”:《侵權責任法》第六條和第七條的規定了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則原則體系,分別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過錯推定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理由在于公平責任是否納入侵權責任歸責原則體系之內,應當由現行法律制度決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二條并不能解讀為公平責任的規定,其實則是在確定損失的正義性分擔,并非行為的歸責。
那么,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應當適用哪一種歸責原則呢?從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技術性中立服務來說,若適用無過錯責任會是中立服務更加被動,網絡服務提供者意味著對所有信息進行監控,這勢必成為網絡產業發展的障礙;若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只能在某些舉證困難或者舉證能力差異大的特殊領域才能起到一定的公平作用;權衡被動型的中立服務、法律關系網絡信息大數據的更新迅速以及相關權利人的利益,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更為合適。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形態
侵權責任形態,是指侵權法律關系當事人承擔侵權責任的不同表現形式,即侵權責任由侵權法律關系中的不同當事人按照侵權責任承擔的基本規則承擔責任的基本形式。侵權責任形態具有三種類型,結合本書論述的技術性網絡服務提供者來說,第一,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形態是替代責任,原因網絡服務提供者對自己管領下的物件即技術性網絡平臺的致害負責。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用戶的直接侵權行為有權利和能力加以監督和管理,卻未采取及時的必要措施,且可能因該侵權行為獲得直接利益,網絡服務提供者構成的是替代責任。第二,根據侵權責任究竟是由侵權法律關系中的一方負責還是雙方負責,分單方責任和雙方責任。加害人一方無過錯沒有責任,那么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形態是單方責任;有可能行為人和受害人都應當承擔責任時,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形態是雙方責任。第三,根據承擔責任主體的數量不同,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共同責任。原因在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對其管領平臺未及及時負責的行為和網絡用戶主觀錯過直接侵權行為共同構成損害結果,該侵權后果由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網絡用戶共同承擔。而關于最終二者以連帶責任、按份責任還是不真正連帶責任的形式分擔責任,將由下文論述的侵權責任的分擔制度來決定。
三、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構成與分擔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構成
侵權責任構成,是指行為人依法承擔侵權責任所必須具備的法律事實要求。并且,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雖明確規定多種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但我們探討的侵權責任構成一般僅指損害賠償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網絡服務提供者在過錯原則下是否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取決于網絡服務者滿足所有的損害賠償責任構成要件。首先,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致害行為是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即消極的不作為;其次,損害事實是網絡用戶直接侵權后損害結果的繼續發生或者擴大;再次,因果關系在于網絡服務提供的不作為行為導致了損害結果的繼續發生或者擴大;最后,主觀過錯則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對其管領下的服務平臺負有安全保障義務,而網絡服務提供者未盡到這種消極的預防損害的義務是其可責性的過錯。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分擔
1、侵權責任分擔的概念和意義
侵權責任分擔,是指在包括賠償權利人在內的數個當事人之間對損害賠償責任和受償不能風險及程序負擔的分配,以及在連帶責任中部分責任人無分攤能力時,對損害賠償責任和受償不能風險責任及程序負擔的再分配。由此可知,這個制度分配“三種責任”:第一,最終責任,是指賠償義務人應該向賠償權利人承擔的與最終賠償責任相等的責任部分。第二,風險責任,是指超過最終責任部分而實質上是承擔了受償不能風險的賠償責任部分。該部分責任與最終責任的同樣是責任的性質,而區別在于通過分攤請求權或者追償請求權的配置,責任人實際上只是承擔了一定的分攤不能或者追償不能的風險,并非實際的最終責任。第三,程序負擔責任,是一種派生性責任,主要指查明全部責任人的負擔、提起追償或者分攤訴訟的負擔以及順位利益的調整。研究侵權責任分擔這一創造性概念的意義在于,與以過錯責任原則來判斷侵權人因主觀上有無過錯而是否需要承擔侵權責任不同,侵權責任分擔原則的功能在于實際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時在數個當事人之間分配各自承擔侵權責任。
2、侵權責任分擔的標準
上述侵權責任分擔的概念已明確了侵權責任的分擔包括最終責任分擔、受償不能風險分擔以及程序負擔分擔。無論何種責任的分擔實質都是一種實現正義的分配,要實現正義的分配必須建立在一個統一的標準之上,即責任分擔的依據。分配正義的標準應當根源于侵權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以及主觀過錯,那么分配的標準應當包含以下兩個要素:第一,過錯,是指主觀上的、法律上的可責難性程度;第二,原因力,是指在構成損害結果的共同原因中,每一個原因對于損害結果發生或擴大所發揮的作用力。可責難性標準與原因力標準在侵權責任分擔中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應當分別適用于“三種責任”。具體來說,最終責任的性質是責任人本應當承擔的責任,以客觀作用與損害結果即原因力標準決定責任分擔,而風險責任的性質相反,受償風險不能對自由的限制更大,以可責難性標準決定責任分擔更為正義。
3、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分擔
以可責難性和原因力為標準,逐步分析最終責任、風險責任和程序責任,最終確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從原因力標準來看,損害的發生以網絡用戶的直接侵權行為為必要,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行為是管領不當而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或擴大起補充作用,以原因為標準為主來確定最終責任上來說,網絡用戶獨自承擔完全的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分擔為0%;從可責難性標準分析,網絡服務提供者對其提供的平臺未盡到消極的預防損害義務(亦可稱為與賓館等場所管理人同性質的安全保障義務),主觀上有過錯地未能防止網絡用戶繼續侵權導致損害發生甚至擴大,這種未盡到義務的主觀心理是對過失的可責難性,其承擔“dutyofcare”的后果,即因其不作為而應當承擔過錯的補充責任。
此外,立法作為利益沖突調整的最為重要的工具,必須置于特定的社會關系或者法律關系之的環境之中。因而,現行《侵權責任法》第三十條第二、三款的規定,有意加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然而,更正義的優化方案,可能是基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優勢地位考慮,將補充責任加強到單向的不真正連帶責任。
注釋
:①②王利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釋義[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158.
③張新寶.侵權責任法[M].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8~49.
④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4~105.
⑤徐偉.網絡服務提供者連帶責任之質疑[J].法學,2012(5):84~85.
⑥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7.
⑦楊立新.侵權法論[M].第二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第四編.
⑧王竹.侵權責任分擔論——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分擔的一般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82.
⑨楊立新.侵權法論[M].第二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525.
⑩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J].中國法學,2009(4):177.
:
[1]王竹.侵權責任分擔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3]楊立新.侵權法論[M].第二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王利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釋義[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
[5]張新寶.侵權法論[M].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6]王竹.侵權責任分擔論——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分擔的一般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7]申屠彩芳.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8]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J].中國法學,2009(4).
[9]徐偉.網絡服務提供者連帶責任之質疑[J].法學,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