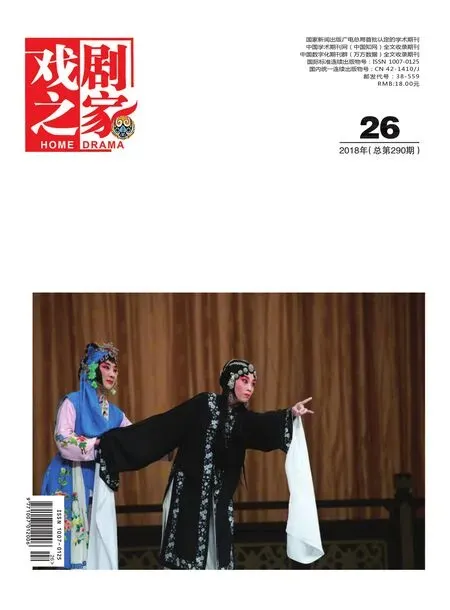淺析二胡獨奏曲《迷胡調》
李奕霏
(河南大學 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作品簡介
《迷胡調》創作于1958年,與《秦腔主題隨想曲》花開并蒂,是秦派二胡演奏家魯日融大師的處女座,也是他的成名作。1961年,《迷胡調》一曲在全國二胡教材會議上一經魯大師演奏便樂驚四座,陸修棠等先生贊不絕口,少年閔惠芬也發出“穿心入肺”之慨。
《迷胡調》是根據陜西東部二華(華縣,華陰)流行的迷胡清唱曲中的“剪剪花”“慢西京”兩支節奏,旋法對比鮮明各有特色的迷胡曲子為素材而編創的二胡曲。
“迷胡”又稱“眉戶”或“曲子”,是陜西關中地區廣為流傳的一種民間說唱音樂,集民歌,說唱,戲曲等風格于一身。每首曲子即可單獨演唱,又可將多首曲子組合,具有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是我國西北地區優秀民間音樂之一。《迷胡調》這首曲子名字的由來也別有一番風趣。對于采用“迷胡”還是“眉戶”一詞,魯大師也是幾經推敲。在陜西民間,人們把古今流行的民歌小曲稱為“迷胡”也作“小曲”。但也因陜西關中西部眉,戶二縣的“曲子”更加流行,所以也有稱“眉戶”一詞的。而“迷胡”一次又有“迷人的音樂魅力”之含義,因此,魯大師采用“迷胡”二字,更為形象貼切。此曲在上世紀80年代再版時曾由編輯改為“眉戶調”,但作者還是認為《迷胡調》更能體現陜西民間音樂的迷人魅力。
二、《迷胡調》作品淺析
《迷胡調》全曲采用復三段曲式結構。第一段是小快板,第二段是慢板,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壓縮再現。全曲長約六分鐘,短小精悍又讓人聽后回味不絕。
第一段曲調輕快,明朗,富有活力。以“剪剪花”為素材。開頭便以具有陜西風味的壓揉演奏,前兩小節第一個音一步到位,不加滑音,加入壓揉更具特色。因此對小指的力量,伸展與手腕的放松要求很高,初學時,可能出現小指發酸,手臂緊張等情況,要注意放松。第三小節便出現了極具陜西關中特色的音階,這種特殊的音階半音關系距離較大,“si”通常會偏低一些而“fa”通常會偏高。由于這兩個音具有一定的游移性,一般常作為陜西音的“特性音”在演奏時要注意掌握分寸。在第一段的中間(47-60小節),出現了一小段材料不同的音樂。這一小段具有詼諧性,氣氛較為緩和,演奏時可以想象為一位白胡子老爺爺歡喜搖擺的場景。緊接著,又是主旋律的出現,在第一段最后,由一個減慢把音樂轉向了較為委婉悠揚的第二段慢板。第二段主要以慢西京為素材,比較具有抒情性和層次感。在一開始的前四小節,演奏的時候要注意以較弱的力度,并且做到音斷意連。隨著曲子的發展,力度與連貫性要逐漸遞增,特別是到達曲子第116小節的時候,情緒在之后的四個小節,兩小句相同的旋律要做出mp與f的對比。整個慢板段落也是重復的比較多,但是每次重復的處理都不同,筆者認為在這一段要演奏出韻味,要注意層次的遞進。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壓縮再現,感情更加歡快熱烈。最后一句以一個顫弓干脆地結束了全曲。
筆者認為,《迷胡調》這首曲子之所以能把陜西地方音樂特點體現的淋漓盡致,與以下三點密切相關。一是音階的特殊性,二是揉弦的個性,三是滑音的使用。在陜西戲曲音樂中有兩種風格截然不同的唱腔,分別是“歡音”唱腔與“苦音”唱腔,從字面意思就可看出分別表達了歡快與悲傷的兩種情緒。這兩種不同唱腔的音階不同,而且骨干音也不同。“歡音”的骨干音是“mi”和“la”;“苦音”的骨干音是“fa”和“si”。而骨干音直接影響著旋律的風格和走向。全曲中最有特色的要屬揉弦了,并且揉弦也是秦派二胡的特色。如果將揉弦細致化處理,會有很多種結果,揉與不揉的對比,輕揉與重揉的對比,快速揉與慢揉的對比,還有上手就揉與遲到揉的對比。而在《迷胡調》這首作品中,揉弦大多是圍繞特性音和骨干音展開的,這樣才能較準確的表現陜西風格樂曲的特色。一首二胡作品中的滑音就像衣服的標簽一樣,最能直接展現樂曲的風格特點。《迷胡調》中使用較多的就是下滑,回滑音,顫滑音(邊揉邊滑),在慢板中的116小節就出現了回滑音與上滑音結合使用,演奏時由三指先從“do”滑向“si”,在滑到降“si”,最后再回到“la”,這樣的滑音使樂句充滿了委婉動聽的感覺,在情感表現方面有錦上添花之效。
三、結語
《迷胡調》這首作品是“秦派二胡”的開篇之作,不僅將地域文化與二胡藝術相結合,更向世界人民展現了秦地,秦風,秦趣。這首曲目的成功,不僅讓魯大師獲得了榮譽,更讓他從中“悟”出了自己今后的創作方向,創作思想和表達方式。即始終立足于陜西民間音樂土壤,不斷挖掘陜西民間音樂資源,時時在作品中尋求新意,努力創建一種具有秦地風韻而又彰顯時代感的二胡音樂,為當代二胡藝術的多元發展盡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