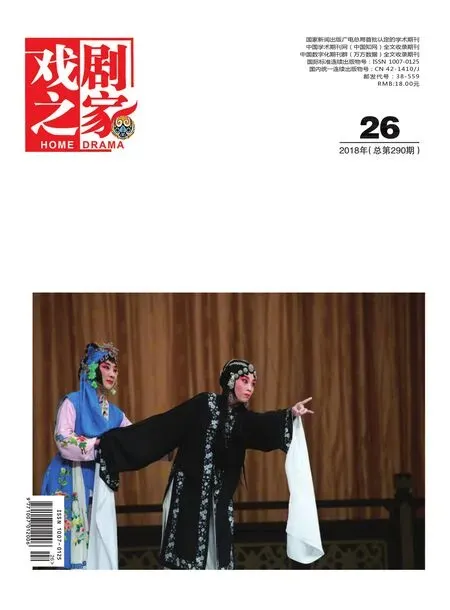電視劇《紅樓夢》插曲《葬花吟》的演唱分析及審美體驗
丁后兵,朱峰玉
(江蘇師范大學 江蘇 徐州 221000)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黛玉吟唱了曹雪芹為體現她冰清玉潔的品質和其卓絕的才情打造的凄美樂章——《葬花吟》。其詞句凝聚無數血淚與怨憤,曹雪芹的想象非常的豐富又奇特,塑造的畫面有無限的凄清之感,表達了林黛玉在心理上對生對死、對愛對恨產生的斗爭,并產生了對生命的迷茫。
一、《葬花吟》的演唱分析
(一)氣息。《葬花吟》的演唱中一方面可以遵循作曲者樂譜中記錄的換氣符號來進行氣息的把握,例如原唱陳力演唱時沒有過多的改動也把歌曲演繹的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可以根據自己對作品的理解以及情感的處理來把握氣息。例如吳碧霞在演唱過程中,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都處理的相當到位,沒有嚴格按照樂譜的記錄來,而是融入了個性化的理解,在氣息處理方面悄無聲息的讓聽者覺察不出。
(二)咬字。歌唱與語言是不分家的,歌唱家所演繹的所有歌曲,都是唱給觀眾聽的。歌唱中很重要的點是必須把語言清晰的傳達給觀眾讓他們能聽懂。因此,咬字在歌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咬字時,首先要咬準字頭,需要用力的咬清晰,但用力不是咬死的意思,咬死會導致歌曲缺乏流動性而顯得僵硬。
如歌曲高潮“天”“頭”“丘”字時值都較長,歌唱者就需要在足夠的氣息支撐下咬住字頭。因為描寫的是黛玉“叩問”蒼天時的悲憤,便不能像第一段那樣輕柔。首先要用力咬準字頭,再將字腹隨旋律推送出去,最后干脆利落的收字尾。將字腹和字尾糅合在一起,做到歸韻清晰,聲音聽起來就自然了。
歌曲輕柔委婉,用氣或是音量都不能過強,此處個“何”字演唱時會相對難處理,“h”處理不好聲音就會不干凈,此處只要稍微抬起舌根至軟腭,讓氣流摩擦發聲。很多帶有“h”音的字都可以這樣處理,聲音聽起來就干凈了。而吳碧霞在演唱此處時,與意大利“tr”發音相結合,這種處理彰顯了她中西結合的特點,別有一番風味。
二、《葬花吟》的審美體驗
(一)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葬花吟》音樂響起,腦海中就盤旋著黛玉葬花的唯美畫面,能透過畫面看見她那柔弱之美、凄苦之美、絕望之美以及那病態中的抗爭之美。而《葬花吟》豈是止步于畫面的作品,它已升華至極強的意境美中了。葬花在人們看來就已經是很詩意很凄婉的一種行為了,又在“花謝花飛花滿天”如此凄苦的畫面了收拾著殘花,也收拾著對自身命運的感嘆。由此,葬花的意境美也被襯托無遺。
意境講究的是情與景的交融,如果只是對“花謝花飛花滿天”這樣對景的描寫,就不足以形成意境,意境的形成永遠離不開情與景的結合。所以《葬花吟》不僅有對自然景物的贊美與憐惜,更有聯想至人對人生哲理的感悟。《葬花吟》用藝術語言勾勒,描寫黛玉以花喻己,又人花合一的表達了自己滿心的凄苦,賦予了作品意境表現的審美價值。
(二)自然流露的情感美。表演者在音樂表演過程中要投入真實的感情,使自己的真實感情與音樂作品融合為一體,這樣才能真實生動的再現作品的情感內涵。而音樂表演又是一種自然流露的藝術,只有從表演者心里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才是最真摯動人的。刻意表達的思想情感往往會破壞表演者與聽者之間的情感共鳴,從而降低作品的美感。演唱中情感的自然流露對表演者的技巧要求很高,如若不是得心應手自然也做不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著名歌唱家吳碧霞在演唱《葬花吟》時,腦海里還原了原著里的畫面與情節,想象自己便是那主人公黛玉,這種身臨其境的體驗使得她所演唱的每一個音符都是從心里迸發出的最真實的聲音,從而達到了情感的自然流露,讓人聽后黯然神傷。
三、結語
歌曲《葬花吟》不僅是高度文學性與藝術性相結合的作品,還是我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杰出代表。王立平先生以其獨特的創作,讓歌曲《葬花吟》成為經典。他從黛玉的人物特點出發,將流行元素融入中華民族傳統音樂中,刷新了觀眾對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審美。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有義務去繼承和發揚其優秀的文化。
通過對本文的寫作,對歌曲本體的分析以及對技巧把握的分析,讓我對聲樂演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認為作為聲樂學習者,我們應該具有分析作品的能力,并能發掘音樂背后的故事與哲理,最終為演唱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