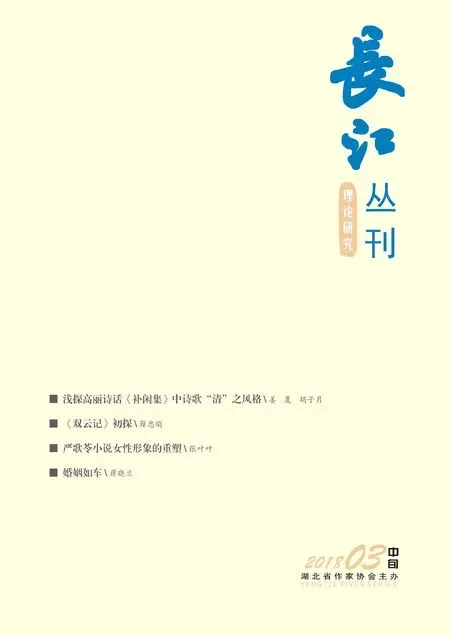論“中體西用”的多重變奏
——兼談中西文化觀的演變
■
廣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明朝萬歷年間,伴隨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許多西方傳教士先后來華,西方文化開始比較迅速的傳入中國,其中特別是自然科學知識頗受明朝士大夫喜愛。然而,時人總體上對西方文化懷抱獵奇、看新鮮的心態,故中西文化的沖突和爭論少有發生。二百多年后,當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屈辱的序幕,國情危急緊迫,對于挾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文明,從偏執腐儒對“奇巧淫技”不屑一顧,到今日學者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和中國文化話語權的聲張,由此,開始了近百年中西文化觀的演變。而這一漫長曲折演變,顯著表現為“中體西用”思想的興起、轉變和破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中西文化觀變遷的角度,對“中體西用”思想重新進行梳理。
一、“中體西用”的興起
鴉片戰爭后,國人猛然認識到我國科學技術已經落伍。在這樣的背景下,魏源率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即學習西方現代兵工技術以拯救中國危亡,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初起時救亡圖存制夷的“防衛型”特征,也揭示了近代中西文化觀中的大方向——向西方學習。最早提出“中體西用”說法的,應該是沈壽康,他說:“夫中西學問,本身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發表《勸學篇》系統論述“體用論”標志“中體西用”理論模式正式形成。
19世紀60年代清廷興起洋務運動,洋務派以作為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指導思想。起先,“中學”主要指傳統的倫理道德、綱常名教,“西學”則主要指為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在洋務派眼中,“中體西用”或確乎是值得驕傲的思想發明。此一范式對中國傳統哲學“體用”范疇(特別是朱熹體用學說)庸俗化而用之,使傳統哲學“體用不二”的“實體與功用”,一分為二,變為“主要與從屬”、“目的與工具”之義。體和用失去其哲學意義,更多成為文化學意義的一對概念。張之洞這批天朝的改革者們一廂情愿設想,“中體西用”乃是處理中西文明的絕佳方案——既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綱常,又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通過工具性地引入西方文化(當時特別地限于技術),吾“先王之制”、“圣賢之道”盡可完整保存。
客觀地說,洋務運動開展期間,”中體西用“思想對于沖破封建頑固派阻撓,引進西方自然科學,促進中國工業、軍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產生發揮過積極作用。經濟上,洋務派先后建成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總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國第一批大型國有工業企業(應注意,這些企業管理體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層管理人員亦官亦商,可謂中體西用之縮影),對中國的早期工業化起到重要作用。
二、“中體西用”的轉變
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深入,原先的“中體西用”思想已經無法指導進一步學習西方經濟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內容。對此,梁漱溟先生這樣描繪道:“……及甲午之役,海軍全體夜沒,于是大家始曉得火炮、鐵甲、聲、光、化、電,不是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后面還有根本的東西……”洋務運動破產了,這與它僅停留于初級的技術學習不無關系。自強求存的仁人志士提倡更大范圍向西方學習,“西學”漸入制度層面,立憲制度、代議制度等諸多社會改良方案進入國人視野。
可是,時一時間并沒有另起爐灶的勇氣,他們只是對“中體西用”思想內涵悄悄進行著轉化,如鄭觀應提出:“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學,其本也;……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鄭觀應已經論述到中學和西學關系,這個論調試圖繼續通過縮小“中體”內容、擴大“西用”范圍的方案,繼續維護“中體西用”。因此,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中,一方面提倡學習西方治國的政教法度,一方面竭力強調“堯舜周孔之道”乃“萬世不易之大經大本”。此外,鐘天緯大力宣揚“唯我孔子之教,如日月經天、江河亙地,萬古不廢”的同時,對西方格致之學成就高度贊譽,大力倡導學習歐洲各國“通民情、參民政”的“大本大原”。這種論述,從表面上看,依然是以往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實質內容已經大大改變。
甲午戰后,伴隨維新思潮的興起,“中體西用”思想進一步轉化,出現了“中西會通”的新論,梁啟超即為其中代表。梁啟超代總理衙門起草《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時,明確提出:“近年各省所設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蓋由兩者之學未能貫通……考東西各國,無論何等學校,斷未有盡舍本國之學而能講他國之學者,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梁啟超明確提出“中西并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堅持以“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為“會通”中西之原則。此外,這里還隱隱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西學比起中學,并未顯得遜色,西學有資格和中學處于同等地位。
近代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認識深入,相應地,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評估亦不斷調整。此為一體兩面的過程,基本上,前者不斷調高預期和評估,后者持續貶低批判。這樣的中西文化“實力對比”,忠實地反映在“中體西用”形態劃定,學界一般劃分學習西方文化(即“西用”部分)為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觀念層層面三個階段。到了學習西方的第三個階段,在最核心觀念層發生的情形是,吳又陵、早期的胡適及大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規范發起了最后的沖擊。至止,作為“用”的西方文化已正式登堂入室,呈現出代替中國文化之體的趨勢,而中“體”也慢慢被拋棄。
三、“中體西用”的破產
如前所言,時人對西方文明接觸越深,仰慕越多;對比之下,就中國文化的分別區劃也更加透徹。中國以道德立國的文化傳統與西方功利至上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價值理想上形成了鮮明對比。如康有為的“西方物質,中國道德”,梁啟超的“西方物質文明,東方精神文明”,孫中山的“西方科學,中國國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國理性”,等等,表達出的都是物質與精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之間的分立、矛盾、沖突。在此種文明的對立沖突中,且又多就中國傳統文化持殘酷偏見,全欲一掌拍死而以為勝利。“中體”基本上成了中國落后、國家衰敗而受列強凌辱的最大原因責任體之一。
由此,又粗略分出兩種陣營: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胡適、陳獨秀、魯迅、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基本屬于前者,而梁漱溟、馬一浮及梁啟超、嚴復有保守傾向。嚴復對“中體西用”持懷疑態度,從中西文明之異質性譏諷其“馬有馬體,牛有牛體。”且極力主張體用不二。但在一戰后,發現西方文化亦毛病纏身,遂還轉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之作為根本之體,堅信不疑。梁啟超等人亦有如是體用觀念的前后轉變。激進主義者從中體西用框架中跳出來,主張一種全盤西化的立場,至少對于傳統文化“中體”之地位發動毫不留情之致命攻擊。而于保守主義者,在考察西方文明諸多毛病之后,他們認定中國傳統文化并非一無是處,至少應對之同情的理解。從歷史上看來,激進的聲音和力量占據了上風。傳統文化歷經劫難,幾近枯竭。
四、結語:呼喚多元平等的中西文化觀
回顧歷史進程:“中體西用”的變化就是“體”與“用”兩個概念內涵的互相消長,“西用”的范圍不斷地擴大,而“中體”如梁漱溟所說,剝筍一樣被人一層一層地剝下來。持中體西用論的人們從買船艦造槍炮到辦新式學校和現代工業,發展為改革政制,卻沒能秉持“中國文化根本”而獲得勝利,中國的富強獨立,恰是在拋棄傳統后付出難以統計的代價之后得來的。
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體西用”概念流轉接近百年之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體用不二”的中西文化觀,指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關系,“中體西用”論的實質在于用“價值理性”支配、約束、統轄“工具理性”。牟宗三的“體用不二”,已不同于一百多年前洋務運動提的“中體西用”——當時所謂“中體”,絕不可能是現代意義所謂“價值理性”,它不是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而是維護“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宗法制度,正像魯迅所說的是“吃人”。
其后新儒家之第三代人物杜維明先生、劉述先先生等均對儒學(傳統文化代表)做了某種定位:“全球化世界中,多元精神資源中的一支。”“中國文化之本,乃是多元世界文明中有益的一員。”提倡“后新儒家”的林安梧也表達了類似看法,我們面對傳統,至少要給予與西方文化同樣的平等的觀照。近年來,有學者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西文化同體共用殊相論”:不管“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都對“體”進行了人為地切割。假如“體”真的可以分成中、西,那么它也就喪失了形而上的地位,下降為世俗世界狹義化的一物,不再擁有“體”涵蓋一切的特征了。鑒于形上本體不可分亦不能分,故從終極上看,人類永遠都只能共同擁有一個“體”。人類既然同體,當然也就可以共用。不僅西方的文化可以取用于東方,反之,東方的文化也可以取用于西方。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雖然彼此面對的是共同的整體性的形上本體世界,但對其展開言說時卻分別使用了差異性很大的語言符號。總之,唯一且共同的形上本體統攝人類的一切文化活動,這些文化活動的繽紛多彩僅僅是分殊現象,故不同文化間可以互相取用,看待中西文化上,需要有一種多元平等的文化觀。
注釋
:①沈壽康.救時策[N].萬國公報,1895(87).
②張之洞.勸學篇[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③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1卷[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333~334.
④戊戌變法(一)[M].:49.
⑤丁偉志.“中體西用”論在洋務運動時期的形成與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94(1).
⑥鐘天緯.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刖足集·內篇[M].
⑦戊戌變法(四)[M].:488~489.
⑧曹躍明.近代中西文化問題與梁漱溟的文化觀[J].天津社會科,1994(1).
⑨張新民.視野交融下的哲學、宗教與科學——答香港城市大學鄺振權教授問[J].陽明學刊,2009(00):384~396.
[1]陳旭麓.論“中體西用”[J].歷史研究,1982(5).
[2]戚其章.從“中本西末”到“中體西用”[J].中國社會科學,1995(1).
[3]楊錦鑾.再論“中體西用”[J].暨南學報,1998(2).
[4]路新生.論“體”“用”概念在中國近代的“錯位”——“中體西用”觀的一種解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5).
[5]馮桂芬.校邠廬抗議[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6]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M].上海:三聯書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