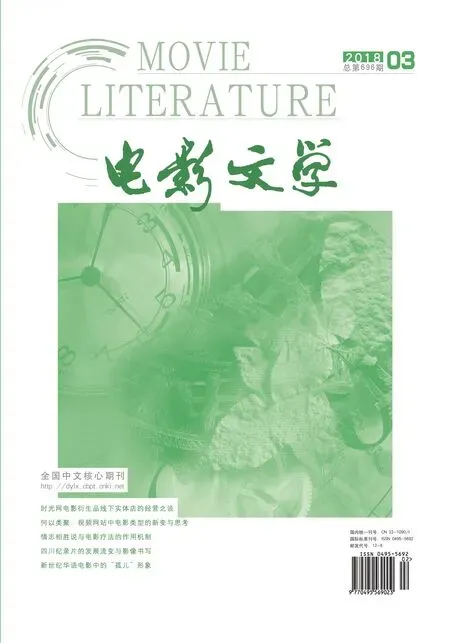好萊塢動畫電影對大眾審美的迎合
宋向華
(中原工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7)
好萊塢動畫電影已經經歷了百余年的風風雨雨,而一直在藝術和市場上保持著雙重的旺盛生命力,成為美國文化輸出霸主地位的有力支持者,也是美國精神的文化符號之一。在探究好萊塢動畫電影成功的原因時,我們必須承認,好萊塢動畫電影對于大眾審美始終有著高度的迎合,當大眾審美發生嬗變時,好萊塢動畫電影也會做出相應的調整。一言以蔽之,在美學理念、美學品質乃至審美價值上,好萊塢動畫電影在有所堅持的同時,又始終都針對著自己最大的受眾群體,年復一年地帶給全世界觀眾巨大沖擊。
一、好萊塢動畫電影與大眾文化領域
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好萊塢動畫電影與大眾文化之間具有與生俱來的密切關系,它基本上是無法脫離大眾審美而存在的。
審美是一個處于動態中的、抽象的概念。就個體而言,它既是與個人的心理結構、成長經歷以及所處時代、社會環境等相關的思維和情感反應,對于具體個體來說,它又是處于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中的。而在千人千面的個體審美之外,又存在一個屬于群體的大眾審美。大眾審美“不僅在于承認事物是美的,而且還要注意所有美的東西都必須有與之相適合的整體,因此趣味不是這個意義上的共同性感覺,即它是自身依賴于一種經驗的普遍性。依賴于他人判斷的完全一致,趣味并不要求每個人都同意我們的判斷,而是要求每個人都應與我們的判斷相協調”。可以說,大眾審美體現了人們在面對審美對象時的一種最為普遍的共同反映,它也代表了特定的社會或時代的審美風貌,相對于個人審美而言,它是相對固定的。
動畫電影作為一種物化了的藝術品,無疑是一個能使人們進入審美活動之中的對象,它的生產本身代表了創作者主觀的審美意識,而它的接受則反映了大眾對于這一藝術文化的回應程度。一貫有“夢工廠”之稱的好萊塢電影被視為當前世俗娛樂王國的締造者之一,其電影的制作具有強烈的商業化意味,作為消費者的大眾始終是好萊塢電影高度重視的對象。甚至可以說,與其說好萊塢電影是一種藝術性的創造,不如說更是一種針對市場投放的產品,好萊塢動畫電影也不例外。電影創作,無論是真人電影抑或是動畫電影,都依賴于一個復雜的工業背景和一定的商業支持。最早的好萊塢動畫電影,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動畫電影,由詹姆斯·斯圖爾特·布萊克頓導演的《一張滑稽面孔的幽默姿態》(1906)受技術和資金等條件的限制,僅有3分鐘時長。而到了30年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動畫長片,即沃爾特·迪士尼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時,電影已經有了完整的敘事、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屬于迪士尼的固有的歌舞表達特色。這背后的長足進步,實際上是脫離不了迪士尼等美國動畫人在《幸運兔子奧斯瓦爾多》(1927)、《威利號汽船》(1928)等作品中的摸索和總結的。在嘗試了種種甘苦后,迪士尼終于掌握了創建動畫奇跡的奧秘,即迎合大眾審美,并因此而聲名鵲起。以取材于格林童話的《白雪公主》為例,迪士尼一方面在故事的整體走向上,保留了原作中體現了民眾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如王子解救公主,王子與公主最終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等,同時又在電影細節的設定上,考慮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人強烈期待“邪不勝正”、和諧團圓的審美取向,削減了原著中的陰暗氛圍,只保留了皇后用毒蘋果毒害白雪公主的第三次謀殺。另外,迪士尼還憑借早前米老鼠系列動畫給觀眾養成的審美習慣,為電影加入了大量的音樂元素。在《白雪公主》成名后,動畫長片就成為迪士尼公司的主要經營方向。可以說,自迪士尼等美國動畫前輩篳路藍縷至今,迎合大眾審美一直是美國動畫人創作的寶典。
除了在銀幕上為各年齡段的觀眾編織夢境之外,當全球化時代,消費主義已經全面蔓延到包括電影在內的各個文化領域中時,好萊塢的動畫電影又將營銷的目標對準了主題樂園、周邊產品、網絡媒體等領域,不斷地在構建品牌產業鏈上做出積極的努力,最終形成了一個以迪士尼、皮克斯、夢工廠等新舊動畫巨頭,以及藍天工作室等動畫新秀先后崛起并長盛不衰的動畫帝國。無論是在商業抑或在藝術上,好萊塢動畫電影當前在業界的執牛耳地位都是無法撼動的。而這一切,都是與好萊塢動畫電影對大眾審美有著充分的研究,并不斷對其進行迎合有關的。
二、好萊塢動畫電影的迎合策略
我們在明確了好萊塢動畫電影對于大眾審美有著先天性的迎合趨勢之后,就有必要來具體探討其迎合大眾審美時的具體策略。
(一)世界觀
好萊塢動畫電影深諳觀眾需要一個與現實世界迥異的幻想世界的審美需求,并且在發揮幻想塑造這樣一個異質世界時,充分考慮到觀眾的接受趣味。如《海底總動員》(2003)中的深海,《冰川時代》(2001)中的冰河時期,《機器人總動員》(2008)中未來荒蕪的地球等,都是能給觀眾帶來新奇感的,但是電影中人物所表現出來的親子之情、友情和愛情等,又都是與現代觀眾熟悉的情感毫無二致的。
(二)價值觀
好萊塢動畫電影在電影主要人物的個性舉止的塑造中往往都反映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一旦主要人物違背了觀眾認可的價值觀,那么這將直接影響觀眾繼續參與審美的意愿。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并非一成不變的,在這一點上,好萊塢動畫電影也能夠敏銳地捕捉到一種最為普適的價值取向,并且以一種較為委婉、幽默的方式對此進行體現。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迪士尼的“公主電影”在數十年來清晰可見的價值觀流變。女性從最早的如《仙履奇緣》(1950)中的被保護者到《花木蘭》(1998)中自立自強、救國救民的大英雄,甚至王子與公主的愛情模式也早已被女性所拋棄,如《冰雪奇緣》(2013)、《海洋奇緣》(2016)等。但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又是被動畫人隱藏于令人捧腹的敘事之中,是需要批評者進行猜謎式深入解讀的。
(三)故事情節
大眾走入電影院進行消費的心理基礎是追求放松和刺激,因此在故事情節的設定上,好萊塢動畫電影一般秉承著兩大原則:一是邏輯清晰,敘事完整,同時又曲折動人,能夠高度集中觀眾的注意力。甚至在具體的矛盾設置、時間節點的安排上,都有著幾近流水線般的嚴酷規定。這方面最典型的便是《瘋狂動物城》(2016),電影甚至在影響主人公命運的大沖突、小沖突等的設計上都嚴格到分鐘。二是情節的基本走向是積極向上的,主人公往往在一部電影中只完成一件主干事件,而這一事件最終都以圓滿結束告終,主人公或是成功完成了一項任務,或是完成了一次冒險,或是實現了自我的成長,或是兼而有之。如在《瘋狂動物城》中,主干事件是食肉動物的失蹤案在兔朱迪和狐尼克的努力下偵破,就兔朱迪和狐尼克而言,他們各自加深了對彼此的認識,變得更為成熟,也在動物城中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生存位置,而就作為一個理想國存在的動物城而言,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之間的歧視現象也得到了緩解,動物們進入一種更和諧友善的關系中。
(四)視聽形式
在技術的層面上,好萊塢動畫電影相比起更為保守的中日等國的動畫電影來說,可謂是始終得風氣之先。在《獅子王》(1994)將二維動畫電影推向登峰造極之地時,皮克斯和迪士尼馬上聯手推出了3D動畫《玩具總動員》(1995)。而同樣是3D動畫,觀眾又不難發現夢工廠在數年之后推出的《怪物史萊克》(2001)已經在視覺上相比《玩具總動員》取得了令人驚嘆的進步。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動畫人更是開始積極嘗試真人與動畫結合的拍攝方式,如以一個兒童演員加全部綠幕和CG動畫完成的《奇幻森林》(2016),其以假亂真之處令觀眾瞠目結舌,極大地滿足了觀眾追求“奇觀”的審美要求。
上述策略帶來的效果就是,就具體的好萊塢動畫電影而言,其目標觀眾中成人與未成年人的比例是不盡相同的,好萊塢動畫電影一方面為了實現“合家歡”而保持身處主流審美中不越雷池一步,盡量給予未成年人正面的影響,這使得好萊塢動畫電影難免帶有啟蒙文本的色彩;另一方面它又避免了在施加這種影響時使自己置于某種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
三、迎合之外的獨特與從容
在充分肯定了好萊塢動畫電影的創作始終是以大眾審美為風向標的同時,我們又必須注意到,在好萊塢動畫電影和大眾審美的關系上,前者并不總是處于被動地位的。應該說,好萊塢動畫電影在順從于社會主流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同時,又潛移默化地通過不斷給大眾制造愉悅和快感,影響著大眾審美。
絕大多數好萊塢商業電影是放棄精英化立場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沒有嚴肅深沉的言說,或是技術上逆潮流而動的“復古”,動畫電影亦是如此。如史蒂夫·斯皮爾伯格的《誰殺了兔子羅杰》(1988)帶有鮮明的后現代主義色彩,而如夢工廠和百代聯手推出的黏土動畫電影《小雞快跑》(2000),萊卡工作室出品的定格動畫《久保與二弦琴》(2017)等則在3D動畫當道的今天進行了可貴的技術復古,并且這種復古反而讓人耳目一新,也同樣受到了大眾的認可。而與之相類似的則可以參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進行的,同樣在思想內涵和藝術魅力上下功夫的“試驗性動畫”,單純就藝術品質而言,這一類動畫電影不乏佳作,但結果卻都因為曲高和寡而乏人問津,完全無法在經濟效益上與好萊塢相抗。
還有一部分“作者”電影讓我們看到,好萊塢動畫電影并不全然采用狂歡式的,迎合大眾觀影口味的敘事文本。在部分好萊塢動畫電影中,觀眾不難發現其一反其他動畫電影滑稽可笑的人物塑造和引人入勝、輕松愉快的情節設置,而帶有主創非常個性化的語言態度。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蒂姆·伯頓的電影,如哥特意味極其濃厚的《文森特》(1981)、《圣誕夜驚魂》(1993)、《僵尸新娘》(2005)、《科學怪狗》(2012)等。這一類電影盡管是小眾的,但好萊塢依然給它們留下了一席之地。而從大眾的反饋來看,伯頓的上述電影也絕非失敗之作。伯頓之所以能以“不迎合”而實現“迎合”,正是與包括伯頓在內的好萊塢電影人多年以來影響、塑造了一類寬容哥特的大眾審美分不開的。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評價好萊塢動畫電影,相較于更為多元也更為混亂的真人電影而言,它在“新瓶”“舊瓶”,“新酒”“舊酒”中總能找到相對平衡的創作路線,在對大眾進行迎合之外又保持了一種獨特而從容的姿態。
美國前國務卿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經表示,羅馬獻給世界的是法律,而美國獻給世界的則是科技與大眾文化。盡管此言論值得商榷,但美國的大眾文化上的影響力確實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就好萊塢的動畫電影而言,它在熟知大眾審美的同時,迎合大眾審美,并最終參與塑造大眾審美,以至于一百多年來經久不衰,最終在產業化運行方面達到高度發達的程度。而好萊塢動畫電影也在對過往經驗教訓的總結中,試圖證明迎合大眾審美并不代表媚俗。可以說,當中國動畫在歐美和日本動畫的夾縫中艱難求生時,好萊塢動畫電影無疑為中國動畫提供了寶貴的創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