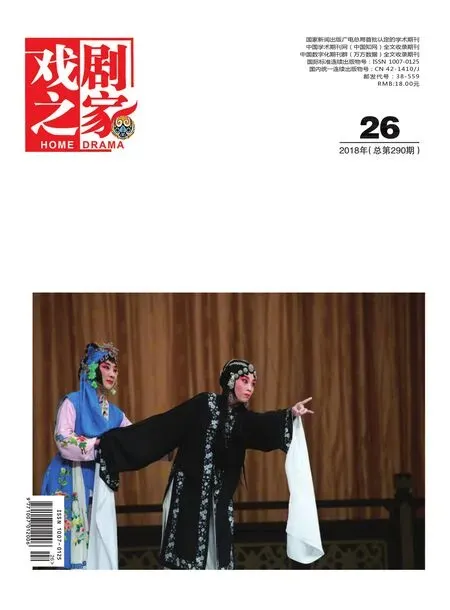論《羅拉快跑》敘事結構的創新思考
王靖一
(遼寧大學 遼寧 沈陽 110000)
一、《羅拉快跑》的板塊式結構
《羅拉快跑》突破了傳統電影理論上“等同于情節的電影結構”,它將傳統意義上的情節結構藏于復雜系統結構之中,《羅拉快跑》的劇作結構是板塊式的結構,采用分段敘述講述同一人物的不同命運。《羅拉快跑》的非傳統式結構對二十一世紀的電影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一)游戲式的板塊結構
影片的開頭部分出現了這樣的一段字幕:“一個游戲的結束,也就是另一個游戲的開始。”沒錯,你完全可以把這部影片理解成為三場“闖關游戲”,但是在這種通俗易懂之下,它以游戲式的板塊結構把“三場游戲”重組成了一場對人生、對宿命、對世界的重大思辨。導演湯姆·泰克沃在與電影結構玩一場游戲,不過與其說是游戲,更不如說這是一場與傳統電影結構的一場斗爭。它是不嚴肅的游戲,但它也是最莊嚴的革命,是與傳統電影結構的革命、是與傳統敘事方式的革命、是同“動畫電影與真人電影相分割”這一概念的革命。游戲化的結構構成也正預示著二十一世紀意識形態衰落感,不難發現,在影片結構中存在的一些元素,劇烈激蕩的音樂、紛繁快速的剪輯、后現代主義的創作感,無一不在號召《羅拉快跑》是一部新時代的電影,它的非整一性的結構賦予了電影屬于視聽時代的鮮明烙印。電影結構系統本身具有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非整一情節結構擊退了傳統電影結構的完整性、統一性、封閉性。在“羅拉要在二十分鐘之內穿過這座城市把十萬馬克交給曼尼”這一整體規定的有力約束之下,三大板塊的系統結構空間展開爭奪,最后構成三個“平行時空式”板塊把結構“權力”重新分配,敘事各自獨立,巧妙的是,三個板塊幾乎沒有敘事上的關聯,但每一個板塊都有傳統敘事結構的起承轉合,在散中求整,又將整打散。以影片的主題立意,使這三個板塊渾然一體,構成了一部帶有哲學思想的動作電影。
《羅拉快跑》的游戲感遠遠大于它的故事感,它超脫了事件發展的正常思維。三大板塊各自獨立,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聯系的,導演在實際上建立起了每個板塊之間的聯系,只不過聯系是細微的、不易察覺的。比如羅拉本是不會用槍的,在“第一次奔跑”中,正在搶劫銀行的曼尼教會了羅拉扳開槍的保險,而戲謔的是,羅拉在第二次奔跑中熟練地扳開了槍的保險。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這樣在劇作中實現了,不是變了魔法,也不是擁有仙術,而只是把人們認為“那么做不是對的”的事情做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這種“游戲般”的聯系其實就是想告訴觀眾:我是故意的。盡管他看起來像是以一種游戲般的態度來“玩弄”這部電影,其實導演是十分嚴謹的,三大板塊式的結構是本片走向二十一世紀不可磨滅的光輝,可最亮之處也最難處理,那就是三個段落之間的銜接問題,影片中的三次奔跑用“兩次冥界”來相接,造成了影片具有連續性的假象。同時通過在“兩次冥界”中改變影片節奏,讓配合羅拉奔跑的快速的節奏突然慢下來,來調整觀眾的心情,給予觀眾更多的對上一段落的思考和對下一個段落提出疑問的時間并在被紅色色調覆蓋下的裸著的羅拉和曼尼的對話實現這部動作電影的抒情性:我們的一生就這樣匆匆碌碌的跑著,直到離開,才肯慢下來。
它是游戲式的板塊結構,但湯姆·泰克沃絕對不是以游戲的態度來吹響這聲新時代電影事業的號角的。
(二)板塊式結構與蝴蝶效應
影片的板塊式結構引發了我們對蝴蝶效應的思考,事物發展的結果對起初條件具有敏感的依賴性,初始條件的差別會極大的差異,說明事物的復雜性。羅拉的三次奔跑像是羅拉玩了三次游戲,每一個關卡選擇的不同導致了游戲結果的不同,即劇中人物的命運的不同。“牽一發而動全身”,羅拉所經過的那些關卡,樓梯上的大兇狗、推嬰兒車的老太太、父親公司中的摩登女郎、拿走十萬馬克的流浪漢,不僅他們的存在決定了羅拉和曼尼的命運,而羅拉的奔跑也決定著他們的命運,影片簡潔自然地分別用幾個鏡頭來呈現出這些人今后的人生,但三個板塊中這些人“每次人生”都不同的命運自然而然的把蝴蝶效應的原理呈現在觀眾面前,命運的蝴蝶效應也與板塊式的結構相輔相成,以游戲化的方式來敘事,寥寥無幾的臺詞,西方經典電影中并不少見的營救式的故事模式,可關于命運、關于這個世界的未知感,關于無以名狀的操控力,這一切都浮現出來,這是影片游戲式板塊結構所帶來的主題的意念化、流動化。《羅拉快跑》的游戲感增強了影片想表述的命運感,諷刺性和質問性,諷刺這無可預知的命運,質問這何去何從的人生。
《羅拉快跑》不只在講述蝴蝶效應中事物發展的復雜性,也講述了蝴蝶效應中事物發展的偶然性。當然,復雜性和偶然性是不可分割的,羅拉營救男友曼尼這一過程是復雜的,但是在這過程中存在的每一過程又是偶然發生的,具有巧合性,比如營救發生的前提條件是曼尼的錢袋子被流浪漢拿走,而在第三次奔跑中,曼尼又遇到了流浪漢并順利拿回了錢袋子,與羅拉完成了雙重營救。《羅拉快跑》通過它事物發展的偶然性的情節選擇安排告訴了觀眾一個道理:相遇即緣。
(三)時間維度與結構的關聯
時間是操控影片的一種手段,一部影片能夠完成一整段人生甚至幾段人生的講述,電影利用蒙太奇手法和人類對時間的心理暗示來對結構和總時長進行分割規定。在《羅拉快跑》中,影片開頭就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整部影片的旁觀者銀行警衛舉著一只手對觀眾說:“游戲開始了,游戲只有90分鐘,這就是全部,其余的都是扯淡了。”有深意的是,這句臺詞實際上出自帶領德國足球隊在1954年世界杯足球賽上奪冠的教練之口,對于在二戰中一敗涂地的德國人來說,這九十分鐘帶來的勝利具有重振信心的重大意義。而影片中一開始就強調時間的概念,可以看出導演個人對時間的感受異常的敏銳,影片中多次時鐘的出現增強了觀眾對20分鐘這一時間的限定心理暗示,更加刺激觀眾的大腦,故事中虛擬的20分鐘的時間剛好就是現實中的20分鐘的時間,就是說羅拉的每一次奔跑大概用了20分鐘的時間,放映時間與故事時間關系緊密,這樣的處理能使觀眾感覺到“舒服”,因為他們的心理暗示時間在影片中得到了證明。無疑羅拉這20分鐘的奔跑在電影史上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的,意味著女性不再是“英雄救美人”中的被動者;意味著電影技術將推陳出新又將多種形式融會貫通;意味著電影突破傳統結構時代的到來。在傳統意義上,能讓觀眾舒適觀影的時長大約為90分鐘到120分鐘,但是《羅拉快跑》利用時間心理學的概念對影片的結構進行創造,以三段20分鐘的時間完成了現實時間與故事時間的突破。人類有一個永恒的難題就是無法控制時間的流逝,但是電影藝術創造出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我們可以操控時間,時間都是我們的,電影是時間的藝術,電影是藝術的藝術。
二、結語
電影是一門時間的藝術,實質上每一部電影都是在與時間抗爭。而德國電影《羅拉快跑》,以時間概念為支撐完成了對電影結構的創新突破,一輪鐘表為限定,大膽地以游戲的模式提出了“我是誰,從何處來,到何處去”這一永恒論題,面對這一論題,《羅拉快跑》沒有直接給出答案。生死往復,循環不止,所有的答案都在那一輪時鐘和奔跑的命運身后。《羅拉快跑》是探索性的電影,它以它獨特的結構、意念化的主題呈現、時間學的靈活滲入征服了傳統,將新時代的電影在1998年呈現給世界。《羅拉快跑》結構上的設定可能會引領電影甚至戲劇的未來發展,故事不再是由創作者規定的,觀眾有權利續寫每一段情節,未來的劇作情節一定是觀眾選擇性的安排,這是蝴蝶效應影響劇作的一個開始,你看,沉浸式戲劇已經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