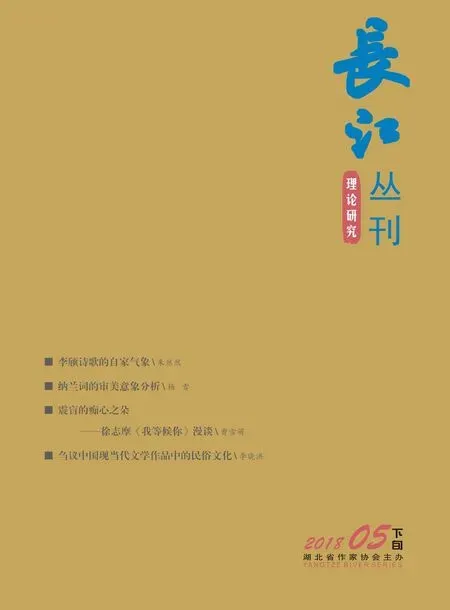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中國文化因素研究
■劉曉穎/信陽師范學(xué)院外國語學(xué)院
日本的俳句是世界文學(xué)中最短小的格律詩之一。俳句原本是一種詼諧的應(yīng)答,一種對和歌、連歌的模仿和戲謔,誕生之初并不能入世界文學(xué)的主流,甚至是某種意義上卑俗的存在,直到松尾芭蕉的出現(xiàn),俳句才正式成為一種有審美價值的文體,正式進(jìn)入文學(xué)藝術(shù)的殿堂,松尾芭蕉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實(shí)踐,開創(chuàng)了日本俳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一、禪宗,佛我同一,物我雙忘
詩能引導(dǎo)我們我們走向禪宗的智慧與平靜。日本文學(xué)史上最有名的俳句《古池》,即出自松尾芭蕉之手。當(dāng)時,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學(xué)思想對亞洲的日本、朝鮮、越南等鄰邦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日本。因此這位“俳圣”的創(chuàng)作靈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松尾芭蕉尊崇李白,喜讀老莊,杜甫,故而,其思想性、表達(dá)風(fēng)格、意境營造清晰反映出中國 宗教思想深刻影響印痕。“古池,青蛙躍入,水聲響”,這首俳句平淡簡單,但靜心品味方覺優(yōu)美之至,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細(xì)細(xì)品讀你會發(fā)現(xiàn)一幅青蛙與舊池塘的景象躍然紙上,點(diǎn)睛之筆在于最后的水聲響,讀者似乎聽到了那一聲清澈簡練的撲通,短短三行字,畫面聲音動態(tài)兼?zhèn)洹K晌舶沤队米钇椒驳脑~藻,記錄了最平凡的一個瞬間,就好比李白的《靜夜思》淺顯易懂,卻能經(jīng)久不衰。這首俳句贏在樸實(shí)生動,青蛙跳入池塘的動作千萬次,但只有松尾芭蕉記錄了下來。
二、含蓄內(nèi)斂,借景抒情
俳句的興盛似乎是大和民族的某種特性的必然結(jié)果,他們有對季節(jié)、風(fēng)物的敏感和含蓄內(nèi)斂。比方在茶道和花道中,他們就講究所用的茶具、花,一定要符合當(dāng)時季節(jié)的心情,例如:櫻花祭,紅葉狩,從這些都不難看出。同樣的,中國詩歌,特別是抒情詩歌也很擅長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fēng)直到夜郎西。”“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樣的描寫方式為讀者展開了一幅美麗的畫卷,然而在這充滿詩意的景象中,包含了怎樣的感情,誰的感情,就要讀者自己去體會去思辨了。筆者一直認(rèn)為,我們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去不斷接受新鮮的東西,因此沒有什么是值得反復(fù)看反復(fù)研究的,除了詩詞。在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境遇里讀同一首詩詞,感受都大不相同,這是中國古詩詞獨(dú)特的魅力。日本俳句短小精悍的藝術(shù)形式必須采用這樣的方式,他常常追求一種欲罷還休,欲言又止的感覺,因此,俳句的創(chuàng)作便從這種中國古詩詞的表達(dá)方式中汲取營養(yǎng),松尾芭蕉有一膾炙俳壇的名句“春將歸,鳥啼魚落淚”,這不僅讓人想到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兩者均以情融景,將傷感春事的愁緒,自然而然的帶到身外之境,又如,松尾芭蕉說:“讓憂郁的我寂寞吧,子規(guī)鳥”,李白有“誰忍子規(guī)鳥,連聲向我啼”,二人也同樣是心中憤懣不平,壓抑不痛快,但又不甘寂寞,于是將子規(guī)鳥變成了自己精神思想的外化,以此寄意于物。
三、物哀,幽玄,閑寂
日本人的審美意識,主要分為這三點(diǎn):物哀,幽玄,閑寂。松尾芭蕉的紀(jì)行之作《奧之細(xì)道》便大有“人生如旅”,“閑寂之美”的意思。開篇序言中“月日者百代之過客,來往之年亦旅人也。有浮其生涯于舟上,或執(zhí)其馬鞭以迎老者,日日行驛而以旅次為家”,這算是他“人生如旅”的集中體現(xiàn)。此外,芭蕉翁的“無常觀”也在書中得以體現(xiàn),“春有芳草夏有蟬,秋有明月冬有雪”,季節(jié)與物序的更迭,凸顯時間無常,更道時間永恒:“人生如旅,草庵易主,日日行驛,處處棲身”。于芭蕉翁而言,空間必定是無常變幻的。而這兩者的無常變幻,直接導(dǎo)致人生的變幻無常,“前途遙不可測。雖抱病出行,將入窮鄉(xiāng)僻壤,卻常思現(xiàn)世之無常,已抱定舍身之念。即使旅途死于道中,亦為天命。”一語成讖,1694年,松尾芭蕉寫下最后一句“旅途罹病,荒原馳騁魂夢縈”。芭蕉先生對死亡的感受竟是“荒野馳騁”,也許對他而言,人生真如幻夢一場罷。
四、發(fā)展背景相似,意境相通
日本俳句和中國古詩詞有很多意境相通之處,這不僅僅是在表現(xiàn)手法上,而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俳句產(chǎn)生的時期,文人的地位十分低下,這和當(dāng)時的中國一樣,封建等級森嚴(yán),他們有的人四處漂泊,居無定所,有的人宦途失意,逃避現(xiàn)實(shí),因此出現(xiàn)了文人傲嘯山林的現(xiàn)象,自然地,中國古詩詞的意境便披著俳句的外衣在日本文壇登場了。我們要承認(rèn)的是,大和民族的確是一個善于學(xué)習(xí)的民族,特別是在漢、唐這樣的中國古代的鼎盛時期,中國以一個施予者的姿態(tài)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文化,因此,中國古詩詞的精髓便深深滲入了日本文化,日本作家詩人都以通曉漢文為尊,松尾芭蕉亦是如此。杜甫有詩云:“門泊東吳萬里船”,芭蕉便將自家草庵提名“泊船堂”,松尾芭蕉寫道:“江戶客居已十霜,便指是故鄉(xiāng)”便是受賈島“客舍并州已十霜,卻指并州是故鄉(xiāng)”的影響。
五、結(jié)語
我們不難看出,松尾芭蕉甚至是整個日本文壇受中國文化影響頗深,松尾芭蕉的俳句淺顯易懂,卻猶如醍醐灌頂,這些俳句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文字優(yōu)美,而且貴在激發(fā)心境,有人說俳句不如唐詩宋詞,筆者認(rèn)為雖然中國文化影響著俳句,但俳句本身也是一種特別的存在,唐詩宋詞有嚴(yán)肅規(guī)整之大氣磅礴,但不能否認(rèn)俳句清新自然也是一種美,文學(xué)作品或有高下,但文學(xué)形式?jīng)]有,就如同黛玉葬花和湘云醉臥,各有其美,我們靜靜欣賞就好。
參考文獻(xiàn):
[1]殷玥.論松尾芭蕉俳句悲秋意象的抒情性[J].文化學(xué)刊,2017(12):59~62.
[2]蘇珊.松尾芭蕉的禪思想的形成及其展開[D].南寧:廣西大學(xué),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