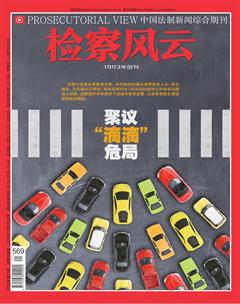出行糾紛先弄清網約平臺的法律責任
肖天存

從審判實踐看,“滴滴”類網約車平臺產生的民事糾紛大多集中在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車費糾紛及司機與乘客間人身損害賠償等方面。不同的糾紛類型及網約車公司不同的營銷模式,會影響到其最終是否擔責。以“滴滴”為例。
首先,當事人以運輸合同糾紛為由起訴要求賠償時,“滴滴”平臺公司為適格被告。
根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16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應當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可見,“滴滴”平臺作為網絡車平臺公司,一般情況下其法律地位為承運人(順風車除外)。
基于“滴滴”平臺公司的承運人身份(順風車除外),在此過程中圍繞履行運輸合同產生的爭議應屬于運輸合同糾紛。因此,一旦當事人選擇以“滴滴”平臺公司違反運輸合同為由起訴,則其為適格被告。
“滴滴”平臺司機與乘客間發生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時,此類糾紛存在和交通事故侵權競合的情形。如果乘客選擇侵權之訴,但應直接起訴實施侵權行為的司機,此時“滴滴”平臺公司不是合格的訴訟主體;而一旦乘客以運輸合同糾紛為依據,選擇提起違約之訴,則承運司機和“滴滴”公司為共同被告,如違約事實屬實,則“滴滴”平臺公司會因此被判擔責。
其次,若對簽約司機及車輛審查不嚴,“滴滴”平臺公司可能會在乘客起訴賠償時受到牽連。
2017年1月13日下午,呂某通過手機利用“滴滴”打車軟件叫車,車牌號為“蘇E271××”的出租車應招接單,呂某于當日17時50分從虎丘區合晉世家站點上車,22分鐘后到達目的地玉山路水上樂園公交站。呂某下車后發現手機丟失,遂報警求助。
該案起訴到法院后,呂某在庭審中主張本案是侵權之訴,認為“滴滴”平臺公司作為網絡交易平臺,面向社會公眾提供網約出租車的服務,直接關系到社會公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故其本應盡到嚴格的審慎義務,對登記的車輛和車主進行嚴格的審核和登記,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廣大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呂某指出本案“滴滴”平臺公司沒有盡到該義務,導致出現假牌照的假冒出租車為其服務,在其財產遭受損失時,平臺不能提供該車輛真實信息,以致其在向警方求助時,警方因為該車是假牌照而無法采取相應的措施,致使其遭受了經濟損失,故平臺公司應予賠償。
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無論本案是屬于運輸合同糾紛抑或是侵權責任糾紛,“滴滴”平臺公司都應當對經平臺許可的車輛進行審查,以確保乘客的人身及財產安全。如果因為其未盡審慎的審查義務致使沒有資質或者不符合營運條件的車輛進入平臺并最終導致乘客遭受人身或財產損失,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案雖因呂某在車上丟失手機的證據不足被駁回起訴,但此類案件中,如果乘客盡到相關財產損失舉證證明義務,“滴滴”公司經查實確未盡審查義務時,將會難免賠償責任。
再次,對于僅提供中介信息服務的拼車行為,“滴滴”平臺公司一般無須承擔相關責任。
根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8條規定,私人小客車合乘,也稱為拼車、順風車,按城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執行。
朱某系經“滴滴”出行平臺注冊的順風車駕駛員。2016年9月16日7時40分,李某通過“滴滴”平臺與朱某達成順風車協議,由朱某將李某從揚州市祝大廟遺址送至南京市攝山星城菜場,乘客應付119.1元。朱某接單后駕駛小型客車載著李某前往約定目的地,當日上午8時55分,朱某駕車沿滬陜高速(江六段)由東向西行駛至386公里附近時,因對前方路面動態觀察不夠,未確保安全行車,與莊某駕駛的大型客車發生追尾,致兩車不同程度受損、乘客李某受輕傷的交通事故。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八大隊出具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朱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莊某及李某均無責任。此案歷經兩審法院審理,朱某提出“滴滴”出行平臺提供信息、適當收費,與其構成了新型的雇主和雇員的關系,故其在履行職務過程中對他人產生損害的,應由雇主即“滴滴”公司承擔賠償責任。一、二審法院均未采納朱某要求“滴滴”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抗辯意見……
從本質上說,順風車這種私人小客車合乘模式,屬于合乘各方達成的共同乘車的民事行為。是在乘客自己本要行走的路線上捎帶順路合乘者,僅作為出行成本的分攤。這里“滴滴”公司收取的是信息服務費用,而不具有營運性質,其身份也不屬于承運人。
在順風車訂單形成過程中,“滴滴”平臺只負責發布信息而不主動對車主進行派單,由車主自行匹配路線并接單,“滴滴”平臺就匹配成功的訂單收取5%的信息服務費。由此可見,“滴滴”公司僅是幫助促成交易,司機、拼車乘客與“滴滴”公司間具有居間合同關系性質,不是運輸合同關系。
雖然合乘是通過“滴滴”平臺促成的,但由于“滴滴”平臺公司只是合乘信息服務平臺,并非承運人。故一般而言,在沒有證據證明其對當事人間發生的侵權行為存在過錯的情況下,“滴滴”平臺公司無須承擔責任。此時,相關責任、義務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