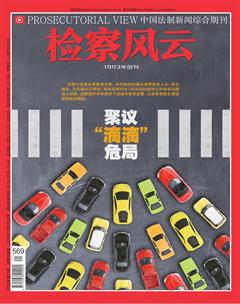順風車:更共享才能更安全
張亮
近日,“樂清姑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一事引發輿論憤議,但畢竟逝者已去,如果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安全保障措施其實是“滴滴”不可承受之重,共享經濟從來就不是單一主體能夠管好的。
首先,讓我們來捋一捋基本概念。網約車是近年來依托網絡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是區別于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新經濟業態。但網約車只是統稱,其實還要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通過互聯網技術拓展業務的巡游出租車。其二是以“互聯網+”形式開展的汽車租賃客運服務業務,也就是有全職司機的專車服務,如曹操專車、首汽約車、神州專車等。最后,才是私家車接入網絡平臺所提供的客運服務,其中的快車已被明確為是一種等同于出租車的營利性搭車服務,而只有相同路線合乘出行并分攤合理成本的順風車,才是真正的共享經濟活動。
雖然順風車的惡性案件時有發生,但不能因此否定順風車的服務功能,這是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很好補充,也符合“互聯網+”共享經濟的發展趨勢。目前仍要繼續支持順風車的發展,主要的激勵措施在于準入機制上,如通過放寬順風車準入門檻,簡化申請和管理系統,對稅收保險等費用參照一般家用車標準等措施,引導大眾積極參與其中。
當然,順風車作為一種共享經濟模式,在分擔合理車費的利益驅動下有效調動閑置的私家車資源,其正當性僅在于市場效率,如果不加限制,同樣會演變成一種低門檻的經營活動,也就是俗稱的黑車洗白,進而產生市場失靈,影響市場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順風車的適用范圍也必須進行限制,制度設計要把握“閑置資源”的核心要件,對具體的駕駛員資質、車輛權屬和安全、經營規模、收費標準等方面做出限制。
從數據上看,順風車發生兇案的案發率和案件數都遠遠低于出租車行業。但是,在大眾的風險認知中,由于順風車的準入門檻比較低,導致輿論認為順風車司機的素質更加魚龍混雜。再加上公眾對網絡信息技術的期待與信任,就當然認為順風車比傳統出租車更安全。前者的主觀意識,只能通過長期的社會教育和風險交流逐漸改善;而后者的安全機制,則可以盡快通過一系列技術措施積極改進。當然,在此必須強調的是,企業作為營利性組織,會極其重視成本與收益問題,如盲目要求順風車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技術來改善安全保障措施,直接后果就是逼企業因沉淀成本太高而退出這個市場,這樣反而又只能回到無從監管的黑車時代。
最近“樂清姑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事件中,公安部門和“滴滴”都對偵查時機的延誤負有責任。但是站在各自立場看,雙方似乎也都有合理事由。對“滴滴”來說,每天面對線上成千上萬的投訴,人工是不可能做到對信息的一一甄別與及時回復,也斷然不會因為第三人的口頭請求就提供運輸合同雙方的私人信息。雖然公安部門也在案發過程中一直配合受害人家屬聯系“滴滴”,奈何這個大企業“不通人情”,在公安部門未出示執法身份,也沒有經法定調查程序的情況下,就是不給特殊對待。試想,若公安部門和“滴滴”有建立良好的應急合作機制,那就不會在這種關鍵時刻出現場景匹配的偏差。
由于共享經濟所特有的網絡信息化要求,順風車要整合線下的閑散交通資源,實現信息對稱以及使用權的高效轉移,就必須依賴網絡平臺,而且目前各地政策都規定,順風車經營必須在已備案的平臺上進行。因此平臺經營者居于管理、信息、技術等優勢地位,已完全能監控線上順風車經營活動的全過程。但一方面,這些經營數據,若沒有法定情形,“滴滴”并沒有向政府開放共享的義務;另一方面,新近出臺的《電子商務法》明確,“滴滴”這類電子商務平臺對平臺活動應當承擔合理注意、安全保障、資質審核、記錄保存等第三方監管義務,否則不僅要承擔相應民事責任,還會面臨行政處罰。對此,順風車平臺已基本實現信息登記制度以及移動端的人臉、語音、指紋等身份識別技術。
綜上所述,政府與順風車平臺合作監管具備了充分的客觀條件和法定依據。除了這些法定義務之外,還可以更進一步,通過“因開放而免責”的制度導向,促進政府與平臺進行合作監管。針對順風車的案例,最緊迫,也是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智慧公安平臺與“滴滴”服務平臺的動態銜接技術與機制,在有調查需求時,可以實時發送交流請求,避免煩瑣的法定程序和身份認證,以便公安部門有條件地即時共享企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