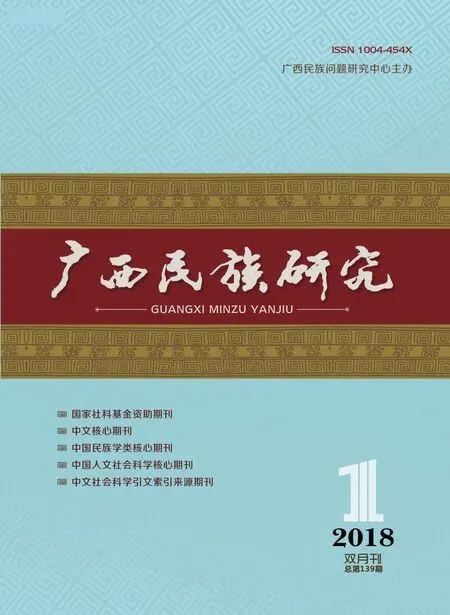廣西多民族雜居格局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動空間研究*
——廣西民族區域自治60年歷史經驗研究系列論文之二
楊 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以來,廣西壯族自治區之所以能夠在落實黨的民族政策、促進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以及各族群眾的全面發展上取得輝煌成就,與區內12個世居民族的團結和睦是分不開的,而廣西漢族與各民族嵌入雜居的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頻繁互動,則是廣西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基石。
一、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格局提供了民族團結環境
一直以來,廣西都居住有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等多個民族,形成了多個民族雜居的生活格局,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民族之間交往聯系越來越頻繁,各民族關系朝著和諧友好的方向發展。
廣西是全國壯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壯族主要分布在廣西中部與西部地區。壯族先民為百越的一支,這一支系的壯族祖先主要為駱越人與西甌。秦漢時期,居住于嶺南地區的先民稱為南越、西甌和駱越,西甌人面對強大的秦軍也有一戰之力,甚至被劉安稱之為“秦敗之引”。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臨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1]614
到東漢時期,西甌和駱越又被稱為“烏滸”“俚”。
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余萬內屬。[2]2842交趾、合浦烏滸蠻反叛。[2]2843
建武十二年,九真激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2]2846
到隋唐時期,“烏滸”“俚”的稱呼變成了“僚”或“蠻”。南宋時期,廣西北部、東部與中部地區的民眾被稱為“撞”,居住在欽州與左江區域的民眾又被稱為土人。
……牂牁、興古僚種復反。[3]503荊州極南界至蜀,諸民日潦子。[4]56
俚在廣州之南,蒼梧、郁林、合浦、寧浦(今廣西橫縣)、高粱(今廣東陽江等地)五郡皆有之,地方數。[6]212
明代,廣西西北部地區的僚、蠻人叫做“俍人”,西北部地區以外的民眾則被叫做“僮”。
廣西大藤峽、淥水、橫石等山,藤縣太平等鄉,徭僮嘯聚擄掠,甚為民害,乞選良將,多調官兵、俍兵攻滅之。[6]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余人。[7]345
到了清代,“僮”得到廣泛使用。而僮又被細分為布壯、布依、布土、布曼、布板等(皆為地方壯族的部落自稱)。20世紀50年代,按照語言文化、生活習俗、心理素質等特征,將其統稱為僮族,1965年,將僮族改成了“壯族”。由于歷朝歷代都實施“分而治之”的政治決策,加之壯族民眾抗爭意識不強,因而壯族都處于分散的狀態,并沒有建立過任何政權,長期以來壯族與漢族都保持和諧友好的關系。
在廣西的漢族先民主要來自于湖北、河南、四川、廣東等地,主要扎根于桂東北、桂東南,但在廣西其他區域同樣有漢族群眾聚居。隨著秦始皇命屠睢領軍攻打百越,移居廣西地區的漢族也越來越多,只是這一階段的漢族移民較為零散,為適應環境往往會完全融入其他少數民族當中。而在明清時期同樣也有大量漢族遷往廣西,其中以明代衛所軍戶制助推的漢族移民潮為主。通過科舉來桂的漢族官吏及家眷,往往居住于柳州、邕州(即南寧)、桂林,而因罪被發落、貶官來桂的漢族,則多數居住于鄉村地區,與駱越先民、苗瑤民族共同居住。
瑤族最早起源自歷史上長沙、荊楚地區的荊蠻,并在秦朝、西漢時期演變為了武陵蠻、長沙蠻或是五溪蠻,在南北朝后期,武陵蠻部落又分化出了莫瑤集團,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瑤族先民。[8]瑤族先民當時主要聚居于湖南北部的城鎮周邊,如岳陽、懷化、常德、益陽、桂陽等地,在廣西則主要居住于全州、富川等地,在廣東則主要聚居于連南、樂昌等地。在唐宋時期,漢文明開始加快了向西南方向擴張的腳步,這也使得瑤族先民被向外推到了桂東北地區,也就是廣西總部。在元代以前,桂林、靈川、臨桂等地方,都聚居了大量瑤族群眾,明清時期瑤族先民進一步向南方的遷徙,也使得廣西幾乎遍布了瑤族聚居點,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在清代中后期,瑤族在廣西地區的聚居地點基本趨于穩定,此時廣西大部分縣級行政區都已經存在瑤族聚居點。
在長沙地區生活的武陵蠻,同樣是苗族先祖。武陵蠻中的一些部落也被稱之為“苗眾”[9],但“眾”中也有許多不同名稱劃分。宋代學者朱輔提出,五溪蠻里也有苗族部分,分布在五溪之地的龍勝、資源、灌陽等地區。在唐末宋初、五代十國時期,一部分苗族群眾經由湖南西部與貴州東部的交界處遷徙到了廣西融水,而明末清初也有相當數量的苗族通過貴州遷居到了南丹與隆林,逐步穩定為今日苗族聚居的情況。[10]
聚居于廣西三江、龍勝地區的侗族群眾,其先民大部分來自于宋代中期到明初時期的貴州東南、湖南西部地區。而仫佬族則是以西南官話(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慶、貴州方言)為母語的漢族群眾與廣西土著僚人(壯族先祖)彼此通婚的后代,聚居地為羅城地區、柳城地區[11]。
“侗人居溪湖中,又謂之峒人。”[12]348“我們侗族祖先,落在什么地方,就在梧州那里,就在潯江河旁,從膽村一帶出走,來自名叫膽的村莊。……為尋生路離家鄉。”[13]31-32
毛南族則是各歷史時期湖南、山東、福建等地遷居至廣西的漢族與僚人通婚的后代,其聚居地一般集中于環江縣,在宋代則被稱之為“茅灘”,到了清代則自稱為“毛難”,直至20世紀80年代,根據歷史調查與毛南族的意愿,才更名為“毛南”。根據語言學家的調查,毛南族的族源很可能與壯族、仫佬族、侗族等同屬于壯侗語族的廣西世居少數民族,屬于古時“僚人”的后代。
“毛南語和壯語(北壯來賓語)相比,在456個詞匯中,有44個與壯語的聲韻完全相同,有141個的語音部分相同,語法結構則完全相同。再和仫佬語相比,在488個基本詞匯中,有79個詞匯與仫佬語的聲韻完全相同,有108個詞匯的部分語音相同,兩者語法結構大體相同。”[14]61-66
回族最早定居廣西則是從宋代、元代開始,到了清朝初年逐步增加,主要聚居于南寧、柳州、桂林地區。
“穿山清真寺是廣西歷史上最早的一座清真寺,建于元代初期。當年,元軍攻占桂林,在穿山、蘿卜洲、望城崗一帶戍守屯墾。這支元軍中有不少穆斯林。駐守桂林后,他們便在穿山東北麓建寺立坊,以滿足宗教生活需要。”[15]
從宋末廣西地方官員多見回族不難看出,至少在宋元年間,穆斯林就已經跟隨忽必烈下嶺南進入了廣西。
俺都刺,答失蠻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嶺南廣西肅政廉訪使。馬合漠,回回人,至順三年(1332)廣西道肅政廉訪使。忻都,回回人,天歷二年(1329)廣西廉訪副使。者林,回回人,至正中廣西行省左垂。慕薛,色目人,進士,至正間廣西行省員外郎。伯篤魯丁,答失蠻人,進士,至元三年(1266)廣西廉訪副使。[16]224-226
京族最早來自于越南吉婆群島,后來通過涂山地區進入廣西,主要聚居于中越邊境的防城港東興市。
“承先祖父洪順三年(即越南封建王朝年號,洪順三年為公元1511),貫在涂山,漂流到此……”[17]3
由于來自于越南,京族在解放前曾被稱為安南族、越族,而在解放后經過調查,被國務院批準統一了京族稱號。
“根據水族民歌的記載,水族先祖原本居住于邕江一帶的‘岜雖山’,后來在戰爭影響下被迫遷往河池、南丹,并隨后通過龍江北上貴州、廣西交界處,并開始從駱越諸部落中分離出來,向著單一民族發展繁衍。”[18]5
據史料記載,今水族聚居的東謝地區,“地方千里”,人口殷實,“土氣郁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糧食產量有較大增加,人們的存糧有了較多結余,能夠用來釀酒以供節日喜慶之用。這些都說明了水族先民自秦代遷入黔桂邊境以來,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在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的前提下,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質已逐漸形成,于是,水族作為單一民族正式形成了。[18]7
由于遷入時兵荒馬亂,遷居工作缺乏整體性,水族的聚居點顯得比較分散。
彝族主要來自于明初時期云南大理、貴州盤縣等地,他們在廣西的主要聚居點是隆林、那坡。
《左傳·桓公十三年》載稱:“楚屈瑕伐羅。”羅與盧兩部聯合起來大敗楚軍。后羅、盧兩部隨楚將莊蹻入滇,然后播遷西南各地,歷久演變,即成為今日的彝族。[19]10
仡佬族來自于貴州興義地區,但遷入時間較彝族更晚,主要是在清初定居廣西,目前定居于隆林地區。仡佬族族源較為復雜,目前學術界對仡佬族的族源、古代族稱并沒有定論,各方爭議較大。
廣西的多民族性,是遷入民族種類繁多決定的,而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則有效保障了各民族在彼此尊重生活空間的情況下更好地進行交流、互動乃至融合。
民族團結需要一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動空間。廣西自秦代以來,在兩千多年的移民運動中,尤其是漢族移民的入桂,形成漢族與各民族雜居的格局。
考察廣西的歷史,從秦漢到隋唐時期,漢族移民入桂,來自不同的地方,到達廣西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漢族支系。在桂北形成稱呼繁多的“桂北平話人”;宋代由狄青率領的軍隊為平定儂智高的起義入桂,其后裔在桂中、桂西形成“桂南平話人”;明代由軍屯制而形成的講西南官話的“桂柳人”;清代推行招墾政策時入桂形成的“廣府人”“客家人”和“高山漢”,與廣西少數民族嵌入雜居。此外,還有歷史上入桂的瑤族和苗族。
“在一起”才產生互動。經過兩千多年的移民運動,在廣西形成今天漢族與壯、瑤、苗、侗等少數民族嵌入雜居的大格局,從而為廣西民族團結建構了便于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動空間。
二、文化交流拉近了各民族間的心理距離
(一)風俗上的交往與融合
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因為自然、氣候、地理位置與周邊文化的影響,會形成各種各樣的生活習慣與民族文化,最終成為一個完整的、難以被外力改變的生活習慣體系,也就是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主要體現在服裝、審美、婚戀、節慶、宗教等等。[20]就廣西本土的情況來看,由于廣西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雜居的地方,少數民族不但被中原的漢文化所影響,同時各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也存在彼此影響的情況。所以,不同少數民族具有相同的風俗習慣的情況在廣西并不罕見,譬如瑤族與壯族、侗族的傳統建筑都是干欄式建筑。廣西的侗族群眾深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影響,在風俗上的表現就是與壯族、毛南族一樣有“不落夫家”的婚戀習俗,這點在老撾的侗族分支“康族”以及越南的“抗族”身上并無體現。
苗瑤地區的先民原本聚居于洞庭湖周邊的平原地區,居所一般也是以深地基的泥瓦房為主。然而來到廣西居住之后,由于廣西地區丘陵密集,不得不居于山中,所以為了避免濕氣侵襲、蛇蟲鼠蟻的滋擾,苗族與瑤族等群眾也開始學習壯族群眾,建起了干欄式建筑。都安的布努瑤歌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壯族傳統歌圩的影響,甚至連演奏器樂的銅鼓也是來自于廣西本土的駱越文化。
在節慶方面,原本不同少數民族都有獨特的節日,節日來源、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但由于多民族長期雜居,廣西的各族群眾也逐漸在漢文化影響下,將春節、清明、中秋、重陽等節日作為本民族的重大節慶之一。當然,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在廣西同樣具有極大影響力,如農歷三月三不僅是壯族傳統的歌圩,也是侗族傳統的花炮節、苗族傳統的“三月三節”等等。即便日期相同,但不同民族的節日文化、由來卻并不一致,如壯族的三月三歌圩又被稱為“歌婆節”,主要是為了紀念農歷三月三成為“歌仙”的劉三姐;苗族的三月三節來源于伏羲與女媧在農歷三月初三相會的傳說;侗族的三月三是為了紀念上古時期侗族先民因忘記及時插秧而逃荒的歷史傳說等等。但由于廣西地區各族雜居,所以當傳統盛會來臨時,各族群眾除了慶賀本族節日,也會向其他民族的群眾道賀甚至是一起過節。風俗方面的彼此融合,是廣西各族群眾實現和諧共處的重要條件。
(二)語言上的交往與融合
語言是人類溝通交流的必要工具,無論哪個民族的交流、交往都需要通過語言來實現。但廣西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區,語言類型非常豐富。除了回族群眾與漢族群眾一樣說漢語之外,廣西其他10個世居少數民族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乃至不同聚居地的同一民族,也有方言上的微妙差異。在廣西,各民族雖然語言上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間的交流障礙并不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長期雜居的各族群眾就已經有了相互學習語言的情況,地理位置接近、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民族間更是如此。最能夠體現這一特點的無疑是在廣西以“大雜居、小聚居”分布的侗族群眾,由于他們長期與漢族、壯族、苗族、瑤族群眾共同在一個區域生產生活,彼此之間的溝通頻率也非常頻繁,所以很多侗族群眾不僅掌握了漢族的語言文字,還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苗語、瑤語、壯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漢語普通話的推廣普及進一步化解了不同民族群眾之間的溝通障礙。廣西許多少數民族群眾(特別是青壯年)都具備流利使用多種語言、方言的能力。譬如在南寧地區,就有大量漢族、壯族群眾同時能夠掌握白話(粵語方言)、平話以及壯語,以滿足自身日常生產生活的交流需求。[21]在語言上的融合、互動,進一步加強了各民族和諧共處、團結一致的良好環境。
通過學者研究不難看出,各民族的語言通過長期溝通交流,彼此存在一定影響,一種民族語言中的一些特定詞語不難在其他民族語言中找到借詞原型。“(新借詞)在壯、傣、侗或者是在布依、毛南、仫佬語言里,其讀音都與漢語的西南官話基本接近。由于吸收進各民族語言的時間短,而且數量龐大,因此新借詞不但還沒有完全服從于各民族的語音規律,相反,在某些方面還突破了原來的語音系統。”[22]以壯族為例,由于與漢族的交往頻繁且較為密切,壯語表述當中不難找出許多由西南官話與粵語方言變形的借詞。
廣西的漢族方言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例如南寧、邕寧周邊地區的平話方言,就是原本的粵語方言在壯語影響下產生的一種本土方言,其中有相當部分的詞匯來自于壯語,同時在聲調上相較于粵語方言,也更近似于壯語,調性跨越幅度更大。廣西不同地區的壯語,也有巨大差異,在桂林、柳州地區的壯族所操語言,在借詞上更多來自于西南官話,而南寧地區的壯語中則有許多粵語方言的借詞。
壯語與侗語之間的借詞或同源詞,有雨、水、火、孩子、腸子、雞、簸箕等等,這不僅是因為壯語與侗語同屬于壯侗語族,同時也是因為廣西的壯族群眾、侗族群眾與漢族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密切的交流互動。相比起來,壯侗語族的毛南語、水語、仫佬語有著較多的同源詞。民族語言的高度融合,減少了不同民族群眾在溝通時的困難,也極大消解了彼此交流的心理障礙,是廣西不同民族能夠在雜居環境下彼此相融相助、團結一致的基礎。
(三)居住文化的交往與融合
民族文化與習俗,是該民族群眾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對客觀存在事物的樸素認知所形成的,所以通過觀察其文化,肯定能夠找到其在生產生活中的意義或價值,這也是文化或習俗能夠長久生存、傳承的原因。另一方面,當不同的文化出現交集時,會產生彼此交融、相互借鑒的現象,從而對本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行優化改善。一個優秀的民族,不僅能夠傳承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也能夠在發現其他民族文化優越之處時虛心學習、借鑒。在廣西,12個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居住環境,建筑式樣也各不相同,但除了漢族的傳統地居型建筑,應用最廣泛的無疑就是壯族的干欄式建筑。
廣西屬于亞熱帶氣候,具有炎熱多雨潮濕的特點,加上區內丘陵多、平地少的地理環境,為適應自然環境,壯族先民發明建造了全木結構的干欄式建筑,這種建筑類型可防潮,躲避猛獸,有效改善壯族人民的生活環境。但在最初受制于生產力水平,壯族先民居住的房屋多為簡陋結構,建造水平也較低,僅能用于擋風遮雨躲避猛獸,耐用性不強,居住空間狹小且防風雨力度較弱。隨著漢人不斷南遷,漢式傳統建筑開始傳播到壯族地區,壯族先民參考漢式傳統建筑對干欄式建筑進行了改造優化,在吸收漢族先進工藝的同時結合當地地理環境,對建筑材料使用、結構布局完善、居住空間設計與裝飾等方面都進行了創新,使干欄式建筑更具有實用性與美觀性。
由于漢族傳統的地居建筑(硬山擱檁式)在平原地區有著堅固、功能分區明了等優勢,所以也很受廣西少數民族建筑工匠的青睞。當然,由于廣西當地的喀斯特地貌有著丘陵延綿不絕、氣溫長年高企、降水量大、悶熱潮濕的特點,所以廣西匠人并沒有直接在本地照搬漢族的傳統地居建筑,而是在學習了漢族傳統建筑的特點與長處后,將其中優勢合理運用到了本地的干欄式建筑當中。南遷的漢族工匠也認識到中原矮小、封閉性較強的地居建筑在廣西地區很難解決空氣流通、防治蛇蟲鼠蟻、隔絕土地濕氣等問題。所以,漢族匠人們也開始在廣西地區的生活生產中學習少數民族尤其是壯族傳統干欄式建筑的優點,并根據漢族移民與后裔的居住習慣,設計了一種全新的硬山擱檁式建筑,將房屋地面架空、擴大了臥室、在前后屋檐下都建立良好的通風口,每個房間都有窗戶,能夠讓室內空氣始終保持在通風干燥的狀態,同時也能夠避免酷暑暴曬。而在各族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過程中,漢族也在建筑選址上逐漸貼近少數民族群眾,各族群眾的居住文化得到進一步融合。
廣西各族居住文化的融合,也體現在壯族傳統干欄式建筑對瑤族、苗族、侗族、毛南族以及水族等民族的居住文化融合上。干欄建筑是駱越文化在建筑居住上的主要特征,而壯族就是駱越先民在廣西的后裔。壯族的祖先是干欄式建筑的創造者,而這種建筑也因其對廣西氣候、自然環境的優越適應性、為廣西地區創造良好居住空間的優勢,得到了各族群眾的歡迎。除了回族多與漢族雜居之外,很多少數民族往往聚居于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壯族傳統干欄式建筑的實用價值在這一環境下得到了充分體現,無論是通風防潮還是居住舒適性上都比其他民族的傳統建筑樣式更優秀。[23]所以,這些民族紛紛仿造壯族傳統干欄式建筑來構建自身居住環境,但同時也保留了許多本民族的建筑特點,例如侗族的重檐干欄式鼓樓、瑤族的半洞半干欄建筑和過街樓、苗族的“人字支撐頂”干欄建筑等等。由于在建筑風格上的借鑒與學習,各族的建筑選址既有本民族傳統色彩,也有著與壯族傳統建筑選址相同的情況存在,所以彼此的居住空間融合也愈發深入,甚至在內部居室隔斷上也有著相似之處。
三、血與火的斗爭增進了民族間的血肉關系
(一)農民運動不分你我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解放戰爭取得不斷勝利,中國共產黨深入廣西各族聚居地、各村落進行了豐富多彩、寓意深遠的宣傳工作,使廣西各民族群眾革命意識不斷增強,為實現廣西各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思想保障與政治保障。在黨的號召、宣傳與鼓舞下,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政治斗爭如火如荼地開展,廣西壯族民眾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紛紛參加農民運動。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由鄧小平、張云逸領導的百色起義與龍州起義分別在百色與龍州爆發,參加起義的有包括壯、漢、瑤等民族的民眾。百色起義與龍州起義后建立了紅七軍、紅八軍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生活在東蘭、鳳山一帶的瑤族民眾,他們長期受到民族歧視與壓迫,為反抗壓迫,爭取平等與自由,韋拔群真誠邀請瑤族同胞參加農講所,但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第一屆農講所開展之時并沒有瑤族民眾前來報道,之后的第二、第三屆農講所開展之后才有瑤族群眾前來學習。[24]“學員來自東蘭、鳳山、百色、凌云、奉議、恩隆、思林、果德、都安、河池、南丹等壯、漢族農運骨干和青年學生共二百七十六名(沒有女同學,瑤族有名額人未到)。”[25]26這說明瑤族民眾的革命思想與革命覺悟得到進一步增強,他們逐漸認識到了革命斗爭對于翻身解放的重要性。之后,越來越多的瑤族同胞積極參與到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當中,漢族與少數民族團結在一起,聯合抵抗敵人。
在建立與保衛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廣西壯族與瑤族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革命斗爭期間,廣西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團結一致,共同戰斗。彼此在心理上、精神上的聯系更加緊密,為實現各民族團結平等和諧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抗日戰爭同仇敵愾
在歷史上多次與侵略者進行抗爭的過程中,廣西各族群眾展現出了極強的愛國精神。在抗日戰爭中,廣西各族群眾同樣繼承了共御外侮的傳統,各族愛國青壯年紛紛入伍受訓,由各族精銳組成的桂軍也在抗日前線中奮勇殺敵,普通百姓在后勤保障上為各族戰士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抗日戰爭的戰火尚未燒到廣西時,廣西作為大后方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募兵參戰。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與指導下,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為首的新桂系在廣西進行了兵員招募工作,大量熱血青年紛紛報名入伍。
1939年底,日軍集合五個師團的力量,從欽州灣登陸,上思、龍州、扶綏、崇左、邕寧等縣先后被攻陷,南寧也在十日內宣告淪陷。在這個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領導壯、漢、瑤等民族民眾,將十萬大山作為據點,分別在欽州、防城、上思、扶綏等地區開展了抗日游擊戰,并建立了抗日游擊隊。在廣西淪陷后,各族群眾還拿起了武器,誓死保衛家園,許多英勇的廣西戰士就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通過壓抑而漫長的抗日戰爭,廣西各族群眾齊肩并踵,共同經受了殘酷的考驗,建立起了深厚的抗日情感,這也是廣西各族在今日和諧共處的基石。各族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充分展現了民族之間團結向上、互助友愛的緊密聯系。
(三)解放戰爭齊肩并進
廣西各族群眾是從1947年夏秋開始參與到解放戰爭當中的。而在此前,欽州與博白地區在抗日戰爭中建立的游擊隊一直都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戰斗目標僅僅定在保全自衛上,游擊根據地分散于漢族、瑤族、苗族、壯族雜居的十萬大山當中。到了1947年初,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開展蔣管區農村游擊戰爭的指示》,從4月開始,中共廣西工作委員會書記秘密傳達了中共中央及香港特委的指示,開始組織廣西武裝起義斗爭。[26]
當時,廣西的解放斗爭口號是要完全實現廣西全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訴求,同時明確了廣西西部地區將成為武裝斗爭的核心區域。[27]隨后,廣西省委領導將特派員黃嘉派遣到了左江地區,并將廣西西南區域的特派員派遣到了右江地區,以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左右江根據地的傳統優勢。
在廣西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少數民族聚居地作為起義的發起點和核心區域具有合理性與必然性。因為在這些地方,少數民族群眾不僅需要承受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還要承受當時官方對民族文化的歧視,生活困苦沉悶、毫無希望可言,所以也希望獲得解放。由于廣西少數民族聚居地多數處于生人罕至的深山老林當中,距離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核心區域較遠,所以統治者在此處的政治影響并不高,而且因為深山老林地形復雜、隱蔽,可利用的自然資源也比較豐富,所以也更有利于廣西地區共產黨人開展工作。
在廣西各地紛紛吹起了武裝起義的號角后,國民黨在廣西的統治力量受到了極大沖擊,于是選擇用更酷烈的方式進行報復。其中從內戰前線回到廣西休整的正規軍174旅,更是對武裝起義部隊進行了嚴酷的圍剿打擊,試圖通過人海戰術與精良的武器裝備,配合保甲制度實現聯合防御、對調查明確為游擊根據地的村莊徹底焚毀,甚至對游擊隊領導人發出了懸紅,試圖通過殘忍惡毒的手段滅殺剛剛萌芽的武裝起義活動。正是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少數民族群眾選擇在尖刀大炮的威脅下悄悄為游擊隊員提供食品、情報以及簡單醫療。在敵人前往游擊根據地進行定點打擊時,正是這些少數民族群眾勇敢地拿起了簡單陳舊的燧發槍、土制炸彈以及冷兵器,與游擊隊共同御敵,徹底打擊了敵人通過圍剿消滅游擊隊的妄想。為了實現這一點,許多少數民族群眾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例如在萬岡縣的圍剿戰斗當中,敵人將近百個壯族與瑤族聚居的山村付之一炬。[28]
廣西各族群眾團結并肩、共同斗爭,實現了廣西地區的解放,同時許多黨員也通過在廣西少數民族聚居地參加斗爭,積累了豐富的戰斗經驗,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工作、經濟生產、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是我黨在完善民族政策過程中的寶貴財富。而漢族群眾與其他各族群眾在廣西解放的過程中相互扶持、互相鼓勵、團結互助的經歷,也使得封建統治、反動統治遺留下來的民族歧視與隔閡得到了消解。在殘酷的戰斗中,許多優秀的少數民族干部紛紛嶄露頭角,并在后來逐漸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力量。
參考文獻:
[1]〔漢〕劉安.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2]〔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西晉〕陳壽.三國志:張裔傳:益部耆舊傳[M].濰坊:團結出版社,2005.
[4]〔晉〕張華.百子全書:搜神后記:博物志卷三[M].武漢:崇文書局,1911.
[5]〔唐〕魏征.隋書: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史部:二十四史[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
[6]明憲宗實錄:卷四:成化實錄[M/OL].(2013-11-20)[2017-8-9].http://sky.cssn.cn/sjxz/xsjdk/zgjd/sb/jsbml/mxzsl_14484/201311/t20131120_844821.shtml.
[7]〔宋〕李曾伯.帥廣條陳五事奏:可齋雜稿:卷十七[M].北京:線裝書局,2004.
[8]蔡邨.瑤族源流探索[J].民族論壇,1997(1).
[9]龍子建.三苗、老苗子和現代苗族──湖北苗族源流分析[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1).
[10]吳忠軍.苗族“跳香”初探:兼論東部支苗族源流[J].民族論壇,1993(3).
[11]吳忠軍.侗族源流考[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3).
[12]〔清〕彭澤修,錢元昌.廣西通志:粵西諸蠻圖記[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13]楊國仁.侗族祖先哪里來[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
[14]廣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環江毛難人情況調查[Z].廣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1953.
[15]廣西地方志編輯組.廣西大事記(元)[J].廣西地方志,2000(4).
[16]〔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三[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17]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廣東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京族社會歷史情況[M].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廣東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1964.
[18]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編寫組.水族簡史修訂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9]陳士林.翻譯與語言[Z].涼山州語委辦公室,1978.
[20]楊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探究[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1).
[21]劉佳,胡金.廣西少數民族語言接觸與雙語類型變化調查研究[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34(7).
[22]蒙元耀.壯傣侗語言底層之比較[J].廣西民族研究,1992(2).
[23]郭紅.以廣西地域民族建筑為例淺析地域建筑文化[J].山西建筑,2007(34).
[24]牙遠波.試論韋拔群對東蘭農民運動發展的歷史貢獻[J].柳州師專學報,2003,18(2).
[25]左右江革命歷史調查組.左右江革命史料匯編:第一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78.
[26]覃伊平.柳北游擊戰斗生活的再現——讀于慎波的《柳北烽火》[J].南方文壇,1993(1).
[27]鄒冰.錢興同志在廣西[J].傳承,1998(6).
[28]巴馬縣志辦公室.國民黨萬岡縣政府覆沒親歷記[EB/OL].(2016-10-28)[2017-7-2].http://www.bama.gov.cn/html/1126/2016-10-28/content-210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