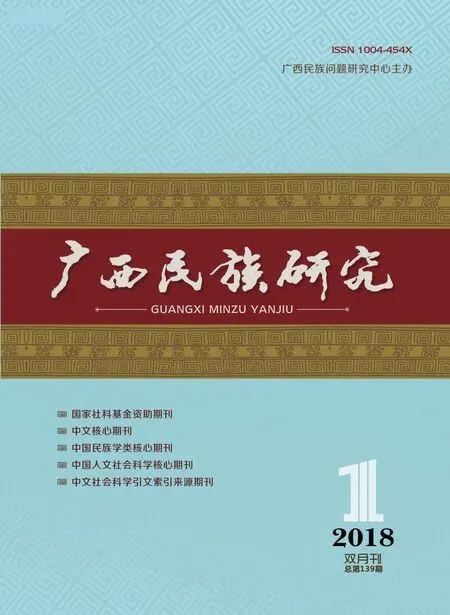文化多樣性與學校教育:西方國家的實踐及中國的歷程
陳學金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程度愈益加深,世界各國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正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1年、2005年分別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幾乎與此同時,“后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一個新興的學術話語。以此為標志,多元文化教育在很多國家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文化多樣性包括哪些內涵?其價值何在?學校教育對于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具有哪些價值與功能?國外多元文化主義及教育的歷史與現狀如何?中國在文化多樣性的學校教育中存在哪些問題?這將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
一、文化多樣性的內涵及價值
人類社會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主要表現在生物性和社會文化兩個方面。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看,社會群體除了體質性的種族差異之外,還存在著生產生活、社會組織、法律制度、道德、語言、宗教、藝術、人工制品、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文化差異。文化的多樣性正是人類社會多樣性的一種表征,亦是一個與人類同時出現的事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最為關注文化多樣性的國際組織之一。該組織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中將文化定義為某個社會或某個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的、物質的、智力的與情感的特征之總和;除了藝術和文學外,文化還包括生活方式、共處的方式、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1]文化多樣性是指各群體與社會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群體與社會內部以及它們之間傳承。文化多樣性不僅體現于人類文化遺產的豐富多彩的表達、弘揚與傳承方式,也體現于借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行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式。[2]
族群多樣性是構成某一國家文化多樣性的重要來源。若按國家的族群來源來劃分,那么國家層面的文化多樣性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多族群國家,即由許多世居族群或民族在歷史上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共同形成的國家;二是移民國家,即由移民群體與土著群體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國家。由于各國受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沖突和戰爭、跨國資本流動、宗教文化沖突等因素的影響,全球性的人口流動正在給越來越多的國家帶來各種棘手的問題。
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無論從某一國家視角還是全球視角考慮,人類社會都不可能使用一套相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生活。若如此,地球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根本不可能承受。同時,文化多樣性降低會導致思維模式單一,從而限制人類的創造性。[3]因此,“保護、促進和維護文化多樣性是當代和后代的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要求”[2]。
從個體角度而言,文化多樣性為個體成長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首先,多樣性的文化為來自不同地區、種族、族群、宗教、語言、階層、性別、職業、生活方式的個體提供了身份歸屬的條件。文化多樣性能夠帶給個體歸屬感、歷史認同感。特別重要的是,身份歸屬感關乎每個個體的生命尊嚴。因此,捍衛文化多樣性與尊重人的尊嚴是密不可分的。其次,文化的多樣性還有助于個體的成長與發展。文化多樣性可以增加個人的選擇機會,它還是獲得良好的智力、情感、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1]因此,尊重和保護文化多樣性,一定要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尤其是尊重那些少數群體和土著人民的各種權利。
從國家層面來看,文化多樣性是社會聚合(social cohesion)的基礎。特定的歷史淵源、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價值信仰是某一社會群體聚合的條件。由不同社會群體構成一個國家,需要共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對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而言,要同時處理好兩個有關文化的議題:一是要平等地保存國內各族群優秀文化,并維持國家的統一;二是要保存、傳播本國的優秀民族文化,與其他國家的文化競爭。前一個議題是完成后一個議題的基礎,政治家和普通民眾更關注少數群體或移民群體的社會融合問題。
從國際層面來看,承認文化多樣性是處理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前提,是建立地區、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佳保障策略之一。通過尊重與包容不同種族、民族、國家之文化特性,有利于加強不同文化中人們之間的對話與協作,有利于使地球村的每一位個體都認識到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有利于創造一種相互信任和理解氛圍,有助于開展全球范圍內的團結互助活動。
總而言之,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而且是一種共同的財富,“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1]。“文化多樣性創造了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類有了更多的選擇,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價值觀,并因此成為各社區、各民族和各國可持續發展的一股主要推動力。”[2]同時,正是文化的多樣性,給人類重新思考定位自身及發展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間,“在面對幾乎無法逃脫的市場與工具理性的宰制命運中,激起人類對自身反省與文化重建的希望”[4]。
二、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選擇與文化傳承
根據教育人類學家的觀點,廣義的教育是人類群體歷時性地傳承文化和共時性地傳播文化的過程。[5]23正規的學校教育只是教育整體的一部分,因為技術與知識的系統傳遞不過是教育的一環而已。[6]34因此,雖然學校教育具有保存、傳遞和創新文化的功能,但它并不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唯一機構。況且,任何一種文化形式要想保存下去,都似乎需要具有功能和市場條件。已有論者指出,“文化市場是維護各種活生生的文化形態的最前沿,強大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能力,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最重要手段。”[7]
在最近幾十年,保護文化多樣性才逐漸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議題。在以往各國家、各族群交往不甚頻繁、競爭不甚激烈的時代,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只是社區內部的事業。任何族群的教育活動都建立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上。在部落社會和農業社會中,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教育的范圍就限定在某一人群活動的范圍之內。在生產活動、宗教儀禮、休閑娛樂的日常生活中,年長一代將有關自然世界、生產生活、倫理關系、宗教禮儀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傳給年輕一代。在傳統的村落和社區,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總是與自然、社會和文化精神緊密融合在一起的。教育過程都發生在具體的自然情境中,這種自然情境包含著歷史的和文化傳統的元素。[8]
現代學校教育的孕育和發展是伴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完善的。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分工的分疏化和專業化,人類社會的知識總量越來越大,作為一個獨立社會子系統的學校教育系統應運而生。與傳統社會的教育形態相比,現代學校的教育對象顯著擴大。傳統社會的教育通過在少數人中間傳承已有知識和文化成果以維持既存的社會秩序。現代學校教育將大多數適齡兒童、青少年集中在一起,將各個行業和部門所必需的基本知識與基礎技能以及基本的社會規范、道德法律等內容,在適合的年齡階段通過最有效率的方式傳授給年輕一代。這種教育是促使個體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必不可少的環節,個體未經歷此過程就很難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生存發展。在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演進過程中,文化①此處的文化是一個綜合性的術語,包括但不限于知識、信仰、藝術、倫理、技能、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與態度。的比較與篩選成為教育過程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只有那些被認為對國家和個體是最有價值的文化才能被作為教學內容,被系統地傳遞給年輕一代。在這個意義上講,近代以來具有強迫性質的義務教育的普及是對以往具有自由競爭性質的多樣性文化的一種“破壞”。
現代學校教育除了具有保存傳遞文化、促進個體發展的功能之外,還具有國家整合與職業分化的功能。這是復雜社會中學校教育功能最獨特的體現。按照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觀點,現代學校教育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學校教育使兒童將社會規范內化,這保證了社會的正常運行。對于這一點,人類學家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觀點更為犀利,他直接指出了教育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曾這樣寫道:“現代社會秩序的根基不是劊子手,而是教授。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不是斷頭臺,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博士。如今,對合法教育的壟斷,比對合法暴力的壟斷更重要,更具有核心意義。”[9]46學校教育還具有職業分化的功能。教育系統就像一個大轉盤,經過這個轉盤的選拔、篩選,不同特質的人進入不同的工作崗位。經過教育系統的洗禮,學生的價值觀念也會形成分化,當然這更多的是通過隱性課程,在學生不知不覺中實現的。
目前,政府與學術界已經形成共識:多族群社會中的學校教育在化解族群沖突、提升族際間信任、確保國家一體化三方面負有主要的職責。[10]27-44實現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完美平衡既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標,也是民主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沒有多樣性的統一性會導致文化獨裁或文化霸權主義,缺乏統一性的多樣性會導致文化的割據和民族國家的分裂。[11]22-23多元文化主義帶給學校教育新使命就在于,與社會系統對教育的過度期望達成某種平衡:一方面維持社會的安定團結,一方面促進多元文化得以傳承。學校教育目標要兼顧多樣性與統一性。[12]4-5
學校教育系統在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的作用是有限度的。首先,正式的學校教育一直代表著“官方的話語”與“共同的文化”,它傳遞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社會與優勢階層的知識、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念,在統一性中加入更多的多樣性需要破除巨大的文化慣性。其次,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是一個涉及生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系統工程,教育系統只是這個復雜工程中的一個子系統而已。加拿大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在現代國家里維持一個獨立的社會性文化是一項需要有雄心大志的、艱苦的事業”。譬如,魁北克的法裔家庭的基本要求是他們的子女上法語學校,這是社會性文化再生產的關鍵一步,因為它可以保證把語言及與之相關聯的傳統和習俗傳給下一代。但是,除非語言在包括政治、經濟、學術等機構在內的社會生活中被使用,否則很難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存活下去。金里卡注意到,多元文化主義只是影響移民族裔群體地位的眾多公共政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有關入籍、職業培訓、職業準入、人權及反歧視法、公務人員聘用、健康和安全甚至國防等方面政策都對移民群體的歸化和融入有重要影響。[13]158-186通過分析移民少數群體的權利保障問題,可以得知移民少數群體的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問題,并不能僅通過教育系統解決。此外,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學校教育在實施中可能會遇到族群文化保存與國家整合、文化保存與個人社會流動、文化認同與經濟競爭等方面的諸多問題。歸根到底,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問題并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議題。
三、國外多元文化主義及教育的新進展
多元文化主義是與文化多樣性這一客觀現實相應的一套理念與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旨在推進和保障少數群體的文化權利,其與人權、民主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在一定意義上,多元文化主義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和社會制度發展的產物,它要完成對個人主義、自由競爭和適者生存帶來的社會競爭、弱肉強食的社會后果的平衡,在公平與正義的旗幟下謀求弱勢群體利益的補償和保障,甚至某種社會結構的翻盤。
在西方國家中,文化多元主義是挑戰同化主義和熔爐觀念的產物。多元主義和同化主義的區別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同化主義認為少數民族文化是對國家統一的一種威脅,要求各少數族群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與主流民族相一致,多元主義則贊頌人類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反對現存的對少數族群地位及待遇方面的不平等;同化主義認為少數族群是主流民族的從屬群體,應盡快放棄其內部認同,多元主義認為少數族群是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同化主義希望消除種族、族群之間的界限,多元主義認為族群界限不可能被消除;同化主義爭取個人間的平等,多元主義則爭取民族間的平等;同化主義認為要由人口多數民族進行統治,而且社會全體要遵從一般的規范,多元主義反對占人口多數民族的統治,并把民主社會視為少數民族互相聯合的社會而不是少數民族遵守多數民族統治的社會。[14]28-52是“沙拉盤”(salad bowl)而不是“熔爐”(melting pot)成為西方國家多元文化主義最廣為人知的隱喻。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對論者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存在的價值,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秀,絕不能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族群或民族的文化。
學者已深刻地認識到:對于文化的要求常常與某種更重要的經濟、政治依賴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對于文化的要求就好像是“有待去做之事”和“一種補償之物”。[15]137多元文化主義追求的是不同群體,尤其是那些在歷史上長期處境不利的群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方面的平等。[16]威爾·金里卡從民族國家構建與少數群體權利關系的視角出發,指出針對移民群體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際上與國家的一體化目標是一致的。[13]總體來看,多元文化主義及其教育實踐走的是一條迂回路線,從爭取族群群體權利到實現個體權利,從對文化差異與平等的認可到對心理與身份歸屬的承認,從尋求文化的平等、文化權利到經濟、政治權利平等。
英國社會學家吉拉德·德朗蒂(Gerard Delanty)提出多元文化主義有五種模式:自由的多元文化論(liberal multiculturalism)、自由社群主義的多元文化論(liberal communitarian multiculturalism)、自由多元主義的多元文化論(liberal 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激進的多元文化論(radical multiculturalism)、后現代的多元文化論(postmodern multiculturalism)五種類型。[17]71-84多元文化主義派別的多樣性實質上反映了不同民族國家的族群構成與面臨的棘手問題的差異性,也反映了同一民族國家內部不同群體與政治派別對于文化多樣性和少數群體權利保障政策的差異性。多元文化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族群權利的政治意味,促進了族群意識的強化,為族群社會動員提供了理論資源。[18]321
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伴隨著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興起,反對種族隔離、多元文化課程、少數族裔文化、教育機會平等、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成為全球教育改革中的熱點詞匯。多元文化教育在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致于有人認為,正是多元文化主義與教育、課程的結合,才引起了人們爭論的激情,“多元文化主義”才被更多地賦予了政治和哲學上的意蘊。[19]8、38
英國著名多元文化教育學者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認為,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有三個目標:積極發展文化的多樣性、維護社會的平等與團結、實現人類公正。[20]42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改革學校、學院和大學,使來自不同種族、民族和社會階層的學生能夠體驗到教育的平等。美國學者班克斯(James A.Banks)認為,要成功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必須推進教育機構的改革,包括課程、教學材料、教與學的風格、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態度、觀念與行為以及學校的目標、準則和文化等方面變革。[11]1他認為,教育者應該從內容整合(content integration)、知識的建構過程(knowledge construction)、消除歧視(prejudice reduction)、平等的教學法(equity pedagogy)、賦權學校文化與社會結構(an 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五個維度來實施多元文化教育。[21]
從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多元文化教育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成為一種最為流行的教育口號。政府從國家意識形態層面加強宣傳,號召各個層面積極采取有效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以應對學校中的種族差異。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教師教育項目也將多元文化教育列入其中。可以說,正是在這一時期,多元文化教育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卡梅倫·麥卡錫(Cameron McCarthy)將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分為文化理解(cultural understanding)、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和文化解放(cultural emancipation)三類模式。[22]第一種模式將重點放在認知層面,第二種模式將重點放在實踐和操作層面,第三種模式將重點放在自我意識和個體能動性的喚醒層面。在麥卡錫看來,這三種模式的理論前設都存在問題,并且對這三種模式都頗有微詞。但是,透過這些模式,我們仍舊可以看出當時教育理論界與實踐界對于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重視,以及其取得的豐碩成果。在20世紀末,“多元文化主義”在公共話語、公共政策與實踐中已經無處不在。
實際上,因政治和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同國家的多元文化教育運動各有側重: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英裔移民和法裔移民的語言沖突、緊張關系及國家認同的問題;英、法、德等國家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從以前殖民地涌入的移民,以及國外勞工移民的問題;拉丁美洲和澳洲的多元文化教育則起源于原住民的民族意識覺醒,與爭取更多的公民權益有關;非洲一些前殖民地國家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針對原住民或人口少數民族如何擺脫殖民時代的種族主義在教育中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之后,包含多元文化教育在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西方國家正在遭受質疑。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西方已經實行了二三十年,如今愈益被認定要為社會的分崩離析負責。對于一個國家政權來說,它最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對于國家和政治的認同。社會大眾和學術界越來越多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多元文化主義是維持了社會整合,還是制造了社會分裂?
其實,多元文化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概念。舊有的多元文化主義派別的共同基礎是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并將討論的話題限定在公共領域,以國家民主的可操作性框架為前提。晚近的多元文化主義派別引入了差異群體權利的觀點,將文化消減為權利,已不可逆轉地造成了公民身份政治化,以致人們懷疑社會整合的可能性。[17]81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一個“后多元文化主義”的時代。法、德、英、荷蘭、新加坡、澳大利亞等移民接收國開始為移民開設公民教育課程,并提高對外來移民的語言要求,以此向移民滲透主流群體的知識和價值規范,以進一步達到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忠誠。[23]
近年來,對于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性批判也越來越多。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犀利地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多元單一文化主義”,因為各種類別總是被歸到同一個民族國家框架之內,“它們是國家的代表機制、資源分配和正義界定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原則的內在產物”,“被設計出來并被付諸實踐”。貝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方法論的民族主義造成了學術上的這種狹隘認識,應該從一個“世界大同化”的視角審視“全球性的他者”。[24]
斯蒂芬·維爾托維奇(Steven Vertovec)提出“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的概念,它表達一種“多樣性”的多樣化和復雜化的涵義。他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至今,英國移民模式發生了重要變遷,這些新移民的經歷、機遇、束縛、軌跡與他們居住地的更大范圍內的社會的經濟的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了這種“超級多樣性”。在過去十年中到達英國的移民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具有多種來源的、跨國聯結的、社會經濟上差別的、法律上分層的因素,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多樣性。這些因素包括移民來源國、移民渠道、法律地位、移民的人力資本、獲得就業、地理位置、跨國民族主義以及地方當局、服務提供者、居民的回應等。[25]
伴隨著跨國民族主義、多元化和個體主義的迅速發展,多元文化主義合理性的根基已經被削弱。文化的多樣性較少地依賴于族裔的異質性,而較多地依賴于建立在階層、性別、宗教和生活方式基礎上新的亞文化的出現。[17]84在德朗蒂(Gerard Delanty)看來,多元文化主義不再是一個包含移民的容器,而成為當代社會多樣性的一種表達。[17]82
對于多元文化主義在一些國家式微和退卻,威爾·金里卡注意到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包括針對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和移民群體三種類型,實際上僅在針對移民群體時,多元文化主義才出現某種后退。在他看來,“后多元文化主義關于多元文化主義退卻的敘事夸大其詞,作了錯誤判斷。許多新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已經落地生根,并沒有遇到任何重大的反沖力或發生重大退卻”。“與后多元文化主義的敘事相反,作為公民化進程的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仍然充滿著勃勃生機,依舊是民主‘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26]多元文化教育作為一種理念和意識形態,它已經贏得少數族群以及部分主流族群的擁護和支持,它是對抗文化同質化、文化霸權有力的武器。但是,作為一種政策和改革措施,還有待于其他社會政策與多元文化教育結合起來,共同促進少數群體的經濟、政治地位和處境的改善。
四、中國學校中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實踐與問題
從文化的族群來源來說,西方國家的文化多樣性主要是由移民群體與土著群體共同決定的,與此不同,中國的文化多樣性主要是由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所決定的。按照費孝通所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27]109-147
中國對各民族文化多樣性關注的歷史背景與西方多元文化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28][29]中國經濟社會在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給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帶來了挑戰。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各界也愈加認識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更存在于文化領域,民族和地方的文化多樣性是寶貴的財富,具有顯著的經濟價值和創新功能。中國政府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框架內,積極倡導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念,充分尊重、保護、傳承、宣傳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教育系統內保護文化多樣性正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概而言之,20世紀以來,少數族群文化和地方知識在中國教育體系中大致經歷了從被視為落后、遭受排斥到逐步受到重視、添加到課程與學校教育體系中的過程。這一過程實際上與20世紀中國不同階段的重大命題、戰略抉擇和政策話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前半葉,在內憂外患、尋求民族獨立、構建現代國家的歷史背景下,代表先進文化的現代性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的文化觀念受到推崇,并被納入到中國新興的現代學校教育中,以期達到重建中國社會與文化之目的,反映地方和族群文化多樣性的知識被學校教育忽略,甚至拋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出四個中央民族訪問團前往少數民族省區進行訪問、慰問活動,了解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狀況。緊隨其后的少數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等活動,更是前所未有地呈現與認定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的事實。但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給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帶來了一定的沖擊與混亂。
20世紀80年代末,具有預見性的中國人類學家注意到“世界性的戰國時代”的特征,倡導實施有助于跨文化溝通的教育。1989年,費孝通在21世紀嬰幼兒教育與發展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在精神文化領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進相互理解、寬容和共存的教育體系,即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體系。這個體系包括21世紀人類共同生存的根本規則。[30]251-261
中央民族大學滕星教授是中國大陸最早接觸并普及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學者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他在借鑒人類學家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和林耀華的均衡論基礎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論。[31]156-158在滕氏看來,保護好中國的民族文化多樣性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在2000年,滕星又提出建議:國家應利用電視、報刊等各種媒體廣泛宣傳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并提倡大、中、小學校廣泛開展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教育,提高學生對文化多樣性保護的意識,培養學生跨文化的態度與行為方式,學會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32]7-19這些觀點是中國教育人類學者對于中國文化多樣性保護的遠見卓識,現在看來也令人振聾發聵。
自2001年開始,中國開始實行國家、地方和學校三級課程管理,這給民族和地方文化以各種形式進入校園設立了法律依據。2006年底,中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于2005年10月20日在第3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承諾尊重個人和弱小群體保存與延續自己文化權利。大約從世紀之交開始,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NGO組織和中小學校,開始探索開發適應本地區經濟文化特點的課程體系。中國的教育人類學者認識到,具有國家主義和城市導向的學校教育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但是過度強調整合的功能,則可能會忽略教育與社區發展的關系,即教育不能促進當地社會發展。通過轉換課程與教學內容,將地方自然生態、民族語言文學、少數民族歷史、民族特色手工藝、建筑、醫學、民族體育、民族歌舞、民間風俗、傳說故事、節日慶典以及其他優秀的民族和地方文化納入到校本課程或綜合課程,可以增強學校教育的社區發展功能。目前,中國的文化多樣性教育主要體現于兩類模式中:一是民族或地方文化的綜合/校本課程;二是民族團結主題教育活動。前者更多地體現地方教育當局與學校的自主權,后者則帶有強烈的國家意志,且是一個長期的重要工作。
中國的中長期國家教育發展規劃已將“加強國際理解教育,推動跨文化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作為重要目標并加以強調。[33]2017年1月,國務院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要求把“加強多元文化教育和國際理解教育,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作為“提高學生文化修養”的具體舉措。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在國家教育政策文件中提及和肯定多元文化教育,[34]極具歷史意義。另外,已有中國教育人類學學者注意到,中國的民族教育應立足于地方、國家和全球三個層面,在課程內容整合與教學方法更新上做出努力,意在通過鄉土教育、公民教育和全球多元文化教育,培養學生鄉土情懷、公民意識和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構建和諧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和全球認同。[35]
反觀近年來中國的文化多樣性教育,仍舊存在著有待改進之處。諸如將文化多樣性的教育等同于介紹國內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等同于民族團結教育;注重知識傳授而輕視交往實踐能力的培養;片面重視中小學階段課程內容的文化多樣性而相對忽視高考制度改革及大學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在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改革中過于強調語言教育的政治目標,等等。完善中國文化多樣性的教育體系,要綜合考慮學生個體發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家的社會整合之需要;體系建設要面向課程、教學、評價與升學就業、教師教育等諸環節;要重視學校教育與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的有效聯合;要鼓勵更多的學生成為雙語雙文化人;要遵從語言學習規律開展雙語教育改革實踐;要重視分析闡釋“經濟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經濟化”等社會現象。
五、結語:尋求一種多重視角的平衡
從國際學術話語的走向來看,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后多元文化主義”時代。我們既要充分重視“文化多樣性”“多元文化教育”對于促進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要關注其可能的消極影響。應該認識到,作為一種話語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教育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普及開來,它們會影響世界各地人們的社會想象、公共政策話語與社會實踐。[36]18-25而在實踐中產生的新的問題、新的矛盾需要新的智慧和新的話語予以協調和解決。雖然學校教育中在促進和保護文化多樣性中存在限度,但是做和改革總勝過于不做,因為這是一個關乎族群和國家認同,關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乎教育平等、社會公正的重大問題。正因如此,無論是在有關文化多樣性與教育的學術研究還是教育改革中,都應突破單純的個體主義、族群中心主義、地方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同時需要加入一種全球的或全人類的視野與關懷,尋求在這些視角達到完美的平衡與統一。
(致謝:巴戰龍副教授和關凱教授先后對本文初稿提出了批評與建議,在此深表謝忱!)
參考文獻:
[1]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EB/OL].(2001-11-2),see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179&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EB/OL].(2005-10-20),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1038&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3]滕星,白英,陳倩.文化多樣性與現代教育[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9(2).
[4]萬明鋼.論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與面臨的困境[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5]巴戰龍.學校教育·地方知識·現代性——一項家鄉人類學的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6]莊孔韶.教育人類學[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7]張小蘭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國際公約[N].中國文化報,2009-01-07.
[8]陳學金.少數族群社區中的教育何以可能——基于《滾拉拉的槍》一個片段的人類學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5(2).
[9][英]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M].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10]Gerard Postiglione.Educ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Multiethnic China. in James Leibold and Chen Yangbin.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Balancing Unity and Diversity in an Era of Critical Pluralism[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4.
[11][美]James A.Banks.文化多樣性與教育:基本原理、課程與教學[M].荀淵,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2]黃政杰主編.多元文化課程[M].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7.
[13][加]威爾·金里卡.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M].鄧紅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4]馬戎.西方民族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5][法]米歇爾·德·塞爾托.多元文化素養:大眾文化研究與文化制度話語[M].李樹芬,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6]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J].美國研究,2000(2).
[17]Delanty,Gerard.Community(Second edition)[M].Oxon:Routledge,2010.
[18]關凱.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
[19][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義[M].葉興藝,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0]哈經雄,滕星.民族教育學通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21]Banks,J.A.Multicultural Education:Development,Dimensions,and Challenges[J].The Phi Delta Kappan,Vol.75,No.1(Sep.,1993).
[22]McCarthy,C.Multicultural Approaches to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17,No.3(1991).
[23][德]斯蒂芬·維爾托維奇.走向后多元文化主義?變動中的多樣性共同體、社會條件及背景[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11(1).
[24][德]烏爾里希·貝克.多元文化主義或世界大同主義:我們如何描述和理解世界多樣性[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11(1).
[25]Vertovec,S.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J].Vol.30,No.6(Nov.,2007).
[26][加]威爾·金里卡.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衰?關于多樣性社會中接納和包容的新爭論[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11(1).
[27]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C]//費孝通.費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8]王鑒.多元文化教育:西方民族教育的實踐及其啟示[J].民族教育研究,2003(6).
[29]萬明鋼.從“差異”走向“承認”的多元文化教育[J].教育研究,2008,(11).
[30]費孝通.從小培養二十一世紀的人[C]//費孝通.費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31]滕星.文化變遷與雙語教育——涼山彝族社區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文本撰述[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32]滕星.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應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C]//胡鞍鋼主編.國情報告·第三卷2000年(上).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33]中國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34]巴戰龍.大力發展基于中國情境的多元文化教育[J].中國民族教育,2017(9).
[35]陳學金,滕星.全球化時代“三種認同”與中國民族教育的使命[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
[36][加]查爾斯·泰勒.現代社會想象[M].林曼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