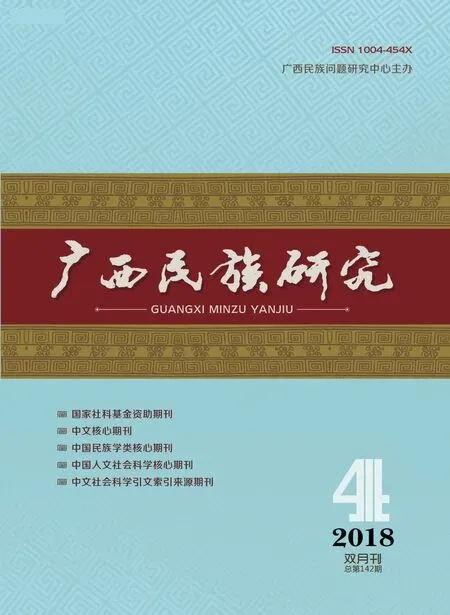花山巖畫與螞 節:大河流域壯族稻作文化的表征
——花山巖畫與“螞 節”比較研究論文之一
何永艷
從花山巖畫“蛙人”原型圖式來看,紅水河流域壯族螞 節是與花山巖畫聯系最為緊密、最具可比性的活態壯族民族文化事象。2018年2月筆者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南丹縣吾隘鎮那地村“螞節”進行了田野調查,結合三年來對花山巖畫的研究與調查,筆者認為雖然不能斷定花山巖畫與紅水河流域壯族“螞 節”之間具有繼承、傳承關系,但是可以斷定二者之間的確存在諸多的相似點、重合點及相通之處。對二者進行關聯比較,發現“螞 節”與花山巖畫最確鑿的核心關聯是“蛙”,它是“螞節”的主要祭祀對象,也是花山巖畫核心圖式“蛙人”的原型。“蛙”是這兩大文化事象共同的、核心的意象,是壯族稻作文明制度性、物質性、觀念性文化層面的核心載體、精神內核和動力表征。筆者認為從這一關鍵點入手進行花山巖畫與螞 節的比較研究,從活態的“螞節”側面反觀花山巖畫,揭示二者在經濟基礎、生計方式上的深刻聯系,在文化比較中窺探花山巖畫的隱秘內涵,挖掘其存活在壯族文化中的文化潛流,具有重要意義。
一、花山巖畫是左江流域稻作文明的表征
花山巖畫生成的總根源在于壯族地區原始經濟和社會形態,花山巖畫的產生必然以一定的生業模式為依托,“那”經濟是壯族先民創作巖畫的經濟生境和生存依托。
(一)左江流域是稻作農業起源中心之一
壯族是歷史悠久的農業民族,壯族地區原始農業可以追溯到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在經歷過漫長的漁獵采集經濟以后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逐步過渡到原始農業時代,甑皮巖時期壯族先民已會用磨棒加工稻米,大石鏟文化的出現標志著廣西許多地區在距今五千年前,已經是成熟的稻作農業區。壯族先民開墾駱田“麓那”,“從潮水上下”,“壯族及其先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形成了一個據‘那’([na2]指水田)而作, 依‘那’而居, 賴‘那’而食, 靠‘那’而穿, 因‘那’而樂, 以‘那’為本的生產生活模式及‘那文化’體系”[1]。
農業專家證實廣西壯族地區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產區之一,廣西自古分布有野生稻,20℃左右的年平均氣溫、1500毫米的平均降水量、全年無霜雪的季風氣候等條件適于野生稻的生長發育,廣西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稻作農業,距今至少有著10000年以上的歷史,“廣西境內的早期稻谷種植比河姆渡早2400—3000年,比云南目前最早的白羊村遺址早5000年左右”[2],康德爾等外國專家認為水稻是從嶺南傳到印度,而后傳到歐洲和非洲的。甄皮巖等遺址還出土了石杵、磨棒、石錘和石磨盤等稻谷加工工具,桂北資源縣和桂西那坡縣都發現了炭化稻的存在,亦可證。在《稻作農業史》一書中,作者認為桂南大石鏟就是駱越先民植根于稻作農業的特殊文化形式,“迄今,在廣西的42個縣、市發現了石鏟遺存約145處,以南部地區,尤其是左江與右江匯合的三角地帶,分布最為密集,左江流域的龍州、寧明、扶綏、崇左、大新、南寧及左江、右江交匯處的隆安等市、縣境都有發現”[3],除了廣西外,廣東、海南、越南等地都有大石鏟分布,以廣西最多,“大石鏟是源于古駱越民族稻作農業的特殊的文化形式,而這種文化是以邕江及其上游的左右江流域為中心向四周傳播的……這一中心地區可能就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明的中心地區之一”[4]88。學者們認為大石鏟是稻作生產方式和耕作技術進步的標志,是為適應稻耕發明的稻作農具,后來發展成為稻作祭祀禮器。除了大石鏟文化遺存外,分布廣泛的“那”地名是稻作農業起源的活化石,“那”字地名“分布地域連成一片,北界是云南宣威的那樂沖,北緯26度;南界是老撾沙拉灣省的那魯,北緯16度;東界是廣東珠海的那洲,東經113.5度;西界是緬甸撣邦的那龍,東經97.5度。這些地名的90%以上集中在北緯21度至24度,并且大多處于河谷平地。就廣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右江流域,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氣溫、日照等都易于稻作。[5]梁庭望也認為:“左江文化區,包括崇左、寧明、憑祥、龍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那坡等縣,地處左江流域,為丘陵和臺地,土地肥美,氣候炎熱,雨量充沛,為壯族重要的水稻產區,與邕南一樣,一年可以兩熟到三熟”。[6]22
可見,左江流域是西甌駱越民族原始居民的家園和發祥地,也是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之一,左江流域稻作農業生產為壯族先民的生活提供了充實的物質生活資料。稻作文化是該地區主要的文化特質。
(二)花山巖畫是“那”文化的結晶
左江花山巖畫古樸粗獷、氣勢磅礴、規模龐大,運用剪影平涂、概括、寫實、夸張、變形等手法將舉手頓足的“蹲踞式”人像描繪得對稱均衡、有力傳神。許多學者認為, 左江花山巖畫圖像表現的就是壯族先民模擬蛙圖騰形體和動作的群體舞蹈場面,誕生的社會根源在于壯族最主要的生計模式——稻作農業,是“那”文化的藝術結晶。
壯族神話敘述,雷公為老大,蛟龍為妹妹,雷兄與妹妹私通,生了怪胎蛙神,標志壯族先民從漁獵經濟走向稻作經濟,稻作經濟占主導地位后蛙神也就上升為民族守護神,于是創造了綿延數百里的蛙神供奉之所——花山巖畫。“壯人以青蛙為圖騰,這是稻作民族的一個重要標志。壯族祖先所鑄銅鼓上有單蛙、群蛙、累蹲蛙等立雕,蛙皮都有十字交叉的稻穗紋,這一畫龍點睛之筆充分體現了蛙圖騰的稻作民族早期標志的性質”。[6]131
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壯族先民在農業中對水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在左江流域,旱季缺水對于水稻種植影響很大,于是人們只好求助神靈進行求雨,在古駱越人的神話傳說中有《特康射日》等神話表達了對太陽的恐懼,當與干旱有關,這是許多學者認為花山巖畫與壯族稻作農業相關的結點所在,水稻—雨水—青蛙—祈雨—祭祀—舞蹈,從花山巖畫引發出的系列文化現象的根源正在于壯族人民的主要生計稻作以及稻作文明生發出的“那文化”。
稻作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壯族先民文化的發展,促進了花山巖畫藝術風格的形成,簡練平涂的繪畫方式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巖畫繪制方式,統一的赭紅色是作用廣、意義深的時代色彩,以“那”文化為核心的稻作文化使得左江花山巖畫彰顯出獨具特色的民族風格:模擬蛙人的統一的舞姿正是對稻作圖騰——青蛙的模擬和崇拜的表現,造型豐富的人物頭飾正是駱越先民在稻作文化基礎之上的服飾文化的表現。“花山崖壁畫是壯族祖先祭祀蛙神的圣地,它寄托了稻作民族對農作物豐收的強烈愿望,花山崖壁畫是原始社會末期到階級社會分化初期的祭祀圖,也是壯族社會分化初期的生動寫照,大人物與小人物之間已經有了不同的地位和財富,但小人物仍還圍繞著大人物,祭司扮成的蛙神向他歡呼,彼此親切,尚不嚴重對立,整個畫面活潑生趣,然而人體卻是鬼影式的透視圖,平涂法顯示出冷峻、嚴峻、劃一、不可一世的奴隸制傳統畫風,可以說是家長奴隸制初期的形態,崖畫還描繪了當時的蛙形舞姿,是一種群體性質酬神舞,銅鼓及銅鼓棺上打扮成鳥的圖像的羽人,頭上羽翎迎風飛舞,裙裾飄逸,體態翩翩,舞姿優美動人。”[6]56
與內蒙古巖畫、賀蘭山巖畫、新疆巖畫以狩獵、放牧等動物主題為主不同,駱越先民進入稻作農業階段后巖畫主題已經從動物世界過渡到人的世界,“左江崖壁畫以大量的人物形象來表現當時重大的社會活動,這一現象無不充分反映了當時藝術已由客體的動物描繪轉向主體自我表現——即對人自身肯定的新時代的風尚和精神”[7]388。
(三)左江巖畫是壯族稻作文明的圖像化總括和表征
陳嘉在《廣西左江巖畫與稻作文化》一文中認為左江巖畫與石鏟遺存具有分布地域上的一致性、發展時間上的銜接性和族群的同一性,考古學家楊清平也認為左江巖畫對大石鏟有繼承和發展,因此,左江巖畫是駱越族群以大石鏟文化為基礎,在大石鏟文化結束后的稻作祭祀文化一脈相承的延續,“桂南石鏟遺存與左江巖畫,維系著駱越稻作文化的傳統,是稻作祭祀文化的不同表現形式, 戰國時期的左江駱越人不僅延續著先民的稻作農業, 同時也傳承著先民稻作祭祀文化”[3]。黃成賢在《壯族先民的雷神崇拜——左江流域崖壁畫性質初探》一文中認為花山巖畫是壯族雷神崇拜的表現,梁庭望在《花山崖壁畫——祭祀蛙神的圣地》一文中將花山巖畫定性為壯族祭祀蛙神的圣地,潘其旭在《花山崖壁畫——圖騰入社儀式的藝術再現和演化》一文中認為花山巖畫是壯族圖騰入社儀式的再現,另有壯族的族徽、方國的門神等諸多觀點,筆者認為從根源上看“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他的心理所決定的,他的心理是由他的境況所造成的,而他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它的生產力狀況和他的生產關系制約的”[8]350,因此,歸根結底左江巖畫的蛙人圖像即是壯族稻作文明的表征,所表達的雷神、蛙神、雨水、豐產等信仰元素都是以稻作生產為基礎的客觀生存所需的稻作祭祀文化,左江巖畫上交媾圖像、孕婦和帶生殖器的男性圖像都是將懷孕生殖與稻作生產聯系的巫術行為,鳥圖像、羽人圖像等也是基于駱越鳥田、飾羽而舞祈求稻作生產的意圖,供奉犧牲、船圖像等也是祈求稻作豐產,甚至花山巖畫上頭戴面具的蛙人像(儺神)也是稻神的象征。類似的稻作文化事象還有隴峒節“求務”、稻谷收割前“跳嶺頭”等,都是駱越稻作文化的產物,目的是祭祀稻神、以舞娛神、求得豐收,左江巖畫是這一系列的稻作豐產文化的圖像化總括和表征。
放眼世界,與同樣具有稻作文明積淀的同根生的泰族也有巖畫,而且其巖畫與壯族左江花山巖畫有相似性,差異性也很明顯。覃圣敏主編的《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第一卷)》一書中,作者對壯泰兩族的歷史地理、種族特征、文化等進行了比較,認為兩族都以稻作生產為生計基礎,地理環境方面也有相似處,在巖畫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泰國巖畫分布在北部普潘山脈和碧差汶山脈的崖壁上,以湄公河沿岸最密集,泰國巖畫也以人物圖像為主,也主要以赤鐵礦加動物膠為顏料紅色、赭紅色繪成,選擇上凸下凹的巖廈作畫,表現舞蹈、儀式、游行等現實生活場景,壯泰兩族的崖壁畫相似處“表現了當時東南亞人們的日常生活、儀式活動和各種風俗習慣,不同的只是人們的種族或民族不同而已,當然這些都取決于地理位置、生活環境和地理狀況的不同”[9]648。可見,壯族花山巖畫與泰族巖畫相似處是類似的稻作生產基礎和日常生活方式使然,差異則是環境、族群等的本質差別。
二、螞 節是紅水河流域稻作文明的表征
“節日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為適應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創造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民俗文化,是一個民族生產方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的集中體現”。[10]1馬克斯·韋伯認為,人是懸在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筆者在對那地村“螞 節”動態儀式過程和靜態道具物品參與觀察中發現,“螞節”民俗文化的物體、行為和事件整體傳達著壯族稻作文化的象征意義,而當地壯族人民 “螞 節”文化意義的形成是建立在對稻作生長與青蛙習性的良性共生正確認識與有效利用的基礎之上的,是稻作文明的文化表征,彰顯了百越“那”文化圈內稻作文明的多姿多彩以及當地壯族人民奇特卓越的生態智慧。
(一)紅水河流域屬于壯侗語族“那”文化圈
吾隘鎮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南丹縣下轄的一個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鄉鎮,“吾隘鎮屬亞熱帶季風區,年均氣溫18.1℃,年降雨量為2500毫米。全鎮有耕地面積15783畝,農田有效灌溉面積8999畝,林地面積20.8萬畝,荒山荒坡650畝”[11]。吾隘鎮位于“紅水河”中游東側,壯族人口達80%以上,除了馬幫五尺驛道外,紅水河水路成為當地在沒有公路之前與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那地村是紅水河沿岸至今仍完整保留著“螞 節”民俗文化的村落之一,屬于壯侗語族“那”文化圈,與鎮政府相距16公里,地處群山環繞的盆地之中,四周有同貢村、楊州村和納灣村等村莊圍繞。該村主要種植水稻、玉米、甘蔗、油菜,兼種植板栗、黃臘李、蠶桑等經濟作物。村民李元文說他們村附近的山上以前種著很多板栗,后來才開始種植桑樹養蠶的。那地村的主要生計方式是水稻,那地村水資源豐富,有一條從紅水河分流出來的小河穿村而過。該村水稻種植一年一熟,水稻收獲以后會種植油菜花,“螞節”舉辦的時間正是片片金黃油菜花燦爛盛開的時節,小河潺潺、青山環繞、美不勝收,“村落面向田峒,房屋掩隱在綠樹清竹叢中,溪流從村前流過,呈現出一派典型的依‘那’而居,據‘那’而作,以‘那’為食的壯鄉田園景象,具有壯族先民的‘那’文化特色”[12]11。
(二)那地“螞 節”蘊含豐富的稻作文化內涵
在那地村螞 節上,筆者還觀察到了富有特色的壯族服飾文化和富于特色的螞 道具,表演耙田舞的村民身穿蓑衣、頭戴斗笠,赤腳,褲腿高低不齊,與農田耕夫無異;跳田間舞的婦女們,頭戴有黃色流蘇的頭巾,身穿民族服飾,頭巾上的流蘇隨著播種、薅秧等動作整齊地擺動,充滿動態的美感和生活氣息;表演螞 舞的螞 仔們穿著類似青蛙皮的衣服,形態動作模擬青蛙,生機盎然、活潑可愛,天峨等地的螞裝扮則有不同,有的以墨汁在上身、后背、臉龐及小腿描畫出螞 紋樣,再配以三角頭巾,獨具特色;在天峨等地螞節中還會出現頭戴面具,身穿破衣爛衫的“卜婭”,此人為秘密選定,在隱蔽處裝扮,在會場中維持秩序、震懾妖魔、驅逐鬼怪,保護螞 魂魄,之后又悄然離去,充滿了神秘色彩,據說扮演此角色者可積德消災。
(三)那地村螞 節蛙崇拜具有稻作文化根源
“蛙是兩棲動物,有頑強的生命力,是天然的游泳能手,在陸地上跳躍敏捷,是技巧專家。蛙又是農作物害蟲的天敵,是春雨最靈驗的預報員。”[14]蛙崇拜并非壯族所獨有,納西族、普米族、彝族、黎族等都有蛙崇拜遺風,納西族婦女的羊皮披肩上有蛙圖案,黎族婦女筒裙上有青蛙紋飾,普米族稱蟾蜍為“波底阿扣”(舅舅),彝族長詩《勒俄特依》中將蛙與人并列分類;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印第安人和北美也有蛙崇拜習俗,弗雷澤在《金枝》中記錄了印第安人將蛙視為雨水的主人以巫術扮演的習俗,列維·斯特勞斯在《嫉妒的制陶女》中記錄了北美關于蛙與月亮的神話,北美人認為月亮中的斑點就是蛙貼在月亮身上而來的。
眾多族群對青蛙崇拜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人自身的生產:生殖,二是物的生產:雨水(氣候)。仰韶、廟底溝文化遺址都有數量眾多的蛙紋彩陶,四川納西族供奉的生殖女神“巴丁拉木”,即為青蛙,壯族神話《祭青蛙》[15]55記錄:雷王的兒子青蛙下來玩,它說它可以去犁田。誰知它到田里專門捉蟲吃,沒有去犁田。人們惱火了,就用開水把青蛙潑死了。天上的雷王知道了,就再也不下雨了。布洛陀讓人們祭奠青蛙給雷王賠禮。于是人們就祭奠青蛙。后來青蛙死而復生,但它上不了天了,不過,只要它一喊叫,天上的雷王聽見,就一定降下雨來,避免了赤地千里、水田干涸、溪河斷流的悲慘境地。從此以后,青蛙在人間便成為人們的朋友。有時天旱了,人們就要祭青蛙,唱“螞拐歌”。武鳴縣壯人稱蛙為“龔叟”(自己的爺爺、祖先);龍州縣壯族也把蛙叫做“阿祖”;田陽一帶流傳的《洛陀洞與螞拐節》神話將螞節與布洛陀緊密聯系;廣西三江侗族三王廟相關蛙神話傳說將蛙視為三王,其廟為祖廟;廣西羅城仫佬族在與壯族螞節相同的時間模仿青蛙形態動作跳螞獅舞。老撾《蛤蟆國王》的神話傳說中講到蛤蟆國王與雨神戰斗戰勝了雨神,簽訂和平條約:地上的人以芒飛射入天空提醒雨神給稻田降雨,青蛙鳴叫是開始耕作的信號,風箏和長笛聲是收獲的信號,該神話揭示了當地“芒飛節”的來歷,對于壯族“螞 節”的淵源有啟示作用。
那地村人崇拜青蛙的原因也不例外,那地村“螞 節”中埋葬的青蛙以雌雄一對為佳,這一特殊要求涉及青蛙的生殖習性,也與人們對青蛙的生殖崇拜相關。青蛙屬于卵生動物,它們的時令季節性很強,冬天的時候青蛙進行冬眠,春節過后二月間萬物復蘇的時節,青蛙們逐漸蘇醒,呼喚雨水,“青蛙有雌雄之分,雄蛙口角旁有一對鳴囊,當鳴叫時,將口腔內的氣體壓進鳴囊,使其擴大成球狀,起共鳴箱作用,發出咯咯聲,十分響亮”[16]83,4月中下旬的時候開始抱對繁殖。
那地村地處群山環繞的一個小盆地中,大部分農田屬于水田,在該村“Y”字型的道路街道兩側幾乎全是油菜花盛開的水田,油菜花是在水稻收割以后種植的,一條清澈的小河沿著道路田邊緩緩流淌,山腳下有些田地種植甘蔗,小河邊少量田地種植桑樹,而板栗、李子、杉樹等果木多種植在山上,大部分田地以種植水稻為主,可見,稻作農業是當地村民的主要生計方式,吾隘鎮文化站站長梁祖曾向筆者解釋說:
青蛙的皮膚很薄,因此能夠敏銳覺察到周圍氣候環境中空氣濕度和溫度的細微變化,所以我們才說‘青蛙叫,雨水到’“青蛙田里叫,谷種田里跳”“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青蛙確實具有氣象預報的功能,這是有科學依據的。所以,我們壯族人通過青蛙骨頭的顏色來判斷來年是否風調雨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蛙骨的不同顏色都是不同的氣候特點造成的,因此對來年的氣候預測具有參考作用。
的確,科學家觀察顯示青蛙是兩棲動物,可同時在陸地和水中生存,它們與雨水具有特殊的親緣關系,這一點與水稻對水的依賴具有生態上的共性,青蛙的皮膚確實會隨著溫度、濕度的變化而呈現不同色彩,雨水降臨前空氣中濕度較大,蛙皮顏色較淺,青蛙感知雨水來臨而高興和興奮于是集體歡呼鳴叫。尼泊爾巴格瑪堤河谷的居民每年雨季時節都要在青蔥的稻田中供奉鮮花、米漿等,并用米飯和九種豆做成的湯“喂青蛙吃飯”,以祈求及時降雨、水稻豐收,傣族人也有類似的祭蛙求雨儀式,都與蛙的稻作豐收象征有關。
在遠古的夜郎國時代,那地州(今南丹縣境內)一帶連年鬧“蝗兵”災,據后人考證“蝗兵”乃今日的“蝗蟲”,夜郎王下令誰能帶兵征剿“蝗兵”便封為大將并招之為駙馬。時有那地永安山一青年名叫駱吉,他智勇過人,土著族人推之為族長。他奉旨帶兵征剿“蝗兵”,他所到之處,“蝗兵”潰不成軍。后“蝗兵”將領施法術,變成數不清的蝗蟲,鋪天蓋地,吃光莊稼,駱吉也用法術披上一件似螞 皮的大衣,揮手一指:大地上突然出現了無數的螞 ,把蝗蟲吃光,駱吉討伐“蝗兵”取得勝利。皇帝招他為駙馬,駱吉不從,愿回鄉務農。一天夜里,皇帝令人把駱吉的螞衣燒掉,駱吉沒有螞 衣,不久便死去。
駱吉死后不久,天下又鬧蝗蟲災,當地師公說,駱吉是天上螞 星轉世,也有人說駱吉是布洛陀的后身,要消滅蝗蟲,要一年一度每逢農歷正月選個吉日為螞 節。在節日里安葬螞 ,要做一口石頭棺材,里面裝一雙雌雄螞 。用“金童玉女”抬到廟里安放(叫埋螞 )。待到當年的三十夜(春節),全村老少舞獅到廟里打開棺材觀看螞 遺骨,若骨為黃色,預示來年糧食豐收;若骨為白色,預示來年棉花豐收;若骨為紅色,預示來年六畜興旺,五谷豐登;若骨為黑色,預示來年定有災難。
從古至今,原屬那地州所管轄的天峨、東蘭、南丹、河池邊界的鄉村,每年農歷正月吉日,家家戶戶按傳統習俗過“螞 節”,在節日里,男女老少跳螞 舞,唱螞 歌,吃螞 飯,以祝愿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那地壯族“螞 節”2006年已申報為國家第一批公布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種植水稻的水田為喜水的青蛙提供了生長繁殖的生態環境,再加上青蛙是益蟲,以捕捉稻田中的蝗蟲、稻螟蟲、稻卷葉蟲等為食,能為水稻的生長保駕護航,二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良性生境。研究顯示:“在丘陵和山區水稻田和池塘的青蛙主要是中國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蛙類是否有益和益的大型通常用‘有益系數’來表示,蟾蜍和黑眶蟾蜍的‘有益系數’分別高達90.14%和71.88%,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分別高達71.15%、93.33%和97.84%”[17]。在那地村流傳的螞傳說故事中英雄駱吉(索吉)正是因為披上了螞衣之后戰勝了蝗蟲災害,為人民的生產豐收做出了貢獻才得以被眾人敬仰膜拜,這是當地壯族人民對青蛙生物有益性的形象外現,對青蛙的崇拜也是由此而生,并將之擬人化、藝術化,在那地村“螞節”的螞山歌中這一點體現得尤其明顯,以下吾隘文化站站長梁祖曾向筆者提供的翻譯成漢語的螞歌文字材料,與東蘭等地螞歌歌詞略有差異:
壯家愛唱螞 歌,螞 歡叫春雨落;螞 捉蟲禾苗好,秋后帶來好收獲。
正月里來是新春,螞 洞中未翻身;祝愿螞 冬眠好,好為壯家鬧春耕。
二月里來桃花紅,春回大地春意濃;只要春雷一聲響,螞 感到一身松。
三月樹木標了苗,螞 出洞伸懶腰;人間春光無限美,螞 歡笑呱呱叫。
四月壯家忙耕田,螞 戲水在田間;低頭戲水抬頭看,一個叫比一個甜。
五月螞 心也飛,為情叫來做一堆;不信你到田中看,小的總要大的背。
六月二十米胞胎,螞 吃蟲忙起來;人來世間善為本,保護螞 理應該。
七月初幾米勾頭,這時螞 蹲水溝;奉勸世人莫去打,壯家美德留千秋。
八月十五是中秋,米黃只等人來收;豐收不忘敬螞 ,壯家習俗要保留。
九月來到天氣寒,螞 要把石縫鉆;鉆進石縫把冬過,來年開春再來玩。
十月來了翻北風,這時螞 無影蹤;它為壯家做好事,愿它今年過好冬。
十一月份雪紛飛,螞 冬眠不做堆;只有三月出來耍,不見寒冬出來陪。
十二月間冷得多,天當被子地當窩;雖然螞 穿得少,天寒地凍睡得著。
壯家要唱螞 歌,傳統佳節年年過;潑水祈求天下雨,螞 歡叫壯家樂。
以上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在沒有科學的氣象預報的情況下,那地壯族人對螞的生活習性了解得非常系統透徹,具有關于螞 預測雨水、干旱、洪澇等氣象知識以及捕食害蟲、消滅蝗災的生物學知識體系,因此認識到了青蛙與水稻作物生長的特殊良性共生關系,他們意識到螞關系到整個族群的生計生活,因此以巫術祭祀的形式奉螞為神明,借助超自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氣候環境對稻作生計的影響。
三、大河流域壯族稻作文明的表征
自然環境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文明類型,左江流域花山巖畫與紅水河流域螞節文化在生境、族群、文化表現上相似、相通,有著顯性的關聯,這些顯性關聯背后蘊含著蛙崇拜的深層關聯,這些深層的和顯性的關聯又都是以共同的稻作文明為根基,二者同為大河流域壯族稻作文明的表征。
(一)類似的大河生境
壯族人的祖先很早就緣水而居,這種對水的崇拜和依賴一直延續到現在,如今左江兩岸的壯族村寨依然呈現沿江分布的特點。
左江位于廣西西南部,是郁江支流,屬珠江水系,全長約345公里,流域面積約13000多平方公里,該流域雨量充足,河水水量豐富,洪水期與枯水期流量相差192倍之多,左江花山巖畫被譽為“崖壁畫的自然展覽館”,它們分布于從廣西壯族自治區寧明縣到扶綏縣的明江、左江兩岸,綿延250多公里,作畫風格、選址和繪制技術、繪制顏料整齊統一,各巖畫點往往存在于河流拐彎的地方,且大多位于河流的凹岸處,左江之水是影響古駱越人選擇巖畫點的主要因素之一。
紅水河位于廣西西北部,為西江水系重要干流之一,因雨季洪水沖刷兩岸紅土使河水呈紅褐色而得名,干流全長659千米,流域面積6.32萬平方千米,約占廣西總面積的37.4%。“與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皆起源于大河文明的情況相似,壯族螞拐節的流布地域也散見于壯族紅水河流域百余里的壯族村寨,且是沿著紅水河沿岸自北向南呈帶狀分布……這些區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勢平坦,土地相對肥沃,氣候溫和,適宜人類生存,利于農作物培植和生長,能夠滿足人們生存的基本需要,故農業往往很發達。大河文明以農耕經濟為基本形態,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較強。”[13]5
左江流域和紅水河流域都是壯族先民的棲息地,考古發掘顯示,新石器時代這兩大河流域就已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時代,當地居民開始鑄造農業生產所用石器和脫粒工具,并已經學會制陶,滿足了人類定居生活的基本要素,很早就發展出有特色的稻作農耕文化,成為壯族人民棲息地。可見,左江和紅水河這兩河流域都是壯族主要的聚居地,早在數萬年前,壯族先民就已在該流域耕作生息,開創了以稻作文化、干欄文化、歌圩文化、銅鼓文化為主要形態的壯族文明,被稱為是“壯族母親河”“壯族文明的搖籃”。這兩河流域都屬于喀斯特地貌,群山綿延、峰巒疊嶂、溝壑縱橫,崇山峻嶺之間田峒交錯,“八山一水一分田”,屬亞熱帶氣候,古人類化石、古代文化遺跡較多。
(二)共同的族群淵源
民族主體一致。紅水河流域與左江流域現階段都以壯族為民族主體,壯族先民都是這兩片土地上的土著民族,這兩大河流域都在數萬年以前已有古人類居住,這兩大流域壯族人口比例都較高,外來民族為后遷入者,壯族是這兩河流域的土著原生民族,壯族文化是其原生文化和主體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小,壯族傳統文化保留完好,融合統籌了該地區的農耕、居住、飲食、宗教信仰、歌謠、婚姻、服飾和銅鼓文化,體現了壯族的精神信仰、宇宙觀和價值觀。
左江流域與紅水河流域都具有水稻種植的從選種、育秧、插秧、耕作、灌溉、施肥、耘田、收割、氣象觀測到宗教信仰、節日習俗、稱謂、地名、思想觀念、飲食等一整套的稻作文化體系,體現了壯族人依水而居、以那為本、憑那而歌、以那為樂的那文化特點。
(三) 共同的蛙信仰
壯族先民在距今約七八千年前就已經發明了人工栽培水稻,開始了原始稻作農業生產。在距今約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壯族稻作農業就有了很大發展,生產力提高,種植面積擴大,種植技術完備,左右江流域的大石鏟文化以及在那坡感馱巖和全州曉景發現的碳化稻谷是廣西稻作農業的文化遺存。開始的時候,壯族人是在河灘湖區隨雨季潮水漲落進行水稻耕種,后來隨著耕種面積擴大,生產力水平提高,他們開辟出田峒種植水稻,依靠泉水溪流和天然雨水灌溉,水稻時常受到氣候環境的影響,大雨連連、洪水泛濫的時候會沖毀田疇;久旱不雨,泉溪干涸,又造成禾苗枯萎,顆粒無收。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壯族先民首先發現先打雷后下雨,而在人間則是“青蛙叫、雨水到”,于是他們洞見到支配著雨水和稻作生產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正是雷神、青蛙,于是他們創造了雷王主管雨水、布伯斗雷王的神話故事,青蛙是溝通人間與天上的使者,與雷神具有特殊聯系。
顯然,壯族的蛙崇拜具有雙重的文化本質,一是生殖繁衍,二是稻作豐饒,與蛙崇拜關聯的最早的原因是生殖崇拜,基于蛙腹與孕婦腹部、蛙口與女人陰戶外形的相似,壯族先民想借助蛙產子繁多的神秘力量增強族群的繁衍生息能力,人蛙婚媾的神話傳說即是力證。隨著壯族進入稻作農業時代,生產能力提升、對蛙的生物性認識加強,洞見了蛙與水稻生長之雨水和病蟲害相關的利害關系,蛙的身上增加了稻作豐饒的使命,與生殖崇拜交融合一形成雙重的蛙崇拜精神內涵,實現了人與蛙的自然和諧、共生共榮的生態境界。因此,青蛙從多子多孫的生殖之神又成為呼風喚雨的雷王的女兒,雨水的使者,壯族的蛙神崇拜從對青蛙繁殖力的自然屬性的崇拜,發展到農業社會保佑風調雨順的社會屬性的崇拜,是壯族人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鮮明抽象思維能力和生產實踐發展的結果。青蛙由此發展為保佑壯族人民風調雨順、幸福吉祥、稻作豐饒、生息綿延的全民崇拜對象。
“從距今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壯族先民形成對青蛙的崇拜習俗以后,歷經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直至唐宋元明時期,青蛙崇拜習俗跨越了漫長的歷史時空,伴隨著壯族的不斷繁衍和發展而世代傳承下來。到了清至民國時期,壯族對于青蛙的崇拜形式逐步發生變化,形成了以崇拜青蛙,祈求風調雨順,人壽年豐為核心的螞節習俗。”[10]13花山巖畫、蛙飾銅鼓、螞節是壯族蛙崇拜的三個典型文化事象,這三者的先后順序大致為,花山巖畫距今2600年以上,蛙飾銅鼓1000-2000年(秦漢、南朝至唐代靈山型銅鼓),“螞節”數百年以上(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對青蛙的崇拜早先是出于對青蛙旺盛繁殖力的崇拜,繼而將稻作豐饒的內涵疊加融合進來。“螞節”中對青蛙生殖內涵和豐饒內涵的表現:尋蛙者多為男性,找到蛙者稱為“蛙郎”,東蘭長江地區“螞節”中女子以纏發銀釵敲擊銅鼓尋找意中人,蛙郎與蛙妹(雷女、九天玄女的結合)的配合、東蘭女子尋找意中人都充滿生殖意味,同時可促進稻作豐饒;男性表演耙田舞時群蛙在側,表演田間舞的都為女性(女性本身有豐饒之意味),蛙舞動作在整個節慶中伴隨始終,這些都具有稻作豐饒意味,同時又滲透有生殖繁衍之意。將生殖繁衍的內涵加入到稻作豐收的目的之內,將蛙的繁衍力借助到稻作的生長上來可促進稻作豐收。“兩種生產”內涵的融合滲透在這三大文化事象中都得以囊括,生殖與稻作兩種內涵的比重有所不同,時間越早生殖崇拜的內涵比重越大,時間越晚稻作內涵的比重越大。
規模龐大、時間久遠的花山巖畫,眾多的人物畫像整齊劃一模擬青蛙舞蹈跳躍,就是在祭祀蛙神,既是以巖畫創作和祭祀儀式等特定的交感巫術,包括了獲取生殖繁衍這種神秘力量,實現族群的凝聚和生息綿延的內涵;又是在向雷王表達雨水要求的形象再現。對于花山巖畫中的蛙人原型,丘振聲有精妙的論述:“廣西左江流域的摩崖壁畫,那些兩腳叉開,兩手高舉的正面立像,既是人的造型,也是蛙的變體……花山摩崖壁畫眾多的形象組成的壯觀畫面, 其氣勢更是咄咄逼人。在那畫面里,不論是正面的立像,身軀前沖的側面像,或由正面、側面像組合的群像,都有一種動力感, 給人一種陽剛的美。這實際上是壯族人民剛強性格和他們審美情趣的具體體現”[14]。
銅鼓面上的立蛙和累蛙造型也是對蛙神的崇拜,銅鼓的類似呱呱蛙鳴的洪亮聲響可以穿越長空傳遞向雷神求雨的功能,累蛙抱對又體現了生殖崇拜的內涵。
(四)文化藝術表現上的相通
四、結語
以稻作為基礎的文化內容滲透到壯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壯族神話大多與稻作相關;壯族社會中將稻田和稻米視為財產的象征;有完整成套的稻耕技術、飲食文化和相應的宗教儀式和人生禮儀,稻作文化還體現在故事、歌謠、戲曲、舞蹈等文學藝術領域中。現如今在廣西地區依然有著許多著名的優良稻作品種,其季節安排、選種育秧、插秧耘田、管理儲藏的技術都相當卓越,磨礪出壯族人堅韌沉穩、勇敢細致的民族性格,壯族人的血液中流淌著稻作文化的基因,世代相傳、生生不息。
綜上所述,“螞 節”和花山巖畫都是壯族稻作文明青蛙崇拜的文化表征,表明了壯族蛙崇拜民族意識具有久遠的歷史性,寄托著壯族人民希望稻作豐收、種族繁衍的美好愿望,滲透著壯族人民質樸、沉穩、向上的民族精神,顯示著壯族獨具特色的審美追求。作為同在大河邊緣的壯族同胞兄弟,雖然左江流域與紅水河流域中間隔有一段地理距離,但在共同的稻作經濟基礎和稻作生產生活實踐之上出于對暴雨洪水、久旱不雨、高山密林的恐懼和人丁興旺、風調雨順、稻作豐收、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在滔滔奔騰的大河邊以銅鼓為核心道具的巫術祭祀的儀式活動表達同樣的蛙神信仰觀念,展現了以水稻種植為基礎的以青蛙為核心文化意象的稻作文化內涵,在蛙神身上凝聚了他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功利目的。壯族人民在這樣的全民聚會狂歡活動中獲得精神的歸屬和心理的安慰、情感的抒發和宣泄,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和信心,社會治理者通過這樣的活動獲得了族群的認同與統治的合法性,共同彰顯了壯族人民借助青蛙崇拜表達的對生命永恒、種群繁衍、稻作豐收的追求,對自然萬物的崇拜,人與萬物生存發展休戚相關,表現了人類永恒的生命、生存主題,體現了壯族人民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熱愛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智慧,是壯族生態文化觀念的最集中反映,在現代科學生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依然是對于現代社會具有借鑒意義的生態典范。壯族的青蛙崇拜客觀上實現了生物平等基礎上的動物保護,原生態的稻作生產模式也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利于壯族地區的生態平衡,真正實現了當地的青山綠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蛙聲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