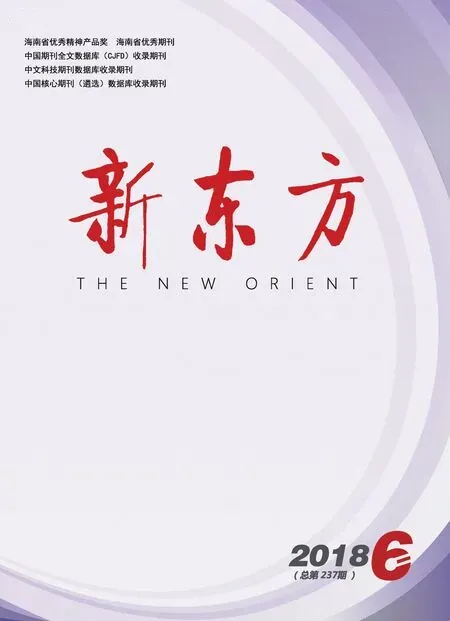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爭鳴史研究
劉洪霞
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之交(以下簡稱七八十年代之交)正是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時期,文學(xué)也經(jīng)受著“震蕩”與“沖擊”。按照批評界的解釋,“十七年文學(xué)”與“新時期文學(xué)”在此期間形成“斷裂”的地帶。在這個思想相對活躍的時期,思想界出現(xiàn)了各種論爭。文學(xué)界在這一時期也出現(xiàn)了許多有爭議的刊物和作品,其中圍繞某些文學(xué)刊物與作品的爭議還上升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xué)事件”。直到今天,無論是當(dāng)事人,還是其他人,還在評說著當(dāng)年的爭論。當(dāng)然觀點(diǎn)與當(dāng)時已經(jīng)不盡相同,但它們是令文學(xué)史無法忘卻的記憶。這也許就是“爭鳴”刊物與作品的魅力,“爭鳴”是這個轉(zhuǎn)型時期的重要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文學(xué)爭鳴有著重要的意義,因?yàn)椤拔膶W(xué)爭鳴不是一種孤立的現(xiàn)象,它是政治的、社會的、文藝的等各種力量與思潮碰撞、沖突的產(chǎn)物。通過文學(xué)爭鳴不僅可以透視出一個社會在政治、經(jīng)濟(jì)、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諸多問題,而且可以在文學(xué)理論、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學(xué)欣賞、文學(xué)管理等各個方面,提供出許多新信息、新觀念、新經(jīng)驗(yàn)。”①張學(xué)正.爭鳴的環(huán)境、規(guī)則與風(fēng)度[M]//1949—1999文學(xué)爭鳴檔案——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爭鳴實(shí)錄.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2002.那么,本文將在這里做一個嘗試,希望能夠整合到目前關(guān)于“爭鳴”的資源,返回到那一時期“爭鳴”的場景中,把它形成一個整體,給予全方位的考察。通過分析“爭鳴”的社會環(huán)境與歷史成因,借助有影響力的文學(xué)刊物與重要的有爭議作品,將其納入文學(xué)史的脈絡(luò),來探討為什么這一時期會發(fā)生如此大規(guī)模的爭鳴?這樣將有利于呈現(xiàn)出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爭鳴”的完整的脈絡(luò),填補(bǔ)文學(xué)史中有關(guān)爭鳴史的欠缺,應(yīng)該是一個有意義的努力。
一、當(dāng)代文學(xué)爭鳴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
從獲得的資料來看,對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爭鳴的研究呈現(xiàn)出不對稱性。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的研究,一個是在八十年代的即時性的對有爭議作品的評論,帶有著八十年代濃重的時代色彩。在極端二元對立的視野中,有的作品被批判,有的作品被褒獎。這一時期的爭鳴并不是文學(xué)層面的討論。實(shí)際上對這一時期文學(xué)“爭鳴”的研究并沒有被客觀化與歷史化。另一個則是近年來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有爭議的作品被紛紛重讀。新的觀點(diǎn)已經(jīng)與八十年代的看法迥然不同。這時的研究是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并不去爭論作品的好壞,并不做二元對立的價(jià)值判斷,而是更加注重“爭鳴”原因的探索以及“爭鳴”文本呈現(xiàn)出的復(fù)雜性。
1989年,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由於可訓(xùn)、吳濟(jì)時、陳美蘭主編的《文學(xué)風(fēng)雨四十年——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爭鳴評述》,這里含蓋了對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爭鳴”的評價(jià)。他們認(rèn)為:“進(jìn)入新時期后的最初階段,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論爭,可以看作是前17年論爭的延續(xù),許多在前17年尚未解決的重大創(chuàng)作問題,都是在新時期的作品討論中獲得解決或獲得認(rèn)識的。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政治環(huán)境的逐漸寬松,這是最基本的條件,但我們更不能忽視這樣一點(diǎn):由于十年慘痛災(zāi)難給文學(xué)家們帶來的歷史反思、哲學(xué)反思以及在這一切啟發(fā)下民主意識、反盲從意識的萌生與增長。正是這些重要的內(nèi)在因素,使近十年的文學(xué)論爭顯得更加自由活潑,暢舒己見。這種歷史的進(jìn)步是令人欣喜的。”①於可訓(xùn),吳濟(jì)時,陳美蘭.文學(xué)風(fēng)雨四十年——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爭鳴評述·前言[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9.在這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xué)“爭鳴”被定了性,是“歷史的進(jìn)步”,原因是它解決了“前17年尚未解決的重大創(chuàng)作問題”。這種判斷式的研究在當(dāng)時是屢見不鮮的,帶有那個時代明顯的特色。該書也列舉了這一時期的爭鳴作品,在二元對立的視野中給予了評判。那個時期,作品不僅要被定性“好”與“壞”,而且被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也是如此之簡單。在這本書中,編者列舉了許多當(dāng)時對有爭議作品一正一反的觀點(diǎn),但并沒有去分析為什么會出現(xiàn)“爭鳴”,是什么因素導(dǎo)致了全社會的“爭鳴”。這時對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爭鳴”的研究不僅停留在二元對立的語境中,而且也的確沒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zhǔn)備去更深層次地探討這一時期文學(xué)“爭鳴”現(xiàn)象,而是更多地做了材料上的梳理。
1995年,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了黎風(fēng)的《新時期爭鳴小說縱橫談》,他自認(rèn)為對這本書的寫作是用“第三只眼”對爭鳴小說和小說爭鳴的“交互式掃描和再批評”,因?yàn)樗f“小說家看社會是一只眼,批評家看小說又是另一只眼”,所以他需要“第三只眼”。盡管這種想要跳出圈子之外,以冷靜客觀的視角去看待問題的想法是值得稱道的。但是,他仍然沒有跳出八十年代研究的思路。作者忽略了這些爭鳴小說產(chǎn)生的歷史環(huán)境,而只是注意到了爭鳴小說本身的效果。這是很典型的內(nèi)部研究的論文集,并且以作品作為獨(dú)立的章節(jié),之間沒有以文學(xué)史的線索穿起來,都散落在那里。每一部被討論的爭鳴作品都是一個獨(dú)立的單元,看不出它們關(guān)于爭鳴有著怎么樣的聯(lián)系。實(shí)際上那一時期的爭鳴是非常復(fù)雜的,僅僅對爭鳴小說做內(nèi)部研究是不能展示出那個復(fù)雜的社會狀況。
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對文學(xué)“爭鳴”的研究有著那個時代的局限。也許是因?yàn)闅v史沒有走遠(yuǎn),還不能對其作出反思;也許是因?yàn)槟且粫r期的“爭鳴”太過復(fù)雜,還無法對文壇論爭風(fēng)云和文學(xué)艱難歷程做全面的歷史澄清。它們的不足,直到今天才看得比較清楚。
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對文學(xué)爭鳴的研究其實(shí)還是停留在史料的梳理上。但是,與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觀點(diǎn)已經(jīng)不同。表面上似乎在羅列材料,實(shí)際上對材料的選擇本身就帶有主觀性。在這個新的時代語境下,對有爭議作品的看法發(fā)生著悄悄的轉(zhuǎn)變。
近年來,有爭議的作品被重評。“重評的目的,是要通過‘重返’文學(xué)史‘現(xiàn)場’,進(jìn)一步了解當(dāng)年文學(xué)生產(chǎn)的社會背景、氛圍和情緒,跨越那些覆蓋在文學(xué)史表面的夸張的修辭,從而對當(dāng)時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真實(shí)狀況獲得一個比較客觀和大致準(zhǔn)確的認(rèn)識。”①程光煒.重評“傷痕文學(xué)”[J].文藝研究,2005(1).這些研究成果已經(jīng)不再停留在20世紀(jì)80年代(以下簡稱80年代)對有爭議作品“好”與“壞”的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上,而是回答了爭鳴作品為什么會被爭議?是什么因素促成“爭鳴”的發(fā)生?在各種因素中,哪種因素成為了主導(dǎo),而導(dǎo)致了“爭鳴”的結(jié)果,等等。這種研究呈現(xiàn)出了被歷史遮蔽掉的許多東西,豐富了對這一段“爭鳴”歷史的認(rèn)識。
《文學(xué)“成規(guī)”的建立》②程光煒.文學(xué)“成規(guī)”的建立[J].當(dāng)代作家評論,2006(2).一文分析了《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時候》在當(dāng)時引起爭議的兩部作品。實(shí)際上這是兩部不同的作品。雖然它們在當(dāng)時都備受爭議,但是,一部在爭議中“勝出”,成為當(dāng)仁不讓的文學(xué)史經(jīng)典;而另一部卻因?yàn)槟承┰蛟跔幾h中“敗北”,被貶為文學(xué)史中批評的對象。可是實(shí)質(zhì)上兩部作品又是一樣的,都沒有脫離“傷痕文學(xué)”的框架,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卻有著不同的結(jié)果。那么,該文就主要分析了造成這不同結(jié)果的內(nèi)在原因是什么,從而揭示了這個時期文學(xué)發(fā)展的某些理路。文章不僅給出了兩部作品在相同的大前提下的某種細(xì)小的不同,而這種細(xì)小的不同是造成兩部作品朝著相反的評價(jià)方向的最重要原因。而且最重要的是,文章在這其中發(fā)現(xiàn)了某種文學(xué)“成規(guī)”,它像一個隱形的存在,左右著作品的命運(yùn)。那么問題又出現(xiàn)了:這一“成規(guī)”從哪里來,是與“新時期”俱來,是在此之前的某種胚胎,還是在“新時期”以后逐步產(chǎn)生的整體?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這里面其實(shí)也存在著眾多的交織。也許可以這樣說:“當(dāng)歷史暫時放緩對文學(xué)知識強(qiáng)制性的壟斷之后,繁雜不一的知識譜系便會蜂擁而出;但是,這樣一來,會對歷史秩序形成某種威脅。于是,又要‘收緊’,然而如此卻不利于‘寬松環(huán)境’,所以接著又‘放’——這種且進(jìn)且退、既這又那的矛盾現(xiàn)象,在80年代初的文學(xué)批評中的表現(xiàn)尤具代表性。”③程光煒.“人道主義”討論:一個未完成的文學(xué)預(yù)案——重返80年代文學(xué)史之四[J].南方文壇,2005(5).那么也就是說,《班主任》與《晚霞消失的時候》都是在“歷史暫時放緩對文學(xué)知識強(qiáng)制性的壟斷之后”的產(chǎn)物,但遺憾的是,“收緊”與“放”也是有限度的,《班主任》恰好是在“放”的范圍之內(nèi),而《晚霞消失的時候》是在“收緊”的范圍之內(nèi)。這樣一來,在當(dāng)時所有評價(jià)《班主任》的“好”,也就有了更客觀的評價(jià),它的“實(shí)際價(jià)值”在歷史的天平上被重新衡量。依此類推,當(dāng)時對《晚霞消失的時候》的評價(jià)的“壞”,也同樣要重新來過。也許當(dāng)歷史需要被重新審視的時候,每一個細(xì)節(jié)也許都不會被放過。那么,“歷史是被成功者書寫的”,也許是一個偽命題。因?yàn)椋瑲v史更是被敘述的,而敘述者的更替就是時間的更替,不能改變。這種研究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內(nèi)部研究,而是“跳出去”的外部研究。
這是對有爭議作品的重讀,這種方式顯然不同于以前,這種研究需要揭示的是,造成這種狀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的問題。“重讀”的前提是一種不滿,不滿于當(dāng)前文學(xué)史的敘述。因?yàn)椤爸刈x者”在質(zhì)疑,以犧牲歷史現(xiàn)象的豐富性而突出當(dāng)下社會的必要性,只記述一面真實(shí)性而削減、掩蓋了另一面真實(shí)性的文學(xué)史表述,這難道是一種“真正”直面歷史的態(tài)度?所以,“重讀者”才產(chǎn)生了在已有文學(xué)史中尋找文學(xué)史的沖動。但是,這是一種大規(guī)模的“重讀”,涉及到的問題是方方面面,未能從“爭鳴”的角度給予過多的關(guān)照,而顯得問題沒有集中到“爭鳴”上來。因?yàn)閷?0年代文學(xué)的考察,“爭鳴”是無法回避的關(guān)鍵詞。也許它就是揭開七八十年代之交爭鳴史奧秘的一把金鑰匙。
二、當(dāng)代文學(xué)爭鳴史研究的意圖與路徑
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xué)界之所以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爭鳴”,是因?yàn)檫@一時期生成了“爭鳴”的環(huán)境。“十七年文學(xué)”中也有爭論,但是兩者的爭論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因?yàn)椋笆吣晡膶W(xué)”并不存在“爭鳴”的環(huán)境,那是一個造神運(yùn)動的時代,有著絕對的真理與信仰。即使出現(xiàn)過小范圍的“爭鳴”,那么緊接著對其的壓制,也是為了進(jìn)一步確保主流文化的“真理”地位。主流文化急需對歷史敘述進(jìn)行新的調(diào)整。這種調(diào)整雖然牽涉到對過去歷史的重評,但它必須借助文學(xué)的力量,這就使文學(xué)參與歷史的重新敘述提供了某種先機(jī)。與此同時,客觀上也造成文學(xué)與主流文化在歷史解釋問題時的矛盾和緊張。歷史語境的變化,構(gòu)筑起文學(xué)“爭鳴”的天然平臺。在這個改革的思想輿論環(huán)境中,中央召開了第四次文代會,號召文藝界要“解放思想”,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鄧小平在《祝辭》中告訴文藝界:“文藝這種復(fù)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么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對文藝界無疑是一個重大的保證。“我們要允許爭,倡導(dǎo)爭,而且要敢于爭,正確對待爭,這樣,我們才能爭出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爭出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春天。”①鄭晉安.“百家爭鳴”關(guān)鍵在于爭[J].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79(4).那么,“爭鳴”已經(jīng)在新時期不僅合法,而且是大力倡導(dǎo)的。
新中國成立后,“百家爭鳴”成為指導(dǎo)科學(xué)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一個方針,是從政治層面來確定它的指導(dǎo)性地位。但是,洪子誠則認(rèn)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有確定內(nèi)涵的概念,對它的闡釋也很難歸入‘學(xué)術(shù)’的范疇。它是國家和執(zhí)政黨處理其與知識分子復(fù)雜關(guān)系的‘政策’。‘政策’根據(jù)社會政治情勢,根據(jù)政策制定者所代表的階級和社會集團(tuán)的利益加以制定,當(dāng)然也會根據(jù)情況的變化不斷予以調(diào)整和修改。離開這一基點(diǎn)去討論這一方針的‘真正’涵義,辯明怎樣才能對其‘正確’理解,都可能是找錯了路徑。這是因?yàn)椋皇┬姓吖倘豢梢詫@項(xiàng)政策說三道四,但最后的解釋權(quán),卻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這是被雙百方針提出和實(shí)施的歷史過程所證實(shí)的。”②洪子誠.雙百方針[M]//洪子誠,孟繁華.當(dāng)代文學(xué)關(guān)鍵詞.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51.洪子誠的這一思想的確在1957年的“反右”運(yùn)動中得到體現(xiàn)。而“雙百方針”真正得以貫徹的是在1956年和1957年的上半年,接下來,“大鳴大放”后的結(jié)果是真正的“消音”。之后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迎來了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一次從政治層面得到確認(rèn),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使得凍結(jié)在文藝工作者心頭的堅(jiān)冰一點(diǎn)點(diǎn)消融,“百家爭鳴”的局面也再一次形成,新時期文學(xué)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形成了自己的面貌。但是,這個時期的“爭鳴”并不是那么單純,以往被過于簡化了的歷史需要在本文中盡力得到復(fù)雜的呈現(xiàn),進(jìn)一步去清晰化“爭鳴”與“文學(xué)秩序”之間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什么是秩序?福柯認(rèn)為:“秩序……是事物固有的內(nèi)在法則,決定事物間相互比較方式的隱含網(wǎng)絡(luò)”,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隱含于這種秩序之中,“科學(xué)理論或哲學(xué)闡釋的任務(wù)在于,說明為何秩序普遍存在著,它遵循什么樣的普遍法則,用什么原理可以說明它,以及為什么是這些特殊的秩序而非其他一些秩序建立起來。”①Foucault, Michel: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20.離開秩序,人們無法對知識構(gòu)成的規(guī)律作出準(zhǔn)確的判斷和說明。對事物秩序的探詢過程,也就是對知識形成和學(xué)科建構(gòu)規(guī)律的探詢過程。事物的秩序深深地嵌入話語實(shí)踐行為之中,相當(dāng)隱蔽、相當(dāng)模糊,因此也就不易分析。對此只有進(jìn)行耐心的假設(shè)和求證,此外別無他途。不經(jīng)過艱苦的考古挖掘,精神世界的沉積層和以往歷史形成的秘密將永遠(yuǎn)不會自動浮出學(xué)術(shù)地表,自動地呈現(xiàn)于人們面前②張清民.話語與秩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5:2-3.。所以說,欲要弄清楚“爭鳴”的真實(shí)原因以及它背后的文學(xué)秩序的狀態(tài),必須以考古學(xué)的精神去對待。
表面上熱熱鬧鬧的爭鳴,在不清楚內(nèi)幕的人看來,就是捍衛(wèi)自我一方觀點(diǎn)而與對方或更多方發(fā)生的爭執(zhí)。而實(shí)際上,某些事情并不是它表面上呈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象,要遠(yuǎn)比這些復(fù)雜得多。“當(dāng)今的學(xué)術(shù)界,正在對‘歷史’進(jìn)行反思。一些學(xué)科通過類似于‘知識考古學(xué)’的方式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仿佛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的觀念進(jìn)行梳理,從中發(fā)掘出新的東西。”③彭兆榮.當(dāng)歷史違背歷史的時候[M]//口述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4:136.研究這段爭鳴史需要對歷史文本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的解讀,“就像托馬斯·庫恩所說的那樣,科學(xué)研究者‘必須學(xué)會在某些熟悉情境中看到一種新的格式塔’,即從人們司空見慣的舊對象中看到全然不同的新東西,仿佛置身于一個陌生的領(lǐng)域一般。此外,他還應(yīng)當(dāng)具有這種本領(lǐng):把盡人皆知的事物改造成為一個仿佛陌生的東西,把常識變成理論,把現(xiàn)象變成問題,通過新的閱讀和闡釋,把理論的地平線的遠(yuǎn)景無限后推,使理論自身獲得一個自由發(fā)放的空間和張力。”④張清民.話語與秩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5:5.到目前為止,許多人仍然認(rèn)為80年代之所以出現(xiàn)了那么多被爭議的作品,是因?yàn)樽髌繁旧沓隽藛栴}。實(shí)際上并不盡然。所以,本文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改變和扭轉(zhuǎn)人們頭腦中這些固有的思想,“爭鳴”的發(fā)生并不是作品本身簡簡單單的問題,而是以這部有爭議的作品作為原點(diǎn),圍繞在這部有爭議作品的周邊有太多的因素都參與進(jìn)來,甚至一個文學(xué)編輯的態(tài)度都在左右著作品的命運(yùn),影響到新的文學(xué)秩序的重建。這似乎有著重建歷史的企圖和沖動,甚至有些想象性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必須明確的是,這種重新建立的歷史,與過去形成的觀點(diǎn),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歷史學(xué)僅僅因?yàn)樗鼘裉斓娜藗冇幸饬x才作為社會活動幸存下來。昔日的聲音對今日至關(guān)重要。但是所聽到的是誰的聲音。”⑤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序言[M].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在眾生喧嘩的“爭鳴”聲中,不同的聲音一定是代表著不同的力量,所以能夠清晰地辨認(rèn)出各種力量的聲音以及它們的強(qiáng)弱,可以判斷出由此而形成的新秩序的樣態(tài)。
“爭鳴”的原因與方式可以通過史料具體呈現(xiàn)出來,但同時也將會出現(xiàn)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爭鳴的過程中當(dāng)時呈現(xiàn)出了怎樣的文學(xué)樣態(tài)。“爭鳴”與“文學(xué)秩序的重建”在時間上是統(tǒng)一的,在“爭鳴”的過程中,新的秩序同時在悄悄地形成。但是,這顯然不是從“此”到“彼”那樣簡單。這里面有著復(fù)雜的纏繞,各方力量的猶疑、退讓、堅(jiān)持等。那么,爭鳴史研究的重點(diǎn)力量就是要放在這復(fù)雜的纏繞中。再具體地說,就是要弄清“爭鳴”與“文學(xué)秩序重建”兩者究竟是怎樣復(fù)雜的關(guān)系,一定要避免草率斷定是由于“爭鳴”而導(dǎo)致的“文學(xué)秩序重建”,事情遠(yuǎn)遠(yuǎn)沒有那么簡單,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關(guān)系。
實(shí)際上,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某個時期能否“爭鳴”不是一個能簡單發(fā)生的事情。當(dāng)然這里的“爭鳴”的含義需要予以界定,因?yàn)槿魏螘r期都會產(chǎn)生爭鳴作品、爭鳴事件,這是極為正常的事情,但是這里的“爭鳴”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呼聲中,在社會政治、思想發(fā)生重大調(diào)整時,這個時候的“爭鳴”關(guān)系到某些“舊秩序”的改變和“新秩序”的建立的問題。當(dāng)然,“爭鳴”的本身也暗示了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中某種東西的松動與調(diào)整。所以,對“爭鳴”的研究是有重大意義的,它能讓我們看清楚某些文學(xué)與政治、文學(xué)與經(jīng)濟(jì)等等的關(guān)系。并且“爭鳴”本身就帶有“眾多”“復(fù)雜”“雜亂”“多聲調(diào)”的含義,那么,從“眾聲喧嘩”中去理順糾纏在一起的絲絲縷縷,這就是“整合”后的“細(xì)化”:把整體中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放在歷史的顯微鏡上一一放大,清晰到它的細(xì)枝末節(jié)。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有一個弊病,也許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對,那就是對事件、問題的模糊化處理法。不去針對問題的本質(zhì),而是說一些無關(guān)痛癢的話,這多少有些逃避問題的嫌疑。然而,對于本來就是“爭鳴”的問題,面對的是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審慎的態(tài)度是必不可少的,歷史化的做法是比較合適的出路。
80年代的“爭鳴”很少從文學(xué)層面來爭議作品,而是從政治、道德、文化的角度去判斷作品的好壞。80年代的“爭鳴”史貫穿了痛苦、迂回、政治、人性、文學(xué)、非文學(xué)種種復(fù)雜因素,這諸多的因素的累加的和就是呈現(xiàn)給我們的80年代文學(xué)新秩序。那么,去放大和放緩80年代文學(xué)秩序重建的過程,就是把“爭鳴”的歷史細(xì)節(jié)化。重新解讀與分析當(dāng)時引起轟動的被爭議作品,以及被爭議事件、被爭議的刊物,都是重新進(jìn)入這段爭鳴史的路徑。對有爭議作品、事件、刊物的研究,意在借此重新刷新那段歷史,而不是在茍同已有的觀點(diǎn),是“在已有的文學(xué)史中尋找新的文學(xué)史的沖動”。
三、文學(xué)爭鳴作品與刊物
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期發(fā)生了“爭鳴”?這個時期的“爭鳴”有著它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與歷史成因,在“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各個階層,編輯、作者和讀者達(dá)成了相當(dāng)?shù)囊恢隆!敖夥潘枷搿笔亲钌畹萌诵牡脑捳Z,所以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在精神層面去擁護(hù)。但實(shí)踐起來,“解放思想”可謂是千差萬別。每一個人對“解放思想”都有著各自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有著嚴(yán)重的分歧,尤其在對文學(xué)藝術(shù)的理解上,很難達(dá)到一致。于是,矛盾產(chǎn)生了。有了矛盾,自然就產(chǎn)生了“爭鳴”。
“爭鳴”的陣地主要是文學(xué)刊物。80年代各種期刊雨后春筍般地生長起來,數(shù)量最多的當(dāng)屬文學(xué)刊物。那是一個文學(xué)的時代,全社會的熱情似乎都集中在文學(xué)這一焦點(diǎn)上。那時候有很多文學(xué)青年,他們?nèi)琊囁瓶实亻喿x文學(xué)刊物。而“爭鳴”的方式與形態(tài)是通過文學(xué)刊物表現(xiàn)出來的。《作品與爭鳴》《文藝報(bào)》與《時代的報(bào)告》等刊物是那一時期重要的爭鳴刊物。它們是“傳聲筒”,不同的“爭鳴”聲就是從它們那里傳出來的。近幾年來對文學(xué)刊物的研究也成為熱點(diǎn)。過去的大大小小的刊物,有過影響的、影響很大的、甚至影響很小的刊物,都逃不過研究者的眼睛,他們想以此作為還原歷史的最佳途徑,這就是舊刊物的魅力。
文學(xué)刊物參與了“爭鳴”,當(dāng)然也參與了文學(xué)秩序的重建。《文藝報(bào)》《作品與爭鳴》與《時代的報(bào)告》這樣在當(dāng)時有影響力的刊物當(dāng)然是“爭鳴”的主戰(zhàn)場,是“炮火聲”最猛烈的地方。“一種雜志和報(bào)紙副刊可以形成一種文學(xué)思潮和文學(xué)流派。當(dāng)代中國,一種雜志或報(bào)紙也能折射出政治思潮和政策路線。”①王本朝.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14.《文藝報(bào)》是思想解放的代表性力量,在極大程度上參與了新時期文學(xué)秩序重建的工作。它與保守派力量《時代的報(bào)告》博弈的過程充滿了曲折和矛盾。在這過程中,《文藝報(bào)》也重新建構(gòu)了自我的新時期的形象,為自我角色做了新的定位。各種復(fù)雜的因素圍繞在《文藝報(bào)》的周圍,使得它的解放程度并不是那么沒有限度,也使得“爭鳴”的聲音顯得并不是那么純粹。《文藝報(bào)》作為權(quán)威刊物,可以成為我們窺探那一時期“爭鳴”的窗口,它是參與文學(xué)新秩序建立的主要力量。《作品與爭鳴》這一刊物帶有明顯的80年代的特點(diǎn),不僅表現(xiàn)在刊物的命名上,更表現(xiàn)在它的辦刊方針上。它不同于《文藝報(bào)》,有一個“爭鳴”的對手。它的對手恰恰是它的自身。《作品與爭鳴》幾乎是與自身“爭鳴”,因?yàn)樗母鱾€欄目之間充滿了矛盾與緊張,既出現(xiàn)“正統(tǒng)”的姿態(tài),又出現(xiàn)“另類”的態(tài)度。在同一本刊物中,形成了多張面孔。實(shí)際上,這恰恰是這個時期思想“爭鳴”的一個生動寫照,毫無保留地在這本刊物中呈現(xiàn)出來。文學(xué)刊物作為一個公共領(lǐng)域,它直接參與到文學(xué)秩序的整合。應(yīng)該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執(zhí)政黨開始著手對文化生產(chǎn)資料實(shí)施完全掌控,對生產(chǎn)過程實(shí)行全面領(lǐng)導(dǎo),也使以媒介、出版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公共領(lǐng)域’,變成了一個個媒介機(jī)構(gòu)和單位。公共空間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民間’也完全被單位和機(jī)構(gòu)所取代。公共領(lǐng)域的解體也潛在地影響到文學(xué)的生產(chǎn)方式,文學(xué)離國家和單位似乎更近了,與社會和民間的距離卻被拉大了。”②王本朝.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05.這里說的是1949年以后。但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情況又有所不同,那就是這個時期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之下,文學(xué)傳媒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定會有異常的表現(xiàn)。例如《文藝報(bào)》與《作品與爭鳴》,它們對解放思想是響應(yīng)的,所以在辦刊中一定有這樣的表現(xiàn)。但同時,作為國家體制內(nèi)的刊物,它又不能走得太遠(yuǎn)。所以,從這些刊物本身就能看到那個時期的矛盾,新文學(xué)秩序建立的復(fù)雜。
有爭議作品是那個時期表現(xiàn)最明顯的一種文學(xué)重建的參與方式。它的影響幾乎超越了文學(xué)界,擴(kuò)展到全社會,使得除了專業(yè)讀者以外,普通讀者也參與到對作品的“爭鳴”中去。這些作品是那個思想混亂年代的載體,通過這些作品,人們在表達(dá)著自己的或者“解放”、或者“保守”的思想。而更為嚴(yán)重的是,某些有爭議作品代表著某些政治力量的導(dǎo)向。雖然表面上宣傳的聲音在說,“這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但實(shí)際上,“百家爭鳴”的空間是被局限在一定范圍中。通過對《晚霞消失的時候》《人啊,人》《班主任》這幾部有爭議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到新的秩序建立時的博弈過程中的“險(xiǎn)象環(huán)生”。
當(dāng)時對每部作品的不同意見,都涉及到當(dāng)時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例如人道主義、啟蒙話語、現(xiàn)代派等問題。通過對作品的研究把那一時期爭論的問題加以整合,使得這個時期的“爭鳴史”成為一個整體,然后,再細(xì)化到每一個爭論的局部。當(dāng)然,不是僅僅考慮作品的本身,就事論事,而是由對作品的爭論生發(fā)出去。《晚霞消失的時候》是一部充滿了內(nèi)在沖突的作品,文本聲音與作者訴說發(fā)生碰撞,主流批評與作者反批評存在對峙。對這篇作品的不同意見,實(shí)際上關(guān)系到當(dāng)時的所謂“解放派”內(nèi)部分歧的問題,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解放”和“保守”的簡單、絕對區(qū)分是不可行的,關(guān)系到“思想解放”的限度和不同想象。就是因?yàn)閷λ枷虢夥畔胂蟮牟煌髡叨Y平才會在作品中出現(xiàn)了對宗教的追求。如果沒有對宗教的追求,這部作品是在“傷痕文學(xué)”的范疇之中的,也應(yīng)該與《班主任》一樣受到褒獎。然而,卻與之遭遇了不同的命運(yùn)。所以說,思想解放尺度的差異是產(chǎn)生“爭鳴”的直接原因。《班主任》則成了文學(xué)史經(jīng)典中的“尷尬”角色。也許誰都要經(jīng)受歷史的淘洗,甚至包括一部作品。曾經(jīng)的“傷痕文學(xué)”的開山之作,新時期文學(xué)的經(jīng)典,也仍然要在歷史的天平上重新來過。《班主任》基本上是恢復(fù)“啟蒙話語”的作品,它在后來受到的質(zhì)疑,也是20世紀(jì)90年代對“啟蒙話語”進(jìn)行檢討的一個部分,當(dāng)然也涉及對“文學(xué)性”的不同看法。
通過文學(xué)刊物與有爭議作品,也許會發(fā)現(xiàn),這個時期“爭鳴”與“重建”充滿了矛盾和緊張的關(guān)系。80年代鼓勵“爭鳴”,但有底線,意識形態(tài)方面猶豫不決,反反復(fù)復(fù),這說明了什么?即“解放派”和“保守派”都要掌握對文學(xué)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所以在作品評價(jià)上爭論不休。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成規(guī)受到威脅,有關(guān)方面想建立新的成規(guī),文學(xué)的大膽探索和急速發(fā)展又不讓他們有這種機(jī)會。這大概就是圍繞“爭鳴”而呈現(xiàn)的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xué)樣態(tài)。
離開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xué)“爭鳴”,直到今天,人們發(fā)現(xiàn)歷史的公案遠(yuǎn)遠(yuǎn)沒有結(jié)束。這些曾經(jīng)在80年代或者“出過風(fēng)頭”、或者遭受批判的有爭議作品,并沒有隨著時間的逝去而煙消云散,它們是那段爭鳴史上永恒的焦點(diǎn)。仍舊有人在繼續(xù)著當(dāng)年的爭論,這包括當(dāng)事人、當(dāng)年的參與者以及沒有經(jīng)歷過那場“爭鳴”的人。同時人們也發(fā)現(xiàn),被爭議的作品的文學(xué)史位置也在悄悄地發(fā)生著調(diào)整,難道這是新一輪“爭鳴”嗎?還是其他的原因呢?也許是因?yàn)闅v史是連續(xù)的,“爭鳴”也就具有了持續(xù)性。那么與之相關(guān)的文學(xué)秩序呢?也就因此獲得了它的動態(tài)性。但是,作品何為呢?它們僅僅是作品。也許,“爭鳴”就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在“爭鳴”中,某些東西被解構(gòu)掉,某些東西被重建;接著,被重建的東西又被解構(gòu)掉,被解構(gòu)掉的東西又被重建,這當(dāng)然不是簡單的循環(huán)論。曾經(jīng)在文學(xué)史上被列為經(jīng)典的作品,在今天也不得不面臨著位置的調(diào)整;而曾經(jīng)被批判的作品,卻獲得了歷史的同情,大有要摘得文學(xué)史桂冠的勢頭。它們更像一個個思想潮流中的標(biāo)靶。然而,“任何人的再批評都不是終極裁判,依然只能是見仁見智,各抒己見,這是一種心靈飛騰的自由和精神馳騁的快慰。真正的裁判,只能是歷史,唯有它才能證明所有發(fā)生和存在的價(jià)值。”①黎風(fēng).新時期爭鳴小說縱橫談·小序[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5.那么,“歷史學(xué)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們建立起與過去的各種聯(lián)系,借此而解析現(xiàn)在的疑難,啟發(fā)未來的潛能。”②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9.“爭鳴”本應(yīng)該是代表著寬容、解放與民主。然而,這一時期的“爭鳴”似乎更復(fù)雜。這次自上而下的“爭鳴”得到了文學(xué)界不同程度上的響應(yīng)。通過“爭鳴”,這一時期的文學(xué)秩序有著很大的調(diào)整,能夠允許更多的聲音存在。但遺憾的是,有的“爭鳴”還是淪落為話語權(quán)的爭奪。恢復(fù)那一時期“爭鳴”的場景,是為了今日的民主與文明。然而,它依然是任重而道遠(yuǎ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