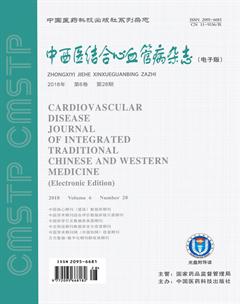抗炎1號治療慢性濕疹療效觀察
李艷 史丙俊 張穎 江雪 邱志梅 刁慶春
【摘要】目的 觀察抗炎1號治療慢性濕疹的療效。方法 選取2018年1月~6月重慶市中醫(yī)院皮膚科門診治療的慢性濕疹患者60例作為研究對象,將其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0例,對照組予鹽酸非索非那定片120 mg,口服,1次/d,復方樟腦乳膏適量外用。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chǔ)上加用抗炎1號,飯后服,1次/d。兩組的療程均為2周,治療期間不對患者的生活方式進行干預。結(jié)果 觀察組患者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結(jié)論 鹽酸非索非那定片及復方樟腦乳膏聯(lián)合應用抗炎1號療效優(yōu)于單用鹽酸非索非那定片及復方樟腦乳膏。
【關(guān)鍵詞】抗炎1號;慢性濕疹;血虛風燥夾濕熱證
【中圖分類號】R275.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ISSN.2095-6681.2018.28..02
濕疹(Eczema)是由多種原因共同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滲出傾向的皮膚炎癥反應。中醫(yī)稱本病為“濕瘡”。早在《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就已經(jīng)提出“諸痛癢瘡,皆屬于心,諸濕腫滿,皆屬于脾”。清代醫(yī)家石壽棠《醫(yī)原》提出“水流濕,火就燥,故水火二氣,為五行之生成;燥濕二氣,為百病之綱領(lǐng)”[1]。很多疾病可由燥濕相兼致病。本病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易復發(fā),單純用西藥治療難以控制及延長復發(fā)時間。加用中藥療效會明顯改善。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1月~6月重慶市中醫(yī)院皮膚科門診治療的慢性濕疹患者60例作為研究對象,均符合《臨床皮膚病學》慢性濕疹的診斷標準[2]。將其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0例。其中,觀察組男22例,女8例,對照組男20例,女10例,年齡>50歲。兩組在年齡、性別及病程上具有可比性。兩組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慢性濕疹診斷標準;(2)辯證符合血虛風燥夾濕熱證;(3)無其他皮膚科疾病及其他系統(tǒng)疾病。排除標準 :(1)有生育要求者;(2)對本研究所用藥物過敏者;(3)合并其他系統(tǒng)疾病,生活自理能力差,主觀表述困難者;(4)未按規(guī)定用藥,中途加藥或換藥者。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予鹽酸非索非那定片120 mg,口服,1次/d,復方樟腦乳膏外用,每日兩次。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藥物的基礎(chǔ)上加用抗炎1號方,飯后半小時開水沖服,1次/d。兩組的療程均為2周,治療期間不對患者的生活方式進行干預。藥物組成:雷公藤20 g,寬筋藤15 g,甘草3 g。本病主要辯證為血虛風燥夾濕熱證,辯證參照《中醫(yī)外科學》第二版,癥候表現(xiàn)為:皮損色暗、色素沉著、皮損出粗糙肥厚、劇烈瘙癢,遇熱加重、伴口干、心煩、小便短赤、舌淡紅、苔薄黃,脈弦滑。
1.4 療效判定標準
根據(jù)EASI進行癥狀評分[3]:紅斑(erythema,E),硬腫(水腫)/丘疹(induration(edema)/papulation,I),表皮剝脫(excoriation,Ex),苔蘚化(1ichenmcation,L)。每一臨床表現(xiàn)的嚴重度以0~3分計分,0=無,1=輕,2=中,3=重。各種癥狀分值之間可記半級分,即0.5。有效率=(痊愈例數(shù)+顯效例數(shù)+好轉(zhuǎn)例數(shù))/總例數(shù)×100%。
2 結(jié) 果
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后療效的對比,觀察組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 討 論
濕疹是臨床上常見的一種變態(tài)反應性疾病,可由急性、亞急性濕疹轉(zhuǎn)變而來,表現(xiàn)為患處劇烈瘙癢、皮膚增厚、色素沉著、表面粗糙、苔蘚樣變,邊緣較清楚,多對稱性分布,本病受生活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較大,極易復發(fā)。中醫(yī)稱本病為濕瘡,古代早已有本病的提及,《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風為百病之長,散行而數(shù)變,故本病劇烈瘙癢。《醫(yī)宗金鑒·血風瘡》:“浸淫瘡此證由肝、脾二經(jīng)濕熱,外受風邪,致遍身生瘡。”肝為風木,脾為濕土,肝火太旺則克脾土,以致脾失健運,水濕泛濫[4]。本病由內(nèi)外因共同作用的。在正邪交爭的過程中而發(fā)病,素有“正氣存內(nèi)、邪不可干”及“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是發(fā)病的內(nèi)在依據(jù)。所以認為本病的病因是素體虛弱,脾虛濕邪困阻,肌膚失養(yǎng),因濕熱蘊久,耗傷陰血,化燥生風,而致血虛風燥,肌膚甲錯而發(fā)為本病。本文根據(jù)科室制定的抗炎1號方,選擇辯證符合血虛風燥夾濕熱證的患者進行治療。雷公藤之名始見于《本草綱目拾遺》[5]。具有祛風除濕、活血通絡、消腫止痛及殺蟲解毒的功效。本品單用有大毒。通過中藥配伍可以降低本品毒性[6]。雷公藤多苷抑制炎癥反應的作用機制是抑制炎癥遞質(zhì)、炎癥細胞因子及炎癥趨化因子的產(chǎn)生以及抑制Th17細胞作用而實現(xiàn)的[7]。雷公藤的不良反應主要集中在肝、腎、血液系統(tǒng)毒性等[8]。雷公藤毒副作用導致肝損傷與脂質(zhì)過氧化反應有關(guān),而甘草具有維持體內(nèi)自由基平衡, 誘導抗氧化和抗氧化的保護作用[9]。清代嶺南本草《生草藥性備要》始載寬筋藤,曰:“寬筋藤有消腫,除風濕,舒筋活絡”[10]。甘草以根及根莖入藥。具有補脾益氣、清熱解毒、去痰止咳、緩急止痛、調(diào)和諸藥的功效。甘草酸具有抗炎、保護肝細胞膜、免疫調(diào)劑等藥理作用[11]。雷公藤單用時毒性最大,雷公藤與甘草60:9時毒性最小[12]。雷公藤誘導肝損傷的作用可能會被甘草減弱[13]。患者病程日久,在血虛風燥的基礎(chǔ)上又出現(xiàn)濕熱的表現(xiàn),三味藥各自歸屬肝、脾、腎經(jīng),肝主風,風性主動,善行而數(shù)變。脾主肌肉,運化水濕,濕性重濁粘滯,濕熱易相間致病。腎為先天之本。三藥歸屬不同經(jīng)脈,各司其職,本方中雖僅有三味藥物組成,配方嚴謹、簡明扼要,減輕患者用藥的負擔,減輕患者的抗拒心理,增加患者依從性。
綜上,抗炎1號方治療慢性濕疹安全有效,值得臨床運用。
參考文獻
[1] 陳一凡,羅文軒,樊柄杰,孔煜榮,曲保全,王 彤.基于《醫(yī)原》淺論"燥濕兼夾"理論的臨床應用[J].貴陽中醫(yī)學院學報,2018,40(01):1-4.
[2] 趙 辨.臨床皮膚病學[M].3版.南京:江蘇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2:160-165.
[3] 趙 辨.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指數(shù)評分法[J].中華皮膚科雜志,2004(01):7-8.
[4] 王奕霖.濕疹的中醫(yī)病因病機[J].長春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18,34(01):79-81+108.
[5] 蘇桂花,苑述剛,馬少丹,張英杰,阮時寶.雷公藤的本草學及臨床應用研究[J].河南中醫(yī),2011,31(04):412-414.
[6] Liu Y,Zhong Q X,Qiu H H,et al.Study on attenuating hepatotoxicity of Tripterygium wilfordii through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J].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2017,42(16):3044-3048.
[7] 胡德俊,彭澤燕,何東初.雷公藤的藥理作用研究進展[J].醫(yī)藥導報,2018,37(05):586-592.
[8] 侯海榮,何秋霞,李曉彬,張姍姍,張 云,張軒銘,郭敬蘭,韓利文,劉可春.雷公藤的效/毒物質(zhì)基礎(chǔ)研究進展[J].現(xiàn)代醫(yī)藥衛(wèi)生,2018,34(07):1018-1020.
[9] 董 婉,李超英,楊 萌,孫 惠.有毒中藥配伍甘草增毒與減毒作用研究進展[J].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8,39(02):12-17.
[10] 吳鳳榮,曾聰彥,戴衛(wèi)波,梅全喜,陳小露.寬筋藤的本草考證[J].中藥材,2015,38(12):2632-2634.
[11] 李新秀.代謝抑制在雷公藤活性成分致其肝腎毒性中的作用研究[D].山東大學,2015.
[12] 馬 哲.雷公藤配伍甘草減毒增效研究[D].遼寧中醫(yī)藥大學,2011.
[13] Cao L J,Miao Y,Huan-De L I,et al.Progress on mechanism of Tripterygium wilfordii-induced liver injury and detoxification mechanism of licorice[J].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2015,40(13):2537-2541.
本文編輯:劉欣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