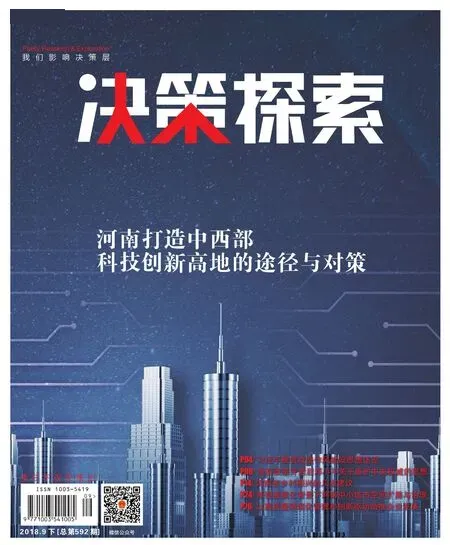矛盾論原理在近代革命中的運用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中國社會上沒有一個對社會狀況形成普遍認識的系統知識,所以當革命爆發時,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被我黨用來指導中國革命的進程。然而在漫長而又艱苦的發展歷程中,革命的形式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機會主義與教條主義在黨內盛行,此時的共產黨人迫切希望找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法。此時的困境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真切的理論渴望和實踐需求,希望能從哲學理論上解答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相互關系這一困擾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性課題。
一、矛盾論思想理論的背景來源
矛盾一詞最早出自《韓非子·難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也是成語自相矛盾的由來。矛盾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在俄國十月革命時期,列寧通過分析事物既對立又統一的原則來分析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在其畢生的諸多哲學著作中,圍繞辯證法的本質與核心進行了充分說明,進而表明對立統一法則是辯證法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且具有決定意義的法則。這是毛澤東提出矛盾論的理論基礎,在中國社會空前動亂、社會思潮雜亂無章的情況下,迫使人們去思考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問題,要求人們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進行正確的選擇。自十月革命傳來馬克思主義后,毛澤東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總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并對其得失進行系統分析,吸收了中國古代辯證法的矛盾同一性思想和現代科學的新成就,完整地系統地說明及發揮了對立統一原則的學說,而且通過自己的哲學基礎將這一學說具體地靈活地與中國革命相結合,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建立了中國革命的哲學理論體系與方針政策,并結合自身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豐富并發展了對立統一相結合的學說,繼而出現了“矛盾論”,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寶貴理論成果。毛澤東創造性地提煉出的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實踐法則,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辯證統一的矛盾法則,是我們黨在政治、組織、思想、路線上同“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同“左”傾教條主義進行斗爭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避免和消除主觀主義的錯誤危害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導。
二、主要矛盾在不同時期的轉變造成革命任務的改變
矛盾論是中國革命的辯證法,要求自覺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不斷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矛盾的特殊性。矛盾論原理的產生為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國情相結合提供了實踐基礎。依靠這一科學成果,剝離表象進而剖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激變和最深層次的根本矛盾,從而為我黨帶領人民群眾更有效地取得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中國近代的主要矛盾即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所以近代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反帝反封。
辛亥革命后,社會進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深化時期,社會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北洋軍閥統治上。《毛澤東選集》中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正是因為主要矛盾的轉變和民主革命的共同信念,所以才產生了國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由此,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共產黨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抓住主要矛盾,沒收地主土地和廟宇等所謂公產的土地,分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對于小田主則減租,強調貧農是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此時中國共產黨抓住社會主要矛盾。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愿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這是認清敵友,也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是順應民心。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拖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一致對外。這既是全國各族各階級人民的一致呼聲,也是矛盾論原理下,主要矛盾引發的必然結果。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轉變為階級矛盾,由中日矛盾轉變為中國人民與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單方面撕毀《雙十協定》后,解放戰爭打響,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可見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對時代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共產黨人在矛盾論原理的指導下,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特殊性的指導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確認識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一心一意為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行革命斗爭,最終取得偉大勝利。
三、以矛盾論原理看待中國革命勝利的必然性
近代中國由于深受腐朽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與以大地主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銳,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越發加深,這是革命產生的根本誘因,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并存于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斗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采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清楚地說明了革命產生的必然性。
近代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多方面歷史原因,帝國主義打開中國大門,使得國人被迫看世界、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客觀原因。同時,也包含了民族資本家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個人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的興起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嶄新的階級——無產階級。而隨著無產階級的產生和壯大,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出現。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廣大無產者和受壓迫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客觀世界發展的歷史規律,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
毛澤東闡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以及兩者的關系,進一步揭示了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和規律。同一性告訴我們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以彼此存在為前提,這解釋了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在特定時期、彼此爭斗的客觀事實。矛盾的斗爭性更加重要,斗爭性是矛盾的內核,是自始至終伴隨著矛盾的產生而產生、矛盾的消亡而消亡,因此矛盾的斗爭性是絕對的更是無條件的。正是矛盾的斗爭性才使事物有變化發展的動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斗爭,兩種對立的階級自形成以來便伴隨著潛在的斗爭性,只是由于雙方力量在沒有達成尖銳對立時才形成了一種平衡狀態,但這種狀態一旦被打破,即斗爭性的不可調和性完全展現出來,那么革命就必然產生了,斗爭發展到一定程度,舊的條件已經失去作用,就會使舊的統一體破裂,在此情況下,量變導致質變,矛盾雙方又在新的條件下構成新的統一體。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新陳代謝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客觀規律,即使是受到特殊原因的影響,使得其具有曲折性和復雜性,但最終的結果仍舊是新事物的產生與舊事物的滅亡。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新的力量,高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旗幟,承載著近代中國革新的歷史使命,必然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
四、矛盾論原理的當代價值
毛澤東的《矛盾論》蘊含著豐富且深刻的哲學內容,是在科學的理論基礎上通過具體實踐得以成立的,指引了中國在重大事件上作出正確的判斷。可以說矛盾論原理指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進步,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共產黨人至今依然使用矛盾論原理指導中國的建設和發展。通過學習《矛盾論》,深刻理解矛盾在事物形成中的作用是我黨作出正確分析的理論依據,是在社會生活中以矛盾論為指導使目的得以正確確立與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基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要有世界眼光,不僅要善于吸取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新成果,而且要善于總結和概括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等最新成果,善于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只有這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具有時代性、先進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與時代化是統一的。當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依托矛盾論原理,透過現象看本質,善于發現中國社會根本矛盾的變遷,時刻緊跟主要矛盾的變化進行自我革新,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