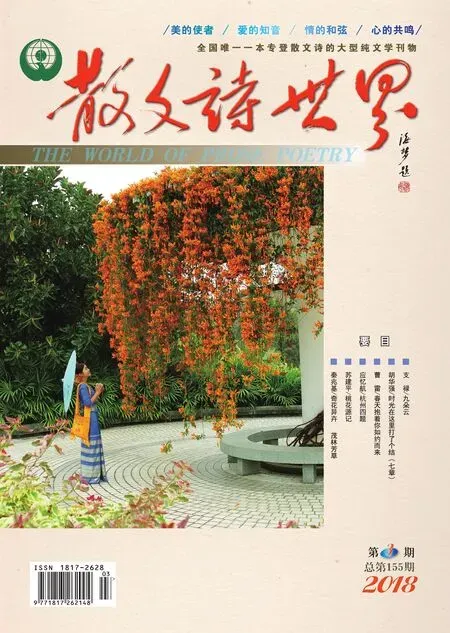我聞到歲月久窖的芳菲(五章)
安徽宣州孫埠高級中學(xué) 潘志遠(yuǎn)
雪就將遠(yuǎn)去
雪就將遠(yuǎn)去,我去送送它。
到野外田地里,河堤邊,草垛旁,或一切朝陽的山坡……
雪無言。許是有千言萬語卡在喉嚨,或不屑于言說,或還沒找到合適的言辭,或已根本不需要對我言說,但愿是后者。
雪很平靜,也很冷靜。從來的那一刻,一直保持著固有的生命的溫度;提升,只能加速其逃遁。
雪明白:讓人狂喜亢奮的日子已逝,厭棄產(chǎn)生,它被鏟除到路邊,被人反復(fù)踐踏,被一次次潑臟水。現(xiàn)在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盡快離去。
雪一天天消瘦。消瘦也不改其白,不失其白。即便死去,也清清白白。
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那些強(qiáng)加給它的玷污,此刻已經(jīng)澄清、分離、沉淀。
滴滴答答的,是它流淌的歡笑。可意會不可言傳,意中意,詩中詩,經(jīng)得起揣摩。
隨溪流淙淙奔騰的,是它的血脈,給大地輸液,給江河補血。
雪的靈魂遁于無形又無處不在。
雪就將遠(yuǎn)去,我必須送送它。長城外,古道邊,雪地有多遼闊,我送它的心,就有多遼闊……
老天的臉
一夜春雨,不,冬雨。
但已完全是春雨的陣勢,叮叮咚咚吵夜,像發(fā)燒后患上百日咳的孩子;淅淅瀝瀝,淋漓個沒完。總之,我沒有好詞匯,好的詞匯,我留給真正的春雨。
早晨起床,拉開窗簾,見天光放晴,吃驚不小,如吃了興奮劑,頓時提起了精神。
心頭閃過一念,大寒第三日,總覺得哪兒不對勁。想到前兩天在公交車上,一老人說今年還沒有見白,如醍醐灌頂:老天給我們一個笑臉,暫且珍惜。
和睦的友好,笑靨的溫馨,是人與人,也是人與自然,難得的情誼。
等到老天變臉,飛雨,飛霜,飛雪……再懷念它的溫和、燦爛、善解人意,未免不是一種幸福。
飛雨,飛霜,飛雪……包括總是陰沉著,都是它的真面目,老天的臉有時比翻書還快。早已習(xí)慣老天的臉,看不夠老天的臉,愛不盡老天的臉,哪怕它瞬息萬變。
老天大發(fā)雷霆的臉,讓我心里一顫一顫的,但我還是好奇地偷看;老天發(fā)火的樣子,震怒的樣子,就像普通人,甚至像個潑婦,它已完全忘記了它是老天。
矜持、威嚴(yán)、高尚、斯文……統(tǒng)統(tǒng)拋到了一邊。
給一頭老牛讓路
回鄉(xiāng)的土路上,我遇到一頭老牛。我的第一反應(yīng)是準(zhǔn)備給老牛讓路。
不是怕遭遇相持的尷尬,更不是怕老牛用角抵我。我知道,如果我徑直走過去,老牛會很儒雅、很有風(fēng)度的給我讓路,讓我人模人樣地從它身邊通過。
為避免這一幕發(fā)生,我提前讓到路的一邊,干脆下到麥田里,讓出全部的路面。
這是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老牛。從不居功,從不埋怨牢騷,把勞碌草一樣咽下,在夜間千百次反芻,津津有味地活一輩子的老牛。
老了,不能繼續(xù)耕耘時將被宰殺,肉燒鍋子被人下酒,皮做成一雙雙皮鞋在我們腳上锃亮生風(fēng),頭骨掛在墻上坐裝飾成為一門藝術(shù)……
想到這些,我的心微微顫抖……等老牛走過,我再回到路上,在它身后我行了一個長長的注目禮。
不是我有菩薩心腸,不是我有紳士風(fēng)度,也不是我突然良心發(fā)現(xiàn),而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和藉口
不給一頭老牛讓路。
我聞到歲月久窖的芳菲
冬的堅守者,一轉(zhuǎn)眼成為春的代言和形象大使。
扎雪頭巾的香樟,綠發(fā)鉆出來,如心中燃燒的火焰,灼燙著我的目光。
穿雪婚紗的女貞子,多么拉風(fēng)、拉眼球。
系雪圍兜的矮樹,我叫不出她的姓名。
到處都是冷酷的風(fēng)度,到處都美麗動人……季節(jié)的主題充分彰顯。無處不在的T型臺,讓每一個人走秀。
近看不如遠(yuǎn)觀,你的婀娜多姿,咔嚓在我心靈的底片。
這一張,那一張……都各具魅力和神韻。
動輒分享,動輒曬,已成為這個時代浮躁淺薄的通病。我只愛珍藏,當(dāng)一幀昔日的舊照,略顯斑駁和發(fā)黃,我聞到歲月久窖的芳菲
在指尖,在鼻息,拂過,旋舞……
一棵老樹
比較來,比較去,我還是覺得這一棵老樹最值得信任和依賴。
當(dāng)陽光雨潑下,它為我舉起一把綠傘,迎我來,送我往,無怨無悔。傘一直撐在它手里,生怕我不期而至,傘不能及時打開……
風(fēng)中歌唱,雨中也歌唱,只為消解我的落寞。
偶爾放飛一葉,旋舞著單翅,不是鳥,卻有鳥的輕盈,自由落體的弧線,蕩出一道虹……別人無所謂,我在心里一遍遍描繪。
觸地的一剎那,我感覺到振顫和轟鳴,不絕于耳。
在水里,造一葉輕舟,劃過魚兒的頭頂,每一尾魚夢里都蕩漾著彩色的漣漪。
當(dāng)我疲憊的身子倚著老樹的軀干,我的靈魂浪跡在千里之外。倚而不依,依而不倚,一棵老樹在我精神的沃土挺拔。
它早已雄姿不再。西風(fēng)颯颯,每天前來索要我的清淚……不給,就使勁吹,吹翻我的五味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