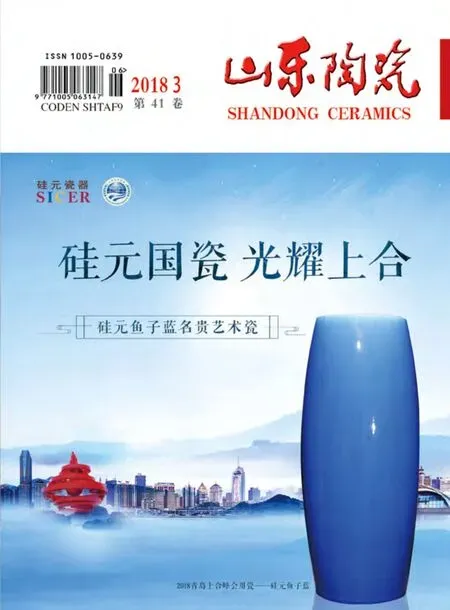淺析“高節瓶”的藝術和裝飾魅力
馮 偉

圖1 高節瓶
從歷史上看,紫砂花瓶的發展一直都是較為冷僻的紫砂陶藝分支,當代紫砂花瓶制作所能借鑒和參考的,多來自于清代宮廷收藏,這些紫砂花瓶占據了絕大多數。而到了當代,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整個紫砂行業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一段發展時期,紫砂花瓶也因此進入了大眾的視野,跟瓷器、青銅器、金銀器花瓶的藝術性達到了同一水平高度,并由此開啟了一段將這些器皿的造型特點結合紫砂材質,融合創新運用的時期。精雕細刻,質樸大方的紫砂花瓶,同紫砂壺一道,成為紫砂藝術行業的一個重要分支。
紫砂花瓶的出現要晚于紫砂壺類,所以它的制作和設計相對于紫砂壺更加的博采眾長,雖然制作上與紫砂壺相似,都是打泥片、打身筒然后鑲接,但由于沒有壺流、壺把以及壺鈕的限制,紫砂花瓶的造型在縱向上可以更加隨意一些。可以說歷史上的陳鳴遠是制作紫砂花瓶的姣姣者,他將紫砂花瓶與其他文房用具囊括進紫砂造型藝術當中,并進行了充分的文化包裝,我們當代所創作的紫砂花瓶基本上由此而來。
圖1“高節瓶”便是以方形身筒為基底,雙柄雙圈耳,高頸圓口,竹節飾,結合字畫的形式創作而成的,這與陳鳴遠充分的賦予紫砂花瓶文化價值可謂一脈相承。瓶身刻道:“喝道前行忽掉頭,風情疑是舊從游。問渠了得三生恨,細雨空齋好說愁……”在瓶的這一面寫情,依照藝術傳統,要在另一面寫景,于是一幅綿綿山水雅居室的圖案便有了,情與景相對正是紫砂花瓶藝術形態和裝飾魅力的體現。
瓶上的陶刻是其主要的裝飾,為的是在紫砂淳樸的質感上求得美感,但是單純的字或者是單純的畫并不符合中國傳統藝術的表達方式,必要字畫相諧,兩者既不能表現出明明白白的關聯,又不可以從頭到尾沒有聯系,要讓兩者之間的聯系朦朦朧朧、隱約可見,從而使作品“高節瓶”具有使人探究的樂趣,從而理解創作者的情感表達意圖,從中吸取人文的審美觀念,獲得藝術上的享受。這件作品中鄭板橋的《贈范縣舊胥》只是表象,真正的情感其實融于畫中。讓人來回品味文字,反復咀嚼,從畫中悟,這就是作品文化裝飾意味之所在了。
從造型上看,“高節瓶”是一個四方鑲接的形態,單看身筒并無法看出“節”味,但結合高頸,瓶底以及雙圈耳的形態,高竹的造型便深深的刻印在腦海里,可以說這件作品本身并沒有塑造成竹節的樣式,但通過上下兩個局部,以及左右雙圈,將竹子的外形總結概括,濃縮到了整體的形態之中,這就造成雖然鑲接時平肩線、圓口都沒有相對細膩的處理,但這種粗而淳的質感,真正的將人的觀賞視線從單純的外形上挪開,從而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瓶上的裝飾,可以說“高節瓶”從形態和裝飾上把握住了輕重主次,充分表現出了本身的藝術和裝飾魅力。
紫砂瓶圓口的潤,以及方身的硬,用上下連貫的曲線完美過渡,通過線條塊面的變化,方中藏圓,將竹子的韻味通過特點的濃縮,實實在在的表達,體現了紫砂傳統的造型美。在這件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到,紫砂陶藝并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將各種藝術以及人文情感等融為一體,每一件作品都有著一條情感和藝術構成的脈絡,沿著這條脈絡,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創作者的創作思路,觀賞的共鳴方式,雖然外在表現是造型和裝飾形象,但內里仍然是情感以及文化價值。我們通常所說提高陶藝作品的意境,實際上是一定程度上提升創作者的文化表達能力,只有提升了文化的表達能力,才能更好的表現出所創作作品的藝術和裝飾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