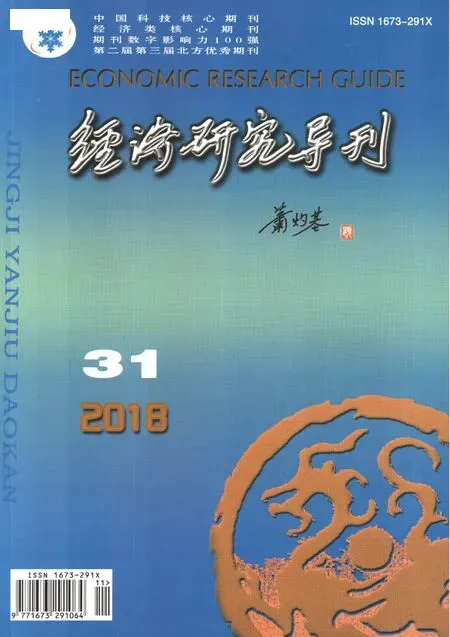要素結構扭曲對開放收益影響的理論分析
鄒全勝
(江西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南昌 330013)
要素是市場生產投入的微觀單位,而要素結構則構成產業結構的基本組織。研究要素結構的動態發展,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索一國產業結構的核心競爭力和開放優勢所在。所以,在市場要素價格扭曲基礎上來分析要素結構對開放收益的影響就成為新開放模式所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要素結構扭曲分析
世界經濟的發展不斷推升各國的開放經濟結構,對生產所投入的高質量要素需求不斷提升。但由于歷史、地理與技術發展的路徑差異,客觀上使得要素分布尤其是高質量要素的分布處于非均衡狀態。要素結構稟賦的逆轉在數量上就要求高質量要素在世界市場流動,從而改變原來固有要素結構。因此,對要素價格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與扭曲,便成為各國尤其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在一定時期內促進經濟發展、提升本國開放收益的重要依賴路徑模式。在發展過程中,以要素結構扭曲所表現的產業發展模式,雖然在一定時期具有對本國經濟發展超強的“刺激效應”,但從長期看,由于要素價格扭曲所帶來的經濟成本問題對本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有滯后影響,從而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中“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使得一國開放收益實質性下降,從而波及一國整體國民經濟福利的下降。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其經濟投入主要表現為初級要素投入的數量型與規模型,其對經濟要素結構性扭曲出現如下特點:第一,表現為外貿和外資政策的“同向激勵”扭曲。表現為外貿中對進出口同向促進鼓勵效果,構成外向型貿易導向的開放經濟模式,外貿依存度提升較高。第二,表現為對外資的差異性制度扭曲,“底線競爭”造成不同地區的制度優惠幅度差異過大,客觀造成國際投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高端位置。同時,國際投資還獲得了投資東道國勞動力成本低、出口匯率低及出口退稅等成本優勢,進一步形成了國際產業鏈競爭中的國際分工優勢。
經濟要素結構性扭曲的結果就是,用扭曲的市場所獲得的資本收益在國內無法形成新的產業模式,而轉而投資外國的貨幣市場,形成貨幣的結構性錯配問題,引發本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客觀上造成與外部市場的不平衡與貿易逆差。
而在要素價格市場形成機制,由于扭曲帶來的結構性差異,也使得要素分布在各地區間不平衡加巨。政府對市場準入、土地、稅收等表現出強力的“有形之手”,短期內偏離了宏觀經濟發展的良性軌道,客觀損害了一國整體國民經濟福利水平。

圖1 要素結構扭曲的埃奇沃斯盒狀圖分析
二、理論分析
首先,假定生產過程投入的經濟要素為靜態屬性,在規范國際經濟學的模型范式基礎上進行經濟要素結構扭曲效應分析。圖1顯示,假定市場存在兩種投入要素:資本要素C和勞動力要素L。資本密集型商品標識為A,勞動密集型商品標識為B,等產量曲線由A、B兩種商品曲線AA曲線與BB曲線標識,兩種商品產出由原點OA(OB)距離到AA(BB)曲線的向量大小標識。AA曲線和BB曲線在點E0處正向相切,兩要素價格在E0處相等。那么,在相切點所處于的OAE0OB的曲線上,可以標識出要素結構配置的有效路徑。短期時間內,如果出現制度、市場或政府干預等原因使得要素價格發生扭曲或偏離的條件下,要素的均衡產出點就會出現在E1點。在E1點,AA曲線和BB曲線將不會出現正相交,而是由AA曲線水平向上位移到A′A′曲線,新的A′A′曲線將與BB曲線相交于E1點。從圖1可以分析得到,對于B商品而言,由于其產出點還在BB曲線上,因此其產量將不變。而對于A商品而言,由于新等產量曲線A′A′<AA,所以在E1點上的A商品產量將小于E0點,從而改變了原來生產可能性曲線,使得生產收益降低。
因此,在假定經濟要素的靜態屬性情況下,從圖2可以看出,經濟要素發生扭曲使得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變化,新生產可能性曲線將自外由內收縮,甚至部分向原點收縮,在原有固化不變經濟要素結構下,生產者的總生產收益下降。①對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內縮,用簡單的生產函數就可以得出。假定生產函數如下:Y*=F(K,L)?y*=(fK/L,1),當扭曲存在使得要素投入減少時,有y<y*,因此生產可能性曲線內縮甚至凸向原點。

圖2 要素扭曲的經濟分析
所以,從經濟要素結構來分析,最重要的是著重于經濟市場內在扭曲的情況。在市場封閉經濟條件下,實現理論分析中帕累托最優的要求是任意兩種市場產品的相對價格等于它們的國內邊際替代率(DRS),同時也等于它們自身的國內邊際轉換率(DRT)。而在開放經濟理論框架下,有且只有國外邊際轉換率(FRT)等于國內邊際轉換率時,所實現的最優化狀態為:FRT=DRS=DRT。但在市場開放體系理論框架下,自由貿易就能保證該條件的實現。因此,任何妨礙該條件實現的擾動因素均可被視為扭曲。當一國所征收關稅的價格扭曲表現為國內價格水平線高于國外價格水平線時,即FRT≠DRT=DRS的條件下,就往往視為貿易扭曲;而當進口產品價格線升高,高效率的國外生產被低效率的國內生產所替代時,即DRT≠DRS=FRT的條件下,則被看作為市場要素扭曲。而消費者剩余的減少,即DRT≠FRT=DRS的情形,則往往視為消費扭曲;當同時符合DRS≠DRT≠FRT的條件時,則可判斷有兩種市場扭曲同時存在的情況。當一國國內市場要素價格扭曲存在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與關稅貿易保護壁壘政策進行組合實施對產業的干預,其政策效果可以發揮最好的作用。但當外國市場存在要素價格扭曲的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則往往不被看著為最優貿易政策。所以,當要素市場存在扭曲情況下,如果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市場是不完全市場,而且存在技術外溢效應時,通過關稅與非關稅的貿易保護措施則可以刺激本國經濟發展,從而借以提高本國的國民福利水平。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一般市場扭曲情況和程度往往不能準確定義和計算,所以在實際貿易保護政策中也就難以精準地實現貿易保護的動態調整措施。因此,通過理論分析說明,貿易保護政策在一定情況下往往并不是糾正市場扭曲的最優措施,具體的實施效果并不很好。所以,應根據不同市場扭曲形成的不同原因,主要從市場經濟要素扭曲的對沖來分析與解決一國開放收益的理論問題。
其次,在經濟要素動態性存在的條件下,以下將基于一個改進的Dixit-Grossman(1982)模型思想來說明在要素結構演進基礎上的不同扭曲分析。
假定市場產品的生產過程由一系列質量連續遞增的要素投入所組成的生產階段,每一個生產階段的收益都有所提高,對要素質量的等級排列進行指數化處理為z,z∈[0,1],初級商品生產階段標識為0,最終商品生產階段標識為1,在各階段中要素成本是線性排列的,即存在一個連續質量排列。假定在世界市場中存在三個國家:國家1、國家2、國家3。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生產階段成本不同,其生產優勢也不同。分別以c1(z)、c2(z)、c3(z)表示生產成本,則每個國家的最終產品的單位成本為在開放的自由貿易條件下,三國的最小化成本為其中,Di(z)標識為貿易保護獲得的扭曲(包括對進口的中間商品所征收關稅成本)。如前假定,生產成本函數ci(z)為一般線性函數,對三個國家的要素結構配置進行如下式求解。


圖3 開放條件下自由貿易均衡

圖4 開放條件下存在扭曲均衡
當市場政策或機制扭曲時。在立足經濟要素結構扭曲的基礎上,其分析的問題將出現如下變化。首先,成本將統一假定為商品進出口的關稅,在扭曲存在的情況。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如圖4所示),一國生產者因為市場扭曲的產生,致使其生產成本相應提升。用生產函數所標識的曲線將發生相應改變,改變后的的生產階段區間將分別移動至因此,開放經濟條件下存在要素結構扭曲效應時,各國的生產成本將會發生相應改變。國家1的投入成本將最大,稍次的國家投入成本為國家2,最后國家投入成本最低的是國家3。世界商品生產的承接路徑將按投入成本的大小,由大至小依次產生,獲取其開放收益的比較競爭優勢。生產改變的趨勢如圖4所示方向,其結果就是:成本低的國家在新的低成本生產區間增加了產量,而高成本國家放棄或降低高成本生產區間的商品生產,退出市場,喪失原有競爭優勢(如圖4各國的生產變化,國家1減少或放棄,國家2和國家3相應增加)。對于一般經濟發展落后國家而言,要達到最低成本國家所獲得的開放收益效果,只需要實行相關的要素扭曲作用就可獲得。而對于經濟發達國家而言,在一段時期出現貿易保護等貿易壁壘帶來的扭曲,同樣可產生如此效應。但如前具體分析說明,在不同市場中扭曲的作用基礎是不同的。
三、結語
因此,在以上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利用利潤函數來進一步說明經濟要素結構扭曲與一國開放收益的相關性問題。現代經濟處于個經濟全球化時代,其市場體系呈現開放性特征,在市場生產中生產者投入經濟要素生產商品或服務,消費者消費而生產者獲利。收益就是生產者在市場收入中除掉投入要素成本、稅費和其他費用后的所余,如利潤函數所表達:R=P1Q-P2Q-M-T。其中,R表示生產者企業所得的收益,P1表示市場中商品或服務的價格,T表示生產者稅務成本,M表示生產者再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費用成本,P2表示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要素的平均價格,Q表示商品的生產量。在利潤函數中,成本決定收益的大小與真實的利潤來源。如上式分析,當P1、M、T不變時,①P1可視為外部市場需求彈性不變,M、T也可視為一段時期的價格剛性。投入要素成本P2就直接對生產的最終收益起到較大的作用。在一個不存在扭曲的完全競爭市場,生產者為了獲得正常收益,其必然選擇的標準是最優的要素性價比,從而達到投入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目的。生產選擇必然是選擇P2最低的投入生產組合,使生產者的生產結構匹配投入要素稟賦特征,并使其具有自主創造能力。而在存在要素結構扭曲的條件下,國家出于對重大產業的保護與扶持的目的,必然驅使生產者選擇的生產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不匹配。由于扭曲的作用,致使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平均價格P2較高的要素。在一個較長期的生產區間,其生產的正常利潤空間必將難以長期獲得,隨著短期優勢的漸漸失去,其競爭優勢就難以維系。因此,在一個開放的市場體系中,投入扭曲要素的生產者往往不具有實現正常收益的競爭力,也就喪失了自主創造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其結果就是被市場淘汰。但在現實經濟中,這些生產者在產業意義上對國家宏觀戰略目標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國家往往會通過“看得見的手”來保護干預,使之具備自主創造能力和壟斷競爭優勢。在利潤函數中,P1和P2通常是由市場供求所決定。由于所保護的重要產業生產者選擇了與要素結構不匹配的生產結構,使得所保護的生產者平均生產成本P2較高,在P1、M、T不變的條件下,其要素投入就不能獲得正常經濟收益。而國家保護這些生產者獲得正常經濟收益的途徑就是通過要素價格的扭曲,利用“看得見的手”來人為降低價格P2。在經濟落后國家,最普通的市場扭曲方法就是對市場農副商品價格的人為壓低,來獲得產業資本的正常收益,也即存在的扭曲的“二元經濟結構”。當然,對于利潤函數而言,國家也會實行一些非市場經濟壁壘和行政手段來提高P1,改變M和T來提升生產成本(如出口退稅、減稅)。貫性做法就是政府利用市場準入標準來控制進入市場企業數量,通過非價格方式來實行數量限制,從而確保重要產業生產者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維系生產者在非市場干預的條件下具有自主創造能力和壟斷優勢。最后,非市場的價格扭曲也包括通常所使用的補貼等形式,來確保與維系生產者在非市場干預的條件下具有自主創造能力和壟斷優勢。但相比較這種方式的作用不如前兩種方式,容易招致外部市場的對等報復。
其結論就是,一國開放發展必須要回歸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本源。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提高競爭提升要素市場化水平和核心要素競爭力來推動經濟發展。所以,要實現一國經濟要素開放收益最大化,就必須引入開放經濟分析框架下經濟要素動態質量觀思想,以要素質量的提升來對沖要素結構扭曲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實現一國經濟在開放條件下的“包容性”與“共享性”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