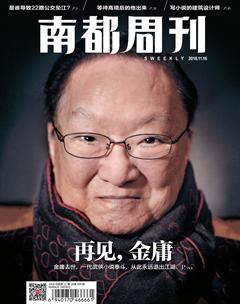保羅·安德魯: 不會寫小說的詩人 不是一名偉大的建筑設計師
河西
建筑界的巨星隕落
法國著名建筑師保羅·安德魯于法國當地時間10月11日去世,享年80歲,是繼羅伯特·文丘里之后,一個月內第二位辭世的建筑大師。
保羅·安德魯是享譽世界的建筑大師,他是中國國家大劇院、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浦東國際機場、巴黎夏爾·戴高樂國際機場等重要建筑的設計師,一生獲獎無數。從1976年獲得建筑學院頒授的魯瓦西-夏爾戴高樂大銀獎,到2006年獲頒國際建筑協會頒發的水晶球終身事業獎,保羅·安德魯的建筑設計備受肯定。
保羅·安德魯生前,記者曾經采訪過他。他的前額基本已經禿頂,后半腦袋上鬈曲的頭發和絡腮胡子一樣灰白,盡管如此,你不會將他和一位古稀老人聯系在一起。他精力充沛,目光堅定,渾身上下透出一股勁,讓你相信,這就是造出中國國家大劇院的那位建筑師。
中國國家大劇院:
“我幾乎都快要崩潰了”
南都周刊: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過程十分漫長,您曾說: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有一次,我幾乎都快要崩潰了”,為什么這么說?和國外的設計競賽相比,中國的設計競賽有何不同?
保羅·安德魯:因為國家大劇院太重要了,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在這么一個敏感的地點建這樣一座建筑,就算建筑師有超強的心理承受力,考慮到畢竟是在中國首都最核心的區域上設計建筑,到底合不合適,需要仔細斟酌。由于它的重要性,來自各方面的建議和批評你都得有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但同時,你不能退步。我有我自己堅持的底線。所以在這兩者永遠是一種悖論。因為你一旦讓步,很可能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永遠生活在矛盾的核心,我需要傾聽他人的意見,但同時我堅持著沒有退縮。這種壓力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因為這里有太多歷史性的建筑,所以我的建筑才變得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旁邊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建筑,或者我沒有建在離開天安門廣場的什么地方,那么我就用不著那么緊張了。因為政治和歷史的原因,建筑的沖突才顯得那么明顯。
南都周刊:您設計國家大劇院時,馬上就想巨大的蛋這樣一種形式嗎?和人民大會堂在一條軸線上,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沒有感受到壓力?您為什么仍然堅持自己的設計方案?
保羅·安德魯:國家大劇院最初的構想并不在現在的位置上,應該是在長安街的邊上。后來,突然,來自總理的命令,說大劇院必須往后退70米,原來能從天安門直接看到大劇院,但現在提出來說不能直接看見。得到這個消息,我快瘋了,我準備退出設計團隊,我不想繼續做下去了。但是我冷靜了下來,既然你們提出不能在天安門看到大劇院,那么我就要求退120米,讓大劇院和人民大會堂在一條軸線上,讓這兩個建筑之間產生一種對話關系,新的建筑好像在對老的建筑說:我和你不一樣。
最初的設想不是這樣,國家大劇院在長安街邊上,現在國家大劇院所在的位置是一個大花園,但這個方案中途被中國高層否決了。我提出了這個新的方案,當時真實的想法其實是:我覺得我這樣的要求不太可能會被中方接受,肯定要被他們否決,但是我沒有辦法,作為一名建筑師,我必須堅持我的想法。
我也沒有和他們大吵大鬧,但是我就提出,既然你們說退70米,那我就要求你們的思維必須再退50米,但是真沒想到,中方高層接受了我的想法,也做了一些讓步。最后的結果皆大歡喜,我和中國當局都沒有丟面子,從最后建筑落成后的效果來看,結果還是不錯的。我沒有爭得什么榮譽,爭得榮譽的是建筑本身,因為它真正地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
南都周刊:我想,如果是一位中國建筑師來擔任設計任務的話,他不會那么大膽,他可能會更多地考慮中國歷史和文脈關系。那么您對城市規劃和建筑單體設計之間的關系怎么看?
保羅·安德魯:我個人覺得我可能比當時的那些中國建筑師更尊重中國歷史和文脈。因為我們設計方案的構思完全考慮到了周邊環境的問題。中國人很明白這一點,建筑和歷史傳統的關系就好像你和你父母、祖父母的關系,中國人很尊重祖先、尊重傳統,但是你永遠也不可能和他們一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你自己,這也是對你父母的尊重。在尊重的前提下,你不見得就是在反叛或較真,你只是很平和地成為你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你才是真正地在與歷史和周邊環境對話。因此,不存在什么“大膽”的問題,我并沒有因為無知所以無畏,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自始至終,整個設計的過程,我都認真考慮歷史問題,從來沒有將其視若無物。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最初設計的國家大劇院方案和最后我們看到的落成的國家大劇院之間差別還是很大的,是什么樣的原因讓您作出這樣的改動?
保羅·安德魯:你應該了解,在中國做設計有很多的限制,比如離開長安街要多少多少米,不能逾越規劃紅線。同時,有太多的人對您說,您要改這個改哪個。現在看來,有些改動是正確的、合適的,但也并不能說所有的都對。
有人跟我說,你應該把什么什么移到什么地方去,我說,你不能將一個建筑像家具一樣挪來挪去,這是建筑,不是家具,這不可能。我服從了一半,同時又堅持了自己的主張,我不知道這樣的做法是否能讓雙方都滿意。
有一段時間,我都準備放棄了,但是最后在對方的誠意下,我堅持了下來。當然,我也做了一些讓步。很明顯,雙方的觀念和想法都有一些差異,這是建筑設計中甲方和乙方之間常常會出現的問題,幸好,我們處理得還不錯。
順便說一句,我很自豪地說,我們在創造未來的傳統。
機場專業戶與詩人建筑師
南都周刊:柯布西埃說:“房子是居住的機器”,你同意他的觀點嗎?
保羅·安德魯:當時我建戴高樂機場的時候,我也套用柯布西埃的說法說“機場是停泊的機器”,一定要把它作為一個機器來設計。但是很快我就改變了我的說法,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像個心臟。心臟比機器更復雜,不能純粹從一個機器的角度來看機場,很快我就越來越明白,不能從純科學的角度來看待空間,它還有人文的一面,你可以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待建筑和空間,這是我們現在特別需要考慮的問題。
南都周刊:除了戴高樂機場,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機場、阿聯酋阿布扎比國際機場、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機場、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文萊機場、中國三亞機場都出自您手,為什么對機場設計情有獨鐘?和您早期在巴黎機場公司工作有沒有關系?
保羅·安德魯:我在機場公司工作就是設計戴高樂機場,從那之后我就愛上了這個行業。為什么呢?機場——尤其在當時——是個全新的建筑樣式,古典時代是沒有機場可言的,意識到機場設計的重要性也是近期的事,它的歷史很短,所以你沒有太多的技術和文化參照,更多的需要你的想像力來發揮作用。確實,機場這片天地給了我施展抱負和才華的空間。我設計了許多大型的機場,這樣大型的機場在當時并不多見,對我來說,這是全新的體驗。
南都周刊:法國戴高樂機場1號候機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里,游客可經由交叉玻璃通道穿過中廳,這樣設計是否可以大大提高通行人流?
保羅·安德魯:你這個細節提得很好。設計一開始肯定是功能性的,就像個機器一樣,我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希望機場的乘客不要走彎路、機場內部也不要出現人流擁堵的情況。我就是希望能夠增強流通性。但是一旦設計好之后,我就發現,這樣設計不僅有功能性的一面,還有詩性的一面。它本身就象征著旅行,象征著飛行,于是,乘客在坐飛機的過程,他就會體會到某種詩性的隱喻。就在那一剎那,我突然領悟了設計的奧秘:如何以一種詩性的方式來做設計,去利用空間。
南都周刊:您是不是從那時開始成為一名詩人建筑師的呢?
保羅·安德魯:可以這么說,但是并不是說我帶著一種詩人的姿態就可以成為詩人建筑師的。在設計過程中,我們總是會遇到許多未知,有許多新的發現和新的創意,在設計的過程中你總能遇到許多很美妙的東西,或者是對生活新的認識,這些是我感興趣的,這才是真正的詩意。就像薩特的《惡心》中所寫到的,一塊丑陋的石頭,你翻過來時,它可能就會發現它美麗的一面。在不斷的未知與發現過程中,我們才有新的可能,我要強調的是這一點。
在我的建筑生涯中,我從來不對人說這空間是多美多詩意,尤其是那些請我來做設計的人,我會對他們說:“你看,這功能多好。”而美不美,我希望他們自己發現。當然,美非常重要。如果有人問我在設計過程中什么重要?我會對他說,預算、功能性都很重要,但是美也很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南都周刊:我們了解的你的作品大都是像國家大劇院這樣的大型公共建筑,我不知道您有沒有設計過私人住宅?庫哈斯認為都市其實是由機場來連接的,你怎么看庫哈斯的觀點?
保羅·安德魯:我覺得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關系是兩者缺一不可。從城市本身的概念來說,城市本身就存在兩種概念,一它是停留的場所,一個是流動的中轉站,沒有這雙重屬性就不會構成城市。我經常想到一幅畫,畫的內容是關于十七世紀的威尼斯的,那幅畫我印象特別深刻。那幅畫非常漂亮,畫工精湛,但是我覺得它既是威尼斯,又非威尼斯。為什么呢?那幅畫把威尼斯最美的建筑都放一塊了,它把它們集中在了一幅畫之中。
這一發現讓我對城市和空間有了新的認識。我覺得,如果讓這幅畫夢想成真的話我相信那會是一場災難。把地標性的建筑都放在一塊,它其實就不成其為一個城市,我說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地獄,很可怕了。城市當然也需要簡簡單單休息的空間,所以真正的城市需要優秀的私人住宅設計的調劑,不能光是高大光鮮的地標建筑。我的立場是兩者需要共存。如果只有所謂“大而美”的建筑存在,那么這地方我相信一定是在新興的郊區里才能看到,但那是沒有歷史和文化積淀的建筑和城市。
南都周刊:在您的設計中,什么是您最滿意的?有什么遺憾嗎?
保羅·安德魯:我對我的設計不會有100%的滿意,我想如果一個設計師有這樣的滿意設計,他大概很快就會因苦惱而喪失斗志,因為他將難以逾越這座高峰。
我常常對我的年輕學生說,你們有能力去做的事,是和你們對自己的懷疑是成正比的。我們總是生活在懷疑之中,對自己能力的懷疑,對自己作品的懷疑,乃至對人生的懷疑,懷疑總是像霧氣一樣包圍著我們,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它的俘虜。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做些什么,我們生來如此。
懷疑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它能讓您對自己喪失信心,讓您望洋興嘆,讓您感到自己的卑微與渺小,這就是懷疑,它能讓您無力去征服自己。
寫小說的建筑師
南都周刊:您也寫小說,出版了小說《記憶的群島》和《房子》,作為一位著名的建筑師,建筑師的身份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何影響?或者反過來說,文學素養是否也有助于您的建筑設計?
安德魯: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在做建筑師的時候,我就是個建筑師;而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就是個小說家。從原則上來說,一個人的興趣愛好對他來說都應該是互相滋潤的,互相帶來養分的。但當然,每一種創作都有其獨立性和特殊性。我覺得,一個好的建筑家應該向一切藝術——繪畫、文學、電影、音樂、舞蹈——學習,建筑的靈感可以來自于這些藝術,可是在具體設計的時候,又要尊重建筑本身的獨特性。寫小說也是一樣,建筑也可以成為文學家的養分,但是寫小說就是寫小說。
南都周刊:寫作和設計對您來說又有什么不同?
保羅·安德魯:建筑是很多人、一個團隊在一起合作,寫作是孤獨的。一個人寫作的時候是很享受的,和我的團隊合作又很溫馨。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設計上,寫作最多也就是十年的時間,所以說我是個很有經驗的設計師,但是一個寫作的新手。
南都周刊:您本人又是如何理解空間的?您小說中的房子更多的是一種內心印象的投射?
保羅·安德魯: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我本身是學建筑工程出身的,所以首先會從物理學的角度來審視空間,這是現實的空間,但同時,它又與我們主觀的投射不可分割。
現代物理學的空間概念非常復雜,很難分析。我覺得在客觀和主觀的空間之間具有一種延續性。你在具體的建筑設計過程中,你肯定會有一些主觀地對空間的認識,而在寫小說的時候,好像完全主觀,其實我們還是會受到科學的物理空間的約束,這問題我們其實無法將其完全割裂開來。兩者之間一定是有關聯的。
南都周刊:順著這個話題我們再來談談空間,您的小說《記憶的群島》和《房子》中的空間是封閉的,而且小說里多處寫到墻,作為一個建筑師,您是怎樣考慮這樣一種封閉空間的?
保羅·安德魯: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作為一個建筑師,我天天在做建筑,我不可能忘掉自己的建筑師身份,也許是下意識地,我會想起這些建筑的細節并把它們寫進了小說。所以你看我的小說里有很多天花板啊、地面啊、墻啊,還有我對環境景物的描寫,比如雨水啊、水的流動啊,那也可以視作是在為建筑設計它的環境,文學當然也可以視作是我建筑設計的一種延伸,但我還是覺得寫作過程——詞語在紙上的排列和設計過程是兩種不同的構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