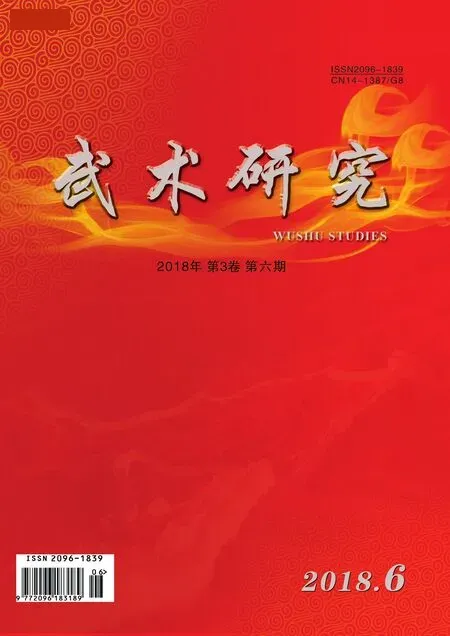社會需要與認同:日本醫療康復領域引入太極拳的歸因研究
劉 聰
四川護理職業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0
太極拳文化由社會的人而創造,被社會所需要與認可,故其在本質上必定受諸多社會文化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等的影響,而這些因素都可以從整個社會系統中去逐一厘清。本研究將參與太極拳文化中的諸多因素視作一個主體,通過這一整體在社會系統中與社會產生的互動過程,去解釋社會對太極拳的需要與認同;并結合實地訪談個案進行淺層與深層的雙向分析,去揭示太極拳在日本醫療康復機構中被社會群眾所需要與認同的歸因,以及太極拳在此類社會環境中被利用而產生出的價值與功能。
1 社會需要:受眾接受太極拳的社會誘因
“所謂需要,是指個體在社會生活中感到某種欠缺而力求獲得滿足的一種內心狀態。”[1]社會個體乃至社會的生存發展初衷皆是為滿足其需要,社會個體一般滿足的是自身生存之需、精神之需,而社會發展需要滿足的是社會文化需求、精神價值需求等。然而根據社會個體的發展狀態又可以將其需要分為三個層次,即:物質生理需求、社會心理需求、價值意義需求,這三個需求層次呈依次遞進關系。同時,這也客觀反映出一個社會的需求,因為個體從屬于社會,個體的需求反襯出社會需求,而社會的需求囊括了眾多個體的需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眾多社會個體的需求可以代表社會的需求。以日本天草慈惠病院為例,其是當地社會中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場域,一個具有鮮明日本社會文化特色的集中地,一個在日本文化、地域、社會環境下生存的社會群體,將中國太極拳如獲珍寶似的引入并推廣,究其原因又是為何?從以上我們對需求的認識中,就可總結而歸之為“需要”二字。故研究太極拳在日本這一社會文化特色場域中的生存與發展,理應將關注點放在它是如何滿足當地社會個體與社會系統的需求方面,通過運用社會學中功能的分析方法,窺視太極拳在日本當地醫療康復領域發揮的顯功能與潛功能等,以此窺探太極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體育項目而被日本當地民眾接受的原因何在?
1.1 顯功能:社會資本的利己性需求
在社會中,顯與潛乃對立相依的兩個存在面,從語義上可知:顯而易見之為“顯”,深藏不露之為“潛”,即易被發現與窺見的與不易被察覺與掌握的兩個含義。“功能”從個體出發可以理解為某事對個體產生的有利作用,從社會意義來看則可以理解為某項社會事物在社會中產生的有效作用,故無論是有利作用還是有效作用,都足以證明“功能”二字歸根究底是形容一項事物發展的褒義詞。在“功能”二字前冠以“顯與潛”,旨在區分功能的兩個層次,即可眼見為實的“顯功能”與需刨根究底方可知的“潛功能”。在社會學中,顯功能是易被大眾所窺見的,且是在人們帶有強烈目的性的行為動機下所產生的利用性效能;潛功能則正好相反,是在人們潛意識性的行為規律中產生的自然性功能。如林中之木為人所用可造紙,可為工藝品,此為木為人所用后的顯功能,而木本就具有凈化空氣之自然屬性的潛功能。
同樣,相對也不同區域社會主體來說:主體的需要構成了其社會行為方法與模式,其參與社會行為的過程產生了一定的效應,滿足需要是行為產生的初衷,獲得成效是行為產生的目的,而成效的獲得是社會主體在參與社會行為過程中通過某種手段或者行為方式后作用的結果。太極拳是一種體育鍛煉手段,更是一種特殊的身體行為方式,它所具有的任何功能也必須是在社會主體將其帶入并參與社會行為后才可以顯現出來,所以太極拳功能的發揮離不開社會主體的需求。在中國,太極拳是一種行為文化,也是一種文化資本[2],細微處可觀其健身強體之功效,粗略出可見其中國傳統文化之本,于大于小都是受人們之所需而產生的產物。
而與此相對,在針日本醫療康復領域調查中發現,一個社會安定、經濟發達、文化開放的國家,雖然具備基本生活保障、文化教育、社會養老福利等各種健全的社會制度,卻仍然存在著不能避免的社會問題即嚴峻的“社會老齡論”[3]問題。通過大量調查分析發現,在日本參與職工課程的太極拳交流活動的年老者占90%以上(50歲以上),參與病院太極拳交流活動的對象年老者為99%(其中1%為病院看護者),參與養老院太極拳交流活動的對象年齡最小的也有59歲,最年長的甚至有108歲。這樣一個社會現狀,恰好與日本當下老齡化社會的基本國情相互映襯,在這樣一個老齡者居多的社會,社會的需求自然應適合于老齡者,而太極拳這樣一種柔韌綿緩的身體鍛煉方式,無疑會成為老齡者傾心喜愛的對象,也固然會成為太極拳快速融入其社會主體的因素。
1.2 潛功能:社會心理的互動性需求
潛功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一種無形的較為抽象的功能,恰如空氣一般,不具實物形態,須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被發現。參與社會的主體屬于客觀存在的實體,而社會主體在參與過程中的心理過程則屬于潛在的不易被觀察到的。因此,太極拳之于人的機體而言,僅僅是一項身體技能,而之于人的思維意識而言,卻是一種身體文化,這就是太極拳文化的魅力所在。從具體客觀形態的功能上,太極拳可以強健體魄、鍛煉身體;從心理抽象層面的功能上,太極拳可以磨練意志、培養性情;從整體身心需求角度觀之,太極拳不僅可以滿足主體的生理需求,還滿足了其更高層次的心理需求。前面提到過,眾多社會個體的需求構成了一個社會群體的共同需求,人之所以形成群體,乃至社會,皆源于“人的社會性”[4],即:人需要在參與社會的過程中定位自我。
人的社會性決定社會個體在社會中對集體關系的依賴,而依賴的前提是需要,它產生于社會個體為滿足自我身心需求的過程中,形成于社會個體構建社會需求關系的互動過程中。在針對天草慈惠病院太極拳交流對象的問卷訪談中:“あなたは太極拳が日本で普及の期待程度?(您對太極拳在日本推廣的期望如何?)”,在這一問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當地民眾(包括病院職工、養老者、病人)對太極拳的渴求程度和太極拳在日推廣的期望程度是非常高的,約占90%的人都表達出非常渴望的意愿。這也說明在參與太極拳交流活動中的這一部分社會群體的需求與心理是趨于相似的,也正是這種統一性的需求心理使太極拳在當地備受歡迎與喜愛。在后來的觀察中發現,這種趨于一致性的群體需求心理,是源于這些太極拳受眾者在交流過程中相互之間關系的維系。實際上,通過觀察發現,在太極拳交流的職工課堂中,來參與的人當中也分為了幾個團體,而這樣的團體多是以家庭為紐帶形成的,在之后還出現了一個家庭帶動另一個家庭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又是以純粹的社交關系為媒介形成的。這也就是說,在他們參與太極拳這類文化交流活動的過程中,他們出于對自我社會角色的認同心理,對所在家庭關系的維系心理,乃至對周邊社會關系的穩定心理,都可以在這個以太極拳文化為中心的場域中得以滿足與實現。
1.3 社會功能:太極拳醫療康復價值的可利用性
何謂功能?功能(Function)從語義上可以譯為:事物或方法所發揮的有利作用[5];它是某項事物或某種方法利用其自身所具備的客觀屬性,所產生的作用與價值。在社會學理論中,對功能具有導向性的是社會結構,也就是社會系統,對功能具有證明性的是價值實現,也就是功能產生的作用。因此,社會結構、功能、價值三者的關系可以理解為相互影響的聯系,功能的實現仰賴于社會結構的構成元素,功能的發揮結果依賴于最終價值的實現程度。功能的分析方法就明確表達出:社會現象滿足社會系統的過程,就是其產生功能的過程;即某項事物或者方法在某個社會系統中發揮其作用與功能的過程,就是它在實現價值的過程,并以此來證明其存在于社會系統的社會意義。太極拳是一項特殊的身體鍛煉方法,太極拳文化是一項存在于社會系統中的社會事實,兼具這雙重社會身份的它,其存在于不同社會系統中的價值與意義又應當如何去理解?
隨社會文化與社會需求的變遷,如今的太極拳已將其技擊實戰屬性逐漸轉變成為強身健體的客觀屬性。現如今,無論是在理論研究層次的學術研究界,還是技術鉆研過程中的的“武術界”,對太極拳的研究與運用皆已將重心放在技擊屬性之外的健身屬性上,如此一來,當今太極拳受眾人青睞的屬性非強身健體莫屬。強身健體是太極拳的客觀屬性,同樣也是社會大眾的共同需要,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太極拳成為社會大眾的特殊需要的呢?首先,人有性別、年齡之分,更有興趣愛好之異,還受到不同社會環境的限制,而太極拳卻是可以同時滿足這些特殊性需求的對象;其次,太極拳的功能除卻早期的技擊實戰和現在的強身健體之外,同樣還具備娛樂、表演、教育、修養心性等大眾性功能;因此太極拳之于社會的功能可謂不可或缺。
2 社會認同:社會影響力下的價值共性
認同(Identification),一個心理學范圍內的名詞,意指個體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肯定,就詞義來理解,認同是一種個體心理上對他人或者自己身份、角色、地位的獲取認可,是個體通過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獲得的結果。文化認同是群體心理作用下產生的一種集體意識認同,是一種由群體主宰并影響個體的意識認同,是群體通過社會整合的影響過程獲得的結果。社會認同是個體或群體對自我身份、地位、屬性、價值等特性的認知過程,是人被社會化的過程,是社會通過價值判定的模式與過程形成的結果。首先,就認同、文化認同、社會認同三者而言,都涉及到人與社會之間的角色問題,且角色的判定實際上是一類社會心理判定模式;其次,三者的結果獲得都屬于社會運行機制內的活動,在這一機制內所遵循的狀態與規范是社會系統制定的;再次,其過程皆屬于動態進行的,是無限循環、無終點的一個過程;因此,認同在社會的范疇內,根據其獲得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我認同、社會認同、價值認同。
2.1 自我認同:社會互動中太極拳的角色扮演
在社會學范疇內,自我認同是指獨立存在于社會系統中的社會個體或者社會事項對自身所處社會環境下的角色定位,也是社會個體或者社會事項在不同社會背景下自我身份的判定。俗語有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需求是構成認同的基礎,社會個體間的相互需求構成了以需求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通過類似社會關系的互動,個體之間給他者包括自身在內的這段關系當中,對他人及自己進行了一種默認角色的心理定位。依此種規律類推,我們就會發現:自我認同的產生實際上就是社會主體或社會事物在處理自身與他者之間社會關系的過程,也就是自我內部與社會外部發生關系的過程,并且通過這個過程給自身及他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進行定義。太極拳文化構成要素中的太極拳與習拳者作為相互獨立存在的社會個體、社會事項,他們各自在不同社會環境下的自我認同過程,也就是他們在探尋自身社會角色扮演與定位的過程。
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將“自我認同”定義為:“某種經由社會習得而在個體自身內形成的東西” 。[6]在社會群體的實踐過程中,自我認同理解為個體身處社會總體環境之后,與社會中的他者發生聯系,并將自我與他者共同轉化為客體的過程形成了太極拳,在太極拳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過程中,產生了太極拳文化,可見太極拳文化的自我認同離不開社會,社會猶如一面鏡子,太極拳文化可以無時不刻的從中窺視自我并衡量自我。太極拳文化的自我認同,主要包含太極拳本體的自我認同與參與太極拳個體的自我認同,一方面,太極拳本體的自我認同是在滿足社會對其的社會需求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太極拳參與主體的自我認同是社會關系互動過程中對其所扮演角色的表現認同。暫且將其劃分為本體認同與主體認同,二者的自我認同直接與社會群體的影響密切相關,對他們自身的扮演角色起著指導性作用,是判定其角色認同的直接因素。
2.2 社會認同:不同社會環境中太極拳的跨界運用
如果第一階段自我認同賦予太極拳在社會互動中的扮演重要角色時,那么處于第二階段的社會認同,是自我認同的更高層次,也是處于三個認同階段的中間位置,它所起到的作用離不開承上啟下的固定模式。如果說自我認同是來自于社會個體或社會事項對自我身份角色的定義過程,那么社會認同則強調的是整個社會群體對社會個體或社會事項的一個認識并定義的過程,相當于是個體之于自我,群體之于個體的區別;而太極拳在中國早已成為一項被社會群體用以展現自我來獲得社會認同的身體文化。根據心理學理論,社會主體的行為皆出自于心理動機的引導,行為產生的本質就是主體心理認同的結果,換句話說,“社會主體的每一個身體行為都是在以認同的心理來表達自我意識與社會意識的同步。”[7]因此,社會群體對太極拳的接納行為,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以一種集體意識的方式對太極拳表達的社會認同;太極拳的健康思維模式是社會大眾所堅持追求的一種生活品質,更是一種對生命珍惜的執著態度。
在國內,太極拳在眾多社會群體的意識里是治未病、防老健身、老年人專屬運動,卻很少有某一社會機構對太極拳的針對性運用或者推廣。中國的社會文化是包容的,可以包羅萬象,容納各異,但正是這樣的包容凸顯了日本文化的精細,因為太極拳在中國的運用與推廣大部分時候是處于一種小眾認同意識形態里,就像武術的各門各派一樣自成一家,各成一系,始終封閉在一個滿足自我認同的驅殼里,與社會文化的共同認同脫離。而在日本的社會文化里,一旦一種文化信仰、新鮮事物得到認可,就會面臨精微細致的認真對待,就好比如太極拳,它可以將其置身于天草慈惠病院這個微型社會環境下,將它的防病、健身、養生、娛樂等眾多功能集于一處,針對每一個受眾群體來區分應用,以達到在這個微型社會系統內部,太極拳受眾心理的趨于一致化,太極拳參與群體認同的集體化效果。
2.3 價值認同:太極拳醫療康復價值的社會效應
一種文化的的生存和構成形態大體包含了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種,而這四種形態是文化與社會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實際上,文化之所以能夠產生并延續生存,它所仰賴的就是與社會產生互動的過程,其實這也是一種尋求自身文化定位與文化認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之于社會所產生的作用、功能就決定了這一類文化所存在于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而最終社會將互動信息反饋給文化的唯一途徑就是價值認同。正如太極拳是屬于一種“現代的傳統”[8]文化,即身處于現代社會結構中的傳統文化,它自身的文化涵蓋了眾多能夠使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價值,物化層的太極拳就是一種身體習得性技能,而精神層面的太極拳卻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語花,因此,作為一種完整形態的文化,太極拳需要現代社會給予它價值認同。太極拳作為引進交流項目的過程中曾遭遇過瓶頸階段,其根本原因就是早期時候對太極拳的引進和運用只是停留在較淺層面“術”階段,所以在選拔太極拳指導員上選用了沒有任何理論基礎知識的“外行人”[9],致使早期的太極拳交流項目停滯不前,不被當地人認可;因為當地太極拳習練者對太極拳的渴求程度并不僅僅停留在基本的“技術”學習上,他們更想知道的是為什么太極拳能夠使他們感覺身心受益,為什么太極拳只能夠在中國被創造?
3 結語
太極拳之于文化,應當歸屬于身體化形態一類的文化資本,它以一種身體形態的文化形式在社會系統中產生,以一種身體感悟的傳承方式在代際聯系中發展,以一種身體文化的傳播途徑在社會互動中發揮其功能。在日本當地社會大眾對太極拳接納與認可的過程當中,無形之間通過行為與意識結合的認同方式,對太極拳的價值給予了認同。而以天草慈惠病院為代表的日本醫療康復領域,在對太極拳項目的引入運用過程中,正所謂“物盡其用”,其初衷是對太極拳這一類文化資本的價值利用,實際上更是對太極拳文化資本的功能發掘;也正如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10]這一概念中,將文化和與文化相關的一切統稱為文化資本,并根據文化及其產物所具備的功能特性將其劃分為“身體化形態、客觀形態、制度形態”[11]三大類,其中身體文化形態則成為文化之于身體外所產生的功能作用所類文化資本,而更好的傳播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