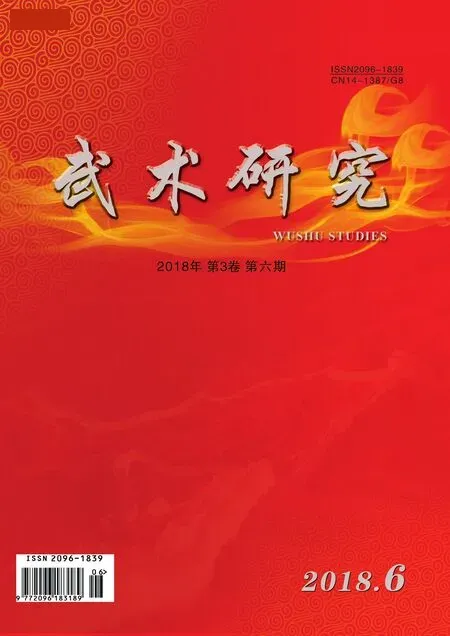淺議馬氏通備武學教育理念
史永琴 佘麗容
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馬氏通備武學是由近代著名愛國人士,著名武術家馬鳳圖先生經繼承與凝煉發展而出的傳統武術實踐與理論體系。后經由馬氏一門的弟子及其子嗣所繼承與發展,廣泛傳播于我國西北、華北、東北、華南一帶,特別是各大高校與學術團體之間,在海外也有廣泛傳播,具有傳承嚴謹,學統嚴密,學術性強等特質,與民間武術普遍流俗于民間的基本狀態之間形成鮮明對比。
目前學術界對馬氏通備的相關研究從總體上來說還是較為欠缺的,對人物、技術源流的研究較多,對技術問題的相對較少,從教育層面來進行闡述的目前尚未出現。馬氏通備武學在整個武術的發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對馬氏通備的研究不能簡單的從武術流派來看,在教育領域中也具有重要影響。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已為各方所公認。但如何而能良好,而能滿意,則非先有良好模范與榜樣作用。[1]本研究將對馬氏通備武學和馬氏通備武學教育理念進行闡述,充分論證馬氏通備教育的合理性。
1 馬氏通備武學概述
馬氏通備經歷了由通臂、通背至通備的過程。有學者認為“通臂”出現的很早,“通備”出現的較晚,通備是從通臂中衍化而來,或者是同音訛傳,當代人往往混通使用。根據清末滄州地區李云標、黃林彪等先賢的傳授,曾經是“外稱通臂而內稱通備”。通臂取其形,通備取其義;也可說前者是具象的、技術層面的,后者則是抽象的,是義理層面的。[2]從字義上講,“通背”是“通臂”的衍化或同音訛傳,“通備”是“通背”的引升和升華。1909年天津中華武士會成立時,為區分“通備”與“通臂”,經馬鳳圖與師友商議,正式提出“通備”稱號。
馬明達教授在《顏李學派與武術》中,主要探討了顏李學派學術思想與通備武術精神的淵源。顏李學派的創始者們不只是倡導文武并重的理論家,而且是躬身履行的實踐家,研習和傳播武術,以武術為健身修性之道,是顏李學派一個顯著特點。顏李學派對武術的積極提倡和躬身傳習,通過他本人和他的弟子們,一定會有流風余韻散存民間,特別是在武風素盛的河北省。約道、咸之間,一位曾任河北省鹽山縣教諭的潘文學其人,也曾在鹽山縣書院分文武兩科教授學生,清末著名武術家李云標、肖和成等人,就是書院武科的學生。這位潘文學,倡言“通神達化,備萬貫一;理象會通,體用具備”之說,以“通備”二字為拳派命名,其精神或直接源自顏李,或受到過顏李的影響,反映了顏李的武術確有遺教存世。[3]顏元所強調的“習行”的教學法,在思想淵源上,受到孔子“時習”思想的影響,但是“習行”內涵比“時習”的內涵更加豐富、深刻。[4]
馬圖先生堅持“融通兼備”的武術思想,對通背拳不斷加以宏廓和熔鑄,從而在理論與技術上形成了一個綜合性質的完整體系,這就是“通備武藝體系”,或稱為“通備武學”。這個體系繼承了明清以來的許多古典兵器技法的精粹,融合長拳(不是現在官方頒布的所謂“長拳”)與短打兩類拳法為一體,創造出以“剛柔相濟、長短兼備”為理論指導的“通備勁”,形成“氣勢雄峻,身法矯健,勁力通透,打手洗練”的通備拳風格。[5]馬明達教授認為:“通備不是一個拳種,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門派,而是一個武術類別,一個內容宏博、結構嚴整的武術體系,也可以說是一個汲取各家之長加以整合熔鑄后形成的綜合性的武學體系。”
有學者對馬氏通備的發展做了簡要概況:“馬氏通備武學體系的構建,經歷了清末民初的創立階段,二十世紀中葉的發展階段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末的提高階段。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創立、發展、提高使馬氏通備武學成就為當今中國武術天地中一個獨步武林,理論體系完整,內容宏博,立意、立象高雅別致,備受世人推崇的武壇顯學。”[6]
2 馬氏通備武學教育理念
2.1 文通武備的教育理念
馬氏通備在教育上強調文通武備,在教育的上層建構中深受顏李學派的影響。馬鳳圖先生認為:“不能把武術簡單地劃撥到“武”的一邊,因為武術里面有“文”的成分。武術理論和技藝都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有豐富的文化背景,它包含和積貯了多種文化成分,包括了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信息,顯然,解讀這些歷史信息具有很高的學術意義,但它又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所以,從本質上講,可以把武術當成是一門文武兼備的“武學”,不同通文就不能真正通武。 強調習練者一定要重視學術素養,須努力借助古典武藝典籍來探討古今武藝的傳承淵源和嬗變軌跡,只有如此,才能抓住武學正脈,循序漸進,直逼壺奧!同時也不被社會上各種流行武術斑駁迷離的表象所迷蒙。不讀書或少讀書的拳家,朝夕苦練可得一技之長,但是總難悟解武學真諦。現在很多人使“廢書不觀,游談無根”,終究是一介武夫,有的甚至連“武夫”都做不到,只會幾路花拳繡腿而已,馬氏通備一貫強調武術是一門“實學”,不是光靠讀書就能掌握得了的,其精蘊所在,特別是古典武藝成分較多的器械,非經名師指點又苦心操練則不能得心應手,不能明白其中的‘玄機’。”[7]
杜威先生說:理論和實際、思想和實行兩相分離,這是從前的人所深信的。[8]例如:重術輕學的現象,這是武術界長期存在的,輕視理論研究,許多重要問題懸而未決,或人云亦云,無所適從;或斷章取義,強作解說;甚而依靠神秘主義以自壯聲色,把拳學引向玄學。相比起來,自身理論體系相對嚴謹的馬氏通備這方面要好很多。文明的高級發展階段,人們過于追求以藝術為核心的高級文明,會導致個體的身體衰敗以及精神軟弱和精神殘疾,即我們所謂的“文弱的文明人”。當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的身體和思維不僅不會隨著文明的發展而發展,反而會隨著文明的發展而身體越孱弱,精神越萎靡。文通武備是既要發展術科,又要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讓習武者在文武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習練馬氏通備既可強身健體,又可增加個人的幸福感,并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防身自衛、保家衛國。文通武備不僅可以讓人學會用文明的方式解決沖突,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用武力解決問題。入通備之門,就要學以求道,學以致用,不然則是徒有其名而已。通備絕不只是拳打腳踢、玩槍弄棒的技藝,這正是以往大批通備追隨者終究走向泯沒無聞之路的重要原因,深刻教訓,不能不總結。
胡適先生曾說:書是過去已經知道的智識學問和經驗的一種記錄,我們讀書便是要接受這人類的遺產。[9]馬氏通備武學在知識結構中不斷強調“文通武備”不單單是要成為學者型的武學家,更要入世濟世,要形性統一,而踐形盡性。馬鳳圖先生聯語“勢通百節招通膽,氣潤三焦德潤身”也正是形容這一精神。通備武藝也一向將健身強體與修身養性并舉,使練習者不但能強身健體,更會受到文化的熏陶,身心都能夠得到有益的發展。為此,要求每個通備學人需要在術與學兩個方面都獲得相應的發展。
2.2 習動教育理念
習動教育即強調以動為主、以剛克柔、以快打慢、千金打四兩的技戰術思想。主要目標是培育勇猛果敢、剛毅堅卓的男子氣概,習動教育理念的衰退必導致“男子漢”消失。尤其是科技文明以滿足人的好逸惡勞的本性為目標,而好逸惡勞的欲望一旦獲得比較完整的滿足,人的身體與精神就會逐漸退化,冷兵器時代如此,熱兵器時代同樣如此。[10]男子氣概既是關乎人的身體力量,更是崇尚“內心強大”的人格力量。人在競爭中常以智慧或體力取勝,但是在智慧與體力大致相當的前提下,狹路相逢,勇者勝。習動教育在亂世盛行,但是在太平世主要追求智育、美育、情感教育,往往會忽視習動教育。
馬氏通備武學作為一個系統,有自己所講究的“勁道”。“通備勁”包括了開合、吞吐、起伏、擰轉四個具體的勁法。“通備勁”一定是指四種勁力的整合表達,并非其中一種或兩種勁力的偶而顯露,也就是說,“通備勁”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系統,不是或見于此或見于彼的一時一勢之力。[11]“通備勁”是“融通兼備”理念的產物,是多種勁力風格的綜合與提純,也是“通備風格”在練與打兩個方面的集中體現。從具體的技術源淵講,“通備勁”是以劈掛拳的“勁道”為主體,充分吸納八極、翻子、戳腳等門派的勁力特點后發展起來的一種力量運行規律,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的武術風格。“通備勁”是將多種拳械武藝融合為一體的基礎,在馬氏通備體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凝聚作用。習慣上,會使用十二打手來進行初期教學,一是解決最基本的橫平豎直的問題,二則是在學習之處找到對“ 通備勁”的明確感覺。“通備勁”既是基礎,也是最高層次的東西。
馬明達教授在教學過程中常提到戚繼光的“拳經捷要篇”[12],強調“拳打不知、千金打四兩、以快制慢、以剛制柔”的戰術思想,在訓練中通過磕磕碰碰來強化擊打和抗擊打能力,以及手、眼、身、步的協調。與此同時,在素質訓練中,尤其注重力量訓練,充分調動各種傳統訓練手段,增強力量,特別是強化膂力。在平常的訓練中將彼我雙方置之于瞬息萬變的境域之中,快是法則,是前提,至于快的靈活掌握和巧妙運用則是戰術和手段,這里面也頗多機巧,須悉心探研,以達“輕快巧捷”“快慢并用”之境。正因為擁有絕對快的實力,于是才可以創造亦快亦慢、或快或慢的變化,也會出現從容相向、以慢制敵的妙趣。以慢制勝是偶爾的,而且必是在快的前提下從心所欲,偶一用之,但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不是時時事事都可以得到的效果。晚近以來,養生拳家往往以“內家”自詡,專講以慢制敵,將偶獲成功的例證鋪陳夸大為具有普遍價值的法則,以至于很多人沉湎于“已慢制快”的技術追求中,出現了中國武術史上不小的理論誤區。
馬氏通備武學是實學,不是奇談怪論,切不可幻想什么神妙的絕招,侈談什么以慢制快、以柔克剛之類的玄虛的高論,馬氏通備武學就是追求最樸實、最普通的道理,堅持以快制勝、以狠打慫、以剛強挫柔弱、以勇敢斗怯懦、以苦學苦練和勇于實踐,掌握最普通最常見最實用的克敵制勝手段。
2.3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就是因材施教,不同的人即使問相同問題孔子也會根據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回答。[13]馬氏通備武學在教學中采用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強調細節教育。馬氏通備將練習者的身體狀況分成龍型、虎型、鷂型三種正型,三個正型以外又有三個亞型,即亞龍型、亞虎型、亞鷂型,三正三亞,即六種體型類別。龍型是長大型,虎型是健壯型,鷂型是敏捷型。以正型標準衡量,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者稱亞型。凡正型都應該具體氣力充盈這一基本條件,氣力不足則居其次,非徒以外觀定型也。教育所以發展人之天賦,故必注意其個性,使各人所具之自然特長各得發育遂長。[14]劃一齊平、毫無殊異之人,絕非馬氏通備的教育理念。在技術動作的教學中,注重強調每個技術動作的細節,嚴守通備技術風格,不擅自改動,保持通備技術體系的原汁原味。
練習通備者先評定身體類型,然后再設定相應的教材系統和發展方向。通備的根基在劈掛。劈掛屬于古典武藝的長拳類,強調以快捷迅猛取敵,以長刁冷抽制勝,基本風格可歸納為大劈大掛,速進速退,陡起陡落,長掣長擊,因此劈掛最適宜身軀高大而四肢頎長的人。也由于此,通備最重龍型,視龍型為三型之上乘,在很大程度上,“通備勁”就是以正龍型為“樣板”設定的。然而,習武者不可能都是身軀長大者,長大固然是一種先天優勢,而虎健強勁同樣也是一種優勢,短小精悍也未嘗不是優勢,一言以蔽之,優勢總是相對而言的,許多時候是因人而宜的。基于這樣的認識,通備先賢們不斷地擴寬技術兼容的范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因材施教,長短隨宜”的訓練思想得以落實,得以從容實行。簡要來說,所謂“因材施教”,就是根據“三型六類”理論,設定習練對像的教材配置,再通過教學實踐進行調整,逐步確定其技術發展方向或主攻方向。一般說來,練通備者,不論其身體高低輕重,都必須練劈掛,接受嚴格的劈掛訓練,以培植“通備勁”的基礎,而且劈掛——特別是單劈手、招風手、纏額手等勁力性招勢,是終其一生不能擱置的功夫。
每個練習者又可以在綜合訓練的基礎上根據身體條件設定專項發展方向,如長大迅猛者宜以劈掛為專擅,強健多力者宜主攻八極,短小精悍者宜發展翻子,靈活敏捷者可多攻戳腳,如此等等。一個人或偏于長,或偏于短,或在七剛三柔,或七柔三剛,各隨其所宜,不但隨其體型材質之宜,而且隨其性情好惡之不同,以貫徹因材施教,隨宜發展的訓練原則。馬氏通備要求嚴守規矩而追求最大程度的自我釋放,因身形各異、力不同科,每個人需逐步找到并形成自己最感舒暢的表達模式。
通備傳習者依據習練者的基本特點,以鞭桿與棍等器械為基礎,引導其向某種器械專項發展,如矯健者專攻刀、棍等,輕捷者專攻劍、鞭桿等。當然可以兼項發展,但大多數況下不宜兼之過寬,由博返約,藝貴專精,對練武者來說,的確是應該遵行的原則。通備的訓練理論豐富而質樸,可操作性很強,經過長時間的實施和驗證,取得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經驗,有些已發展成為規范化的教程,整理這些教程是通備武學一項重要工作,目前這項工作正有序的進行著。
2.4 習行教育理念
習行教育理念倡導受教育者的實踐表率作用,強調每一個習練通備的人,追隨馬氏通備思想的人,都可以以身作則,以己為表率,發揮榜樣作用和很強的示范作用。這是既是儒家經典教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同時也是顏李學派重要的治學修行方法。馬鳳圖先生強調他所宏揚的“通備”是平實而嚴謹的“實學”,不存在任何虛妄難解的內容,沒有什么秘不傳人的玄機。但是馬氏通備體系深深地根植于武術文化的歷史淵源之中,內涵十分豐富,分技又比較細密,所以,如果要把它歸納成為簡明扼要的幾個要點,深入淺出地講出來,讓人一聽就明白,這其實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馬氏通備武藝幾代傳人都堅持“文通兼備”的指導思想,因此這一門武學在傳承上也秉承“擇人必嚴,傳藝必嚴”的授受原則,努力尋找具有文化基礎的武術愛好者作為傳人。馬氏通備武藝“傳藝必嚴”是人所共知,從無折扣的,但是因為某些歷史原因,具有優秀文化基礎的人才并非俯拾皆是,這給“擇人而授”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是即使如此,馬氏通備武藝也一直堅持從高文化層位人群中尋找傳人,無論是馬鳳圖先生、馬明達教授,還是馬廉禎老師都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一線工作。
馬鳳圖先生認為通備傳人,必須是學術兼博的具有高等文化素質的精英人才,正如馬鳳圖先生當年所言,“不讀萬卷書,難作通備人”。而為師為長者,則必須是德藝皆修、具有高尚文化品格的學者,這也要求每一個通備傳人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將自己打造成為“德”“業”都出類拔萃的人。
馬明達教授堅持認為只有“口傳心授”才是傳承傳統武學精髓的正確途徑,因而在推廣的過程中能夠堅守“傳藝必嚴”的原則,又曾明確表示,“絕不使用流俗方式進行武術的傳播”,這在劣質書刊、光碟出版物橫行的今天,實在是擲地有聲的鏗鏘之音。正因為在精英教育下的高素質傳人,也正因為有這樣的指導思想,通備武藝才能于今日武林之中傲然而立,在門派林立中避免種種歪風斜氣的浸染,守住自身頭上腳下一方嚴謹精純的天地。
3 結語
馬氏通備武學教育理念嚴格意義上講是馬鳳圖教育理念的延續,馬鳳圖教育理念又深受顏李學派的影響。他是時跨三代(晚清、民國和新中國)的人,是新舊結合最典型的人物。馬氏通備武學之所以擁有這么強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其核心是他所倡導積極、主動應對的狀態。他所倡導的很多教育理念是新舊結合的,某種意義上馬鳳圖教育理念和張之江先生所倡導的教育理念是一脈相承,各自表述的。馬鳳圖先生所倡導的是利用現代的、科學的、理性化的知識結構、梳理方法將傳統武術的訓練法、分類法、認知、價值表象等都進行改良,來形成全新的系統,這個系統在他的時代被定義為通備武藝,到馬明達教授時期被稱為“馬氏通備武學”。杜威先生說:“教育是社會進步和社會改革的基本方法,是人類社會進化最有效的一種工具。”[15]
馬氏一門所傳承的通備武學,是一個經過許多武術先賢努力而逐步建構起來的武術體系,在技術上和理論上都極具特色,并保存了許多稀有的古典武藝內容。[16]馬氏通備武學,現已發展成為最具學術潛力的武學體系,它的發展一直都受到廣大武術愛好者的深切關注。陶行知先生說:“教育是一種行動,而行動需要理論的指導,沒有理論的行動,那是盲動。并且行動之能否成功,要看理論之是否正確。”馬氏通備武學堅持“融通兼備”的學術理念,不斷借助交流豐富自己,提升自身的學術含量和文化品位,其理論體系一直在不斷的完善之中。馬氏通備武學所宗奉的交流,包括了跨地域的、多民族的和古今武藝的交叉融會與多元貫通,因此,它最大的特點是打破門派框架,走出拳種局限,明顯具有多元綜匯的優勢。通備武學始終堅持走學科發展的道路,堅持高揚“武學”的大旗,堅守“練打結合”的技術方向,貫徹強身健體的公共價值。同時,努力探掘和整理古典武術文獻,建構既有傳統淵源,又有創新特色的武學體系,并且已經成就斐然,得到武術界有識之士和國際武術學界的同聲贊揚,這是通備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