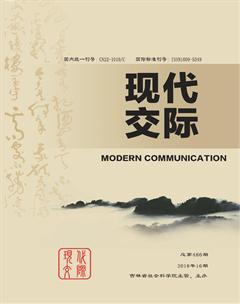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譯者的適應性選擇研究
關燕梅
摘要:作為一個跨學科性質的研究理論,生態翻譯學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該理論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環境的選擇過程,強調譯者的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通過“三維”轉換方法實現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因此,文章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通過對比分析方法對《匆匆》兩個英譯本中譯者在三維轉換層面的適應性選擇作出分析解讀。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 《匆匆》 適應與選擇 “三維”轉換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16-0068-02
一、生態翻譯學理論
作為翻譯學領域內一種新的研究形態,生態翻譯學建立了以翻譯適應選擇論為中心的翻譯理論體系。生態翻譯學理論“以‘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題概念為基調,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為核心,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解的翻譯理論范式”。(胡庚申,2008a)該理論強調譯者的主體作用,并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即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不斷作出適應性選擇的過程”。根據胡庚申提出的理論基礎,翻譯適應選擇論以“譯者”“適應”“選擇”作為其核心要素,以“三維”轉換為翻譯方法來指導翻譯實踐,即實現譯文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上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因此,作為一種全新的理論視角,生態翻譯學突破了以往翻譯研究的局限和缺點,將翻譯放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來探討翻譯實踐,更好地詮釋了翻譯過程的本質。
二、《匆匆》及相關研究
《匆匆》是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的作品,文章語言精練,韻味深長,圍繞“匆匆”二字將時間流逝的蹤跡用細膩的筆觸表達出來,同時也傳遞出作者對時光流逝的無奈和惋惜。通過以往對《匆匆》翻譯研究的梳理,大多研究者是從傳統翻譯視角如翻譯“信、達、美”原則(張 欣,莉文,2014)、形合意合(李迪,2014)、篇章銜接手段(王聰慧,2012)、功能對等理論(楊帆,2017)等對原文及譯文進行分析。這些研究通過比較原文與譯文來探討二者是否實現了語言上的對等,并對譯文文本進行藝術性與審美性的探索。盡管母燕芳(2010)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對《匆匆》及英譯本在語言維對譯者的適應性選擇進行了分析,但從該角度對《匆匆》進行三維轉換的研究仍很鮮見,因此該文從生態翻譯學理論出發對張培基(以下簡稱張譯)和朱純深(以下簡稱朱譯)的譯文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層面進行對比,分析不同譯者對原文翻譯環境的適應與選擇,以整合高質量的譯文。
三、“三維”視角下《匆匆》譯文的對比分析
散文在翻譯過程中因其語言特點而顯現出復雜性和困難性。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任何高質量的翻譯文本都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從多個層面適應與選擇的過程與結果。在翻譯前,譯者需要對原文、目標讀者及社會環境作出分析;在翻譯中,譯者不僅要實現在語言層上的轉換,更重要的是實現對文化層和交際層內涵意義的轉換。巴斯奈特(1990)認為“翻譯是文化內部與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絕不是一個純語言的行為,它深深根植于語言所處的文化之中。”因此,譯者不應局限于傳統的僅關注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是將最終影響交際理解的文化因素也置于翻譯實踐,并選擇與目標文化相適應的譯文。
(一)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維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2008)作為一篇語言凝練又富含哲理的散文,如何準確地將原文轉換成讓譯文讀者理解的語篇,讓譯文讀者通過語言來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就需要譯者發揮主體作用,選擇適合原文語境和譯文語境的語言表達。
例1:但不能平的,為什么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張譯:However, I am taking it very much to heart: why should I...all?
朱譯:It is not fair though: why should I... nothing!
該句中兩位譯者對“不能平的”這一詞采取了不同的翻譯方式。朱譯用“not fair”僅從字面意義進行直譯,將“fair”譯為公平、平等之意,而此處作者表達的是內心的疑惑和憤憤不平,這里直接用“fair”顯得較突兀,對原文生態環境的理解和對作者當時寫作背景的把握稍顯欠缺,因此也就沒有將作者對時光匆匆流逝卻又無奈的苦悶表達出來;而張譯用“taking it very much to heart”這一短語,準確理解了作者的表達意圖,其中“heart”一詞更是凸顯了作者內心深處的種種疑慮,譯出了作者因時光流逝而痛惜感慨,讓讀者領會了原文作者的時代境遇,產生了共鳴。因此,張培基的譯文在語言維上對原文做到了更為恰當的理解,實現了在語言層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二)文化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文化維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與闡釋”。(胡庚申,2008) 在翻譯過程中,為使譯文讀者準確理解原文所表達的思想內涵,翻譯者需要重點關注兩種文化涵義間的適應與選擇。因此譯者應該在真正理解兩種文化共性和差異的基礎上,將原文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準確地傳給譯文讀者,實現交際意圖。
例2: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
張譯:The sun has feet too, edging away softly and stealthily .And, without ... revolution.
朱譯:The sun has feet , look , he is treading on,lightly and furtively; and I...revolution .
在該句中,作者通過擬人手法恰當地把時間稍縱即逝的狀態描述了出來,表達了作者因時間流逝而無奈和感嘆。在譯文中,兩譯者充分地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感嘆和痛惜。但思想的同一中又蘊含著變化,而這種變化就體現在詞語所負載文化涵義的差異上。兩譯者對原文“輕輕悄悄地”一詞做了不同的處理,譯出了各自的特色。張譯用了“softly and stealthily ”,朱譯用了“lightly and furtively”。根據原文作者表達的情感以及對文化觀念的理解,“太陽輕輕悄悄地挪移”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描寫,沒有任何感情色彩上的修飾。張譯用了兩個中性詞,做到了對原文環境的適應,而朱譯用的“furtively”一詞帶有貶義色彩,沒有很好地適應原文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內涵。因此譯者在翻譯富含文化內涵的篇章時,要深入理解原文的文化內涵,把握原文翻譯生態環境,選擇符合文化維度中的語言表達形式,實現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