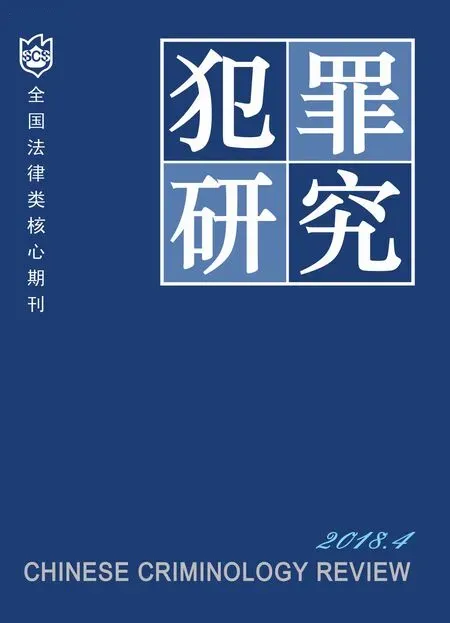犯罪控制視野下死緩適用地位探析
姜遠亮
死緩是我國獨創的別具特色的死刑執行制度,具有限制死刑實際執行與促進犯罪人改造兩大功能。經過《刑法修正案(八)》與《刑法修正案(九)》的修訂與完善,死緩制度發展成由一般死緩、限制減刑型死緩及終身監禁型死緩構筑的三位一體的刑罰系統,并且向死刑立即執行轉化的條件更加嚴格,極大壓縮了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空間,逐漸擔負起死刑立即執行替代者及死刑制度掘墓者的歷史角色。從本源意義上追溯,死緩是為“少殺”而生,其自產生之日起便擔負起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使命。然而,將一個死刑犯判處死緩是少殺,將多個死刑犯判處死緩也是少殺,將全部死刑犯都判處死緩更是少殺,這三種情況都實現著死緩少殺的制度功能,但發揮少殺功能的程度卻大不相同,第一種情況發揮著最小限度的少殺功能,第三種情況發揮著最大限度的少殺功能。究竟哪一種少殺程度為死緩制度所追求,在不同歷史時期死緩有無一以貫之的優先適用權,死緩能否實現少殺功能最大化?這必然涉及死緩制度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問題。隨著死緩制度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其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日益成為亟待明確的重要課題,即在死刑適用中,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誰是通例誰又是特例;在判處人數上,死刑立即執行犯與死緩犯孰多孰少及所占比例。對上述問題探究,有助于明確我國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調控我國限制乃至廢止死刑適用的步伐,并將對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實踐產生重要影響。
一、理論爭鳴: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之觀點概覽
我國死刑包括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兩種。在罪該處死的被告人數量恒定的情況下,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在適用數量上必然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死刑立即執行的大量適用必將擠壓死緩的適用空間,反之亦然。因此,兩種死刑執行方式之間基于地位之爭的較量與對抗實屬難免。誰是死刑適用的通例,誰又是特例,一直是死刑適用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對此,刑法學界與實務界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種見解。
(一)死緩特例說
死緩特例說認為,死緩只是對罪該判處死刑中極少數有改造希望的犯罪人給予最后一次悔過自新機會的刑罰制度。立法者在刑法典中設置死緩制度,是將原本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極少數犯罪分子拉出地獄之門,為其“死而復生”提供特殊渠道。既然是特殊渠道,那么死緩就只能作為死刑適用的特例。特例說似乎也得到現行刑法典的支持。《刑法》第48條規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從文本表述來看,首先,該條對死緩適用標準即“不是必須立即執行”,采用的是需要明示列舉的排除式規定,而對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卻采用的是保留式規定。按照社會通識判斷,采用保留式規定一方一般都是事物的通常狀態。其次,該條所使用的是“可以”一詞,而不是“應當”。即便存在“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況,司法機關也有不選擇死緩而逕行適用死刑立即執行的權力。難怪有學者指出,“立法首先是將‘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作為通例,而將死緩作為在‘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時的特例。”①盧建平:《死緩制度的刑事政策意義及其擴張》,載《法學家》2004年第5期。上世紀80、90年代的司法實踐似乎也印證著這種觀點。有資料顯示,人民法院每年判處的死刑犯,多數都是死刑立即執行犯。死刑立即執行犯占每年死刑犯的總數約為80%。②胡云騰:《死刑通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71頁。死緩特例說的觀點在實務界曾廣有市場,并且在嚴打時不斷得以強化。
(二)死緩通例說
死緩通例說認為,死緩應當作為死刑適用的首要選擇和基本方式。只有對罪該處死、案發后又負隅頑抗、拒不認罪服法、積極悔改的罪犯,才能將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作為最后適用的非常的迫不得已的選擇。③梁根林:《刑事制裁:方式與選擇》,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頁。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論證:其一,從死緩制度設計意旨上看,死緩自從其創設之日起就發揮著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功能。如果讓死緩制度不辱使命,就必須使其成為死刑適用的通常方式。死緩制度的創立者毛澤東同志曾明確提出死緩適用的比例,即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者。其二,在限制乃至廢止死刑日益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下,我國應當積極順應這一國際趨勢,減少死刑實際適用,改善死刑超級大國的形象。目前在立法廢止暴力犯罪死刑舉步維艱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大規模地適用死緩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因此,死緩應當成為死刑適用的首選。這種觀點在學界頗受追捧,成為通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多有濃厚的死刑廢止情結,在對“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標準的明釋時,要么從正面廣泛列舉諸種情形,要么從反面限制性地標明須立即執行的情形。
(三)死緩必經說
死緩必經說為少數學者所堅持,認為死緩應當成為死刑適用的必經程序,對所有死刑犯都應當判處死緩。④張文、黃偉明:《死緩應當作為死刑執行的必經程序》,載《現代法學》2004年第4期。這種觀點的主要論據是:死緩制度是為限制死刑適用而生,而只有讓死緩成為死刑適用的必經方式,才能使死緩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制度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否則,死緩的適用難免會受到司法裁量權的人為排擠,尤其會受到死刑民意或媒體輿論的影響,導致民意殺人與輿論殺人現象的發生。同時,將死緩一體適用也能避免就死緩適用標準爭執不休的亂局。
上述三種觀點,死緩特例說有違該制度設立的初衷,亦不符合限制乃至廢止死刑的國際趨勢,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在死緩通例說與死緩必經說的較量中,持死緩必經說觀點的學者列舉出死緩選擇性適用的三大弊端及死緩作為死刑執行必經程序的五大優勢來論證,①張文等:《十問死刑——以中國死刑文化為背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43頁。似乎二者優劣立顯、高下分明,死緩必經說有著死緩通例說無可企及的優越性。但對于死緩通例說與死緩必經說孰是孰非,不能簡單而論,而須置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考察。在一定歷史時期,死緩的某種地位可能滿足該歷史時期的社會需求,而在另一歷史時期,該種地位又可能因不合時宜而慘遭遺棄。拋開社會歷史條件而單純地就事論事,難免給人形而上之感。如同死刑廢止的話題一樣,死緩的適用地位也絕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價值選擇問題,而是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可以說,在死刑適用地位上,死緩并不是一個單靠決策者政治魄力就可以人為拉伸與緊縮的橡皮筋,也不是靠立法者大筆一揮就能產生立竿見影之效的程式機器。因而,在對上述觀點進行評析之前,有必要結合社會歷史條件對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的歷史演進做一回溯及對其發展趨勢做一前瞻。
二、回溯前瞻: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之軌跡探索
死緩特例說、通例說、必經說實際上向人們展示了一條強化死刑→限制死刑→廢止死刑的清晰路徑,描述了三幅死緩適用狀況的不同歷史發展場景。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隨著包括社會治安形勢在內的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刑事政策特別是死刑政策在其中起著調節器的作用。上述三種觀點正是對死緩在三個不同歷史階段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的精當寫照,由此可以將新中國自有刑法以來的刑事法制發展歷程與前景劃分成三個階段,即死緩地位演進之“三階段論”。
第一個階段自1979年刑法頒布到2007年死刑適用狀況之轉折。這一時期可以稱為死緩特例時期,死緩僅僅作為死刑立即執行的補充,司法實踐中充斥著為數眾多的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該時期由于我們改革開放全面鋪開,社會處于急速轉型期,由此出現嚴重的社會失范現象,社會治安形勢極其嚴峻,嚴重惡性犯罪居高不下。在這種情勢下,為了保持對嚴重犯罪的高壓態勢,決策者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強化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進而將死緩禁錮于特例地位。一是在刑事政策上,奉行嚴打政策,要求對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的惡性犯罪從重從快地打擊;二是在刑事立法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多部單行刑法,使1979年設置的死刑條款急劇膨脹,并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基本得以保留;三是在死刑復核程序上,將大部分死刑案件的復核權下放到地方,下放力度之大、范圍之廣、時間之長令人匪夷所思。可以說,這些舉措是在當時的社會形勢下遏制嚴重刑事犯罪不得已的策略或極為無奈之選擇。在嚴打刑事政策指導下的刑事司法必然會擠壓死緩的適用空間,使得死緩處于死刑立即執行補充的地位。死刑立即執行則在司法實踐中備受推崇,成為死刑適用中的寵兒,而死緩自然沉于失寵的角落。有學者根據當時司法實踐狀況推斷,我國每年判處死刑的,至少3/4以上是死刑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②胡云騰:《死刑通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頁。
第二個階段從2007年至將來某一時期。這一時期是死緩通例時期,死緩在死刑適用的地位步入新常態,其通例地位愈加鞏固,適用率不斷攀升。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大領域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民生活日益富足,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識尤其是權利意識和人權意識空前增強。開啟死緩通例時期的是“一個大背景和兩大標志性事件”。“一個大背景”是指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刑事司法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將單純的懲治型司法、對抗性司法拓展為與恢復性司法、合作性司法并重之局面,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亦如火如荼地開展。“兩大標志性事件”是指,首先在刑事政策上,黨中央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取代了單向度的嚴打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中央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基于對20多年嚴打政策的理性反思而出臺的新型刑事政策。該政策要求“針對犯罪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該寬則寬,該嚴則嚴,有寬有嚴,寬嚴適度。”①高銘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酌定量刑情節的適用》,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1期。在我國刑罰體系總體趨重、“多殺長判”成為司法實踐科刑主旋律的情況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有所側重的,其更加強調“以寬濟嚴”。其次,在死刑復核程序上,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26年之久的死刑復核權,由其統一行使。死刑復核權收回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剝奪了地方官員操持生殺予奪的大權,更是體現了中央對死刑適用的審慎態度及對生命權的充分尊重。由于最高司法機關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我國死刑適用狀況發生歷史性的變化,2007年判處死緩的人數多年來首次超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國開啟了限制死刑的立法運動。2012年和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不僅廢止了22個死刑罪名,而且創設了兩種特殊的死緩類型,并嚴格了死緩變更執行死刑的條件,增強了死緩替代死刑立即執行的功能。在此時期,死緩必將逐步擴展發揮作用的空間,壓縮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范圍,使司法實踐中被執行死刑的人愈來愈少,進而為第三個階段的到來創造有利條件。當然,死緩適用率的提升一方面要靠司法實踐循序漸進地推進,另一方面要及時借助立法之手鞏固司法推進的成果。
第三個階段是將來某一段時期。這一時期是死緩必經階段。這時社會文明與法治進步已達到相當程度。經過第二個階段死緩適用率的大幅提升,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必將緊緊壓縮在包括故意殺人在內的致命性暴力犯罪案件中。將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最后一塊領地讓渡于死緩適用,使死緩成為所有死刑案件的必經程序,這必將是一個“驚心動魄的跳躍”。死緩必經時期是死緩達到廢止死刑一個步驟的必經時期,是我國死刑徹底廢止的前夜。世界各國幾乎是以相同的方式走上一條死刑之路,卻以不同的方式走上一條死刑廢止之路。②陳興良、周光權:《刑法學的現代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頁。我國死刑廢止必然要借助于死緩制度,通過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來實現,而不能是疾風驟雨式的激烈變革。雖然死緩歸屬于死刑麾下,與死刑的命運息息相關,但是在這一時期,死緩更為鮮明地扮演著死刑制度掘墓者的角色。可見,死刑的終結是通過死緩的極限適用來實現的,當死緩成為所有死刑案件必經的前置程序時,死刑可謂是壽終正寢了。
縱觀而論,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特例地位、通例地位、必經地位可以說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脫離當下的社會歷史條件而談論死緩的適用地位不是流于 “滯后”就是疏于“超前”。當然,強調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并不等于否定決策者積極的政策引導。筆者認為,死緩的適用狀況與刑事政策的指引息息相關。有什么樣的刑事政策,就有什么樣的司法,政策嚴則司法嚴,政策寬則司法寬,可以說是一種基本的國情。③趙秉志:《死刑改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頁。決策者可以采取積極有效的舉措推動某一階段的歷史進程。
在不同的時期,由于死緩的適用地位不同,死緩制度的實際功能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在死緩特例時期,死緩在很大程度表現為一種死刑赦免功能。通常基于政治、外交、民族等因素考慮而對某些人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因此,樊文教授經考察我國以往司法實踐后,指出死緩“形式上盡管仍然是經由法官的裁判變更刑罰,但是本質上是比較特殊的附條件赦免制度”。①樊文:《論死刑立即執行犯赦免請求權之保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5年第5期。在死緩通例時期,死緩發揮著死刑限制功能。隨著死緩的大量適用及死緩適用率的不斷提升,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被擠壓在極其有限的空間,并呈現逐漸萎縮的趨勢。在死緩必經時期,死緩發揮著死刑廢止功能。隨著死緩通例時期死緩之死刑限制功能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死緩適用率必將向其極限位置靠攏,死緩對死刑最極端的限制便是死緩必經狀態。此階段死刑基本上形同廢止,僅有死刑之宣告,殊有死刑之執行。
三、正本清源:對現階段死緩通例地位的論證分析
死緩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要與社會歷史條件相適應,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死緩必然有其應處的地位。這種應處地位取決于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治安等因素在內的社會歷史條件,同時也深受決策者政治抉擇與政治魄力的影響。不容否認,死緩特例僅是我國社會急劇轉型期、社會治安極其嚴峻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權宜之計,是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而不能作為應對犯罪的長遠之策。死緩特例有違死緩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意旨,與可“殺”(死刑立即執行)可“不殺”(死緩)的堅決“不殺”(死緩)的死刑政策相背離,同時也有悖于當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寬濟嚴的要求。現在死緩特例觀點已經為我們所擯棄。在我國死緩變更為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數量微乎其微的語境下,主張死緩必經說無異于事實上廢止死刑。在嚴重、惡性犯罪居高不下、集體意識對死刑存在廣泛公眾認同的情況下,死緩必經說確實有所超前,超越了其所處社會歷史條件。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現行刑法中還存置有較多死刑罪名、司法實踐中死刑使用人數較多而又不能廢止死刑的情況下,奢談將所有判處死刑的罪犯一律適用死緩,是不切實際的,這既不符合我國的犯罪現狀及同犯罪作斗爭的需要,還超出了廣大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從而不為廣大群眾所支持。②釗作俊:《死刑限制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306頁。甚至連持死緩必經說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將死緩作為死刑案件的必經程序所招致的阻力與廢除死刑的阻力不相上下。③張文等:《十問死刑——以中國死刑文化為背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頁。綜觀死緩地位的三種形態,死緩通例說是我們當下應當堅持的切實可行的選擇。然而,關于支持死緩通例觀點的理據,學界通常認為,死緩通例說是我國當下嚴格限制與慎重適用死刑政策指導下的產物,是黨中央在限制乃至廢止死刑的國際趨勢下作出的價值選擇。筆者并不否認這種立論根據,但是該立論根據過于偏狹與短視,既沒有傾聽現代刑事法治的訴求之聲,也沒有考察刑罰適用狀況的現實樣貌,缺乏理論根基與經驗依據。
首先,從價值選擇上講,死緩通例地位是新時期決策者基于價值衡量而在政策取向上慎重抉擇的產物。同一死刑條文,如果持限制死刑適用與否的不同觀念,會直接導致受刑人生或死截然不同的結果,進而得出實際被執行死刑人數大小不同的數據。④同上,第190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語境下,就是要用盡可能節省的刑罰取得最佳的預防犯罪效果。⑤江必新:《樹立科學的刑事司法觀——論刑事審判十大關系》,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10期。因而,在我國死刑立即執行大量適用的現實情勢下,死緩作為限制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制度安排必將備受推崇。在刑事法治更加昌明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死緩還肩負著踐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歷史使命。在死刑適用上,以寬濟嚴實際上就是以寬和的死緩來“濟”嚴厲的死刑立即執行。因而,司法實踐應當從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政策走向中,從死刑立即執行適用所固有的弊害中,從死緩制度設計的意旨中對死緩的地位展開新的認識。唯有站在此高度,我們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導出死緩是死刑適用的通例,司法實踐中判處死緩的人數在數量上理應超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
其次,從刑事法治上講,死刑立即執行的謙抑性決定其必然成為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的“最后手段”。對于一個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國度來說,崇尚法治尤其是刑事法治應該成為該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在現代法治社會,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門的補充法、保障法,因而刑法具有第二次法之品格。此種品格決定刑罰應當成為社會其他手段無法保護法益時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同理,在刑罰方法之中,位于刑罰之巔的死刑應當成為其他刑罰方法無法保護法益時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進而在死刑執行方法之中,死刑立即執行應當成為在應對罪該處死的犯罪行為時,其他死刑執行方法無法充分保護法益時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換言之,能用其他手段處理的,絕不動用刑罰;能用其他刑罰方法處理的,絕不動用死刑;能用死緩處理的,絕不動用死刑立即執行。死刑立即執行成為法治社會對犯罪的各種反應方式中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手段,因此死緩具有相對于死刑立即執行的優先適用權,這是死緩成為死刑適用的普遍現象的法理根基。從刑罰的謙抑性到死刑的謙抑性再到死刑立即執行的謙抑性,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刑事法治文明的進步與人權保障功能的強化對死緩地位的訴求。死刑立即執行作為最嚴厲的刑罰手段,則無疑應當成為其他相對較輕的刑罰方法不能發揮其功能時最后適用的非常刑罰方法。①梁根林:《刑事制裁:方式與選擇》,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最后,從經驗事實上講,位于刑罰金字塔最頂尖的死刑立即執行必然是各種刑罰方法中適用最少的措施。判處死緩的人數多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不單單是價值選擇的結果,也不僅僅是刑事法治力倡之訴求,更是一種基于經驗法則的事實命題。人類社會的基本經驗告訴我們,判處刑罰的人數與刑罰的強度呈反比關系,并呈現出金字塔分布的態勢。按照正常的刑罰金字塔生態分布,適用刑罰強度越重的犯罪行為,其犯罪人的數量就越少。死刑作為眾刑之首高居刑罰金字塔的塔尖,其適用人數在整體犯罪人中所占數量最少,而越往下走,隨著刑罰強度的降低,適用該刑罰的犯罪人的數量就越來越多,到達塔基時為懲處輕微犯罪行為而設置的刑罰適用人數最多。因為,對于大部分來說,都缺乏實行重大犯罪所必需的氣魄,就像缺乏表現偉大美德所必需的氣魄一樣。②[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頁。死刑立即執行和死緩不僅僅是死刑的執行方式,也可以看做是死刑的子刑種,起到量刑臺階的功能。作為獨立于死刑立即執行的死刑子刑種,死緩在刑罰強度上明顯遜色于死刑立即執行。同理,在死刑大刑種下,判刑人數也呈現金字塔分布的態勢,作為死刑中較為嚴厲的子刑種,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數量自然應當低于死緩的適用數量,這才是死刑子刑種的正常分布狀態。刑罰金字塔分布態勢理論為司法實踐中擴大死緩適用提供了經驗根據。
由此可知,在當下死刑適用地位上,死刑立即執行應當處于特例、非常狀態,而死緩則應當處于通例、通常狀態。因而,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死緩的犯罪人數量理應多于適用死刑立即執行的犯罪人數量。然而決策者卻因特定歷史時期一時的治安狀況惡化,長期奉行嚴打政策,一直將死刑立即執行當作死刑適用的通例,而把死緩作為特例適用。直到2007年,死刑適用才回歸理性的分布狀態。
四、固本培元:強化死緩通例地位的現實路徑
要使死緩保持并鞏固其在死刑適用中的通例地位,不斷拓展發揮少殺功能的空間,就必須有不斷改進的制度措施跟進。否則,死緩通例地位會游移不定,其在死刑適用中的地位甚至會倒退到2007年以前的狀態,導致死緩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制度目的落空。因而,合理的制度安排與嚴格的程序設計是保障死緩通例地位的不二法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不斷完善死緩制度相關內容及配套措施,為其擴大適用清除障礙。目前,死緩適用的主要障礙有兩個:一是死緩適用標準不夠明確,使得其適用范圍極易受到司法機關人為壓制;二是死緩懲罰力度有待檢驗,使得其適用力度仍會受到公眾心理抵制。因而,在現實操作上,應當堅持“一個放寬,兩個嚴格”的改進思路,采取有效舉措以適應死緩通例時代的發展需要,并為死緩從應然的通例地位向超然的必經地位跨越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個放寬”是指放寬死緩適用的標準,為盡可能擴大死緩適用提供實體依據。刑法將“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作為適用死緩的標準。但是對于何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既沒有刑法典的明確規定,也沒有司法解釋的具體闡述。正是由于該標準的抽象性、模糊性、難以操作性的缺點,使得司法機關獲得了充分的自我理解與自行解釋的巨大裁量權。在飽受嚴打觀念與重刑主義思想慣性影響的制度環境下,司法實踐對此標準往往是嚴格掌握,擠壓死緩適用的空間。并且這種飄忽不定的標準極易受到社會治安形勢、民憤、輿論等外界因素的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很容易將排除死緩適用作為迎合民意輿論及擺脫現實矛盾的慣常之策。因而,對“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標準,我們必須加以改進,改進的方向便是標準的明確性和擴張性。首先,最高審判機關應當在實證調研的基礎上通過司法解釋明晰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的界分標準。在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之中,明晰其中一個,另一個的邊界自然會變得清晰。在具體操作上,既可以從正面盡可能多地列舉“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諸種情形,也可以從反面限制性明示“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但是在現行立法框架下,列舉“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更為可行,學界亦往往從此角度入手對司法實踐的通常做法進行歸納列舉,而且這種方式可以使我們適時地根據情勢發展增列死緩適用的新情形,從而不斷擴大死緩的適用范圍。其次,最高審判機關應當加強案例指導,建立并完善案例指導制度,遴選并發布具有代表性的指導性案例,為死緩適用提供更加具體的參照標準。同時,最高審判機關可以通過指導性案例的推陳出新,不斷擴張死緩的適用空間,確保死緩適用率的持續提升。
“兩個嚴格”一個是嚴格限定死緩變更執行死刑的條件。1997年刑法將“故意犯罪”作為死緩變更執行死刑的絕對條件,取代了1979年刑法“抗拒改造,情節惡劣”的規定,使得變更條件具有極準的明確性與極強的可操作性。但是這種無視故意犯罪具體情狀而一概變更執行死刑的做法與死緩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的意旨嚴重背離,也與為現代刑事法治所極力摒棄的絕對確定的法定刑并無二致。故意犯罪在犯罪性質、犯罪情節、主觀惡性等方面存有較大差異,不能不問故意犯罪性質之差異、情節之輕重、惡性之大小,只要出現故意犯罪就改為死刑立即執行。這一點也得到司法實踐部門的認同。其實,在1997刑法修訂時,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組于1996年11月8日所提《刑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的修改意見中即指出“在緩期兩年期間又故意犯罪的條件外,還應當加上‘情節惡劣’等限制條件”。①高銘暄、趙秉志:《新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總覽(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1頁。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對死緩變更執行死刑條件的修訂完全沿循了這一修改思路,以“情節惡劣”作為故意犯罪的限定條件,無疑有利于減少死刑的實際執行。但新的問題也由此而來,就是如果把握這里的“情節惡劣”?有學者指出,“情節惡劣”的表述過于概括、抽象,其限制死緩變更執行死刑的作用有限。②陰建峰、宋大偉:《論死刑變更執行死刑的條件》,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2016年第3卷,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筆者對此深以為然。“情節”的內涵復雜、外延模糊,包羅各種各樣的情狀。“惡劣”的判定更是主觀色彩鮮明,難以作出精準界定。理性的死緩制度設計應當對故意犯罪的范圍加以合理限定,使之既不過于嚴苛,又不流于輕縱。在此,筆者建議最高審判機關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從罪質與刑量上對故意犯罪的范圍施以雙重限制,以進一步明確“情節惡劣”的含義。具體而言,一方面從罪質上限制,將故意犯罪限定為侵犯公民重要人身權利犯罪和能最直接、最鮮明地反映犯罪人可堪改造程度的脫逃、組織越獄、暴動越獄、傳授犯罪方法犯罪,從而將普通侵財等惡性不大的犯罪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從刑量上限制,要求犯罪人所犯的上述罪行應當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罪質與刑量雙重限制”方案并不會造成對緩期執行期間犯其他故意犯罪的死緩犯的輕縱。《刑法修正案(九)》創設了死緩期間重新起算制度,對于故意犯罪未被執行死刑的,要求重新計算緩期執行期間,這無疑加重了死緩犯實際執行的刑期。
第二個嚴格是嚴格掌握死緩減為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后減刑假釋的適用規格。死緩罪犯與其他罪犯不同,這些人是在“少殺、慎殺”政策下得以保留生命的最嚴重的罪犯,在對其進行減刑和假釋時理應更加嚴格。《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前,我國刑法并未在減刑假釋方面對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的情形作出限制性規定,使之區別于原本就判處無期徒刑的情形。質言之,由死緩減為的無期徒刑與原本判處的無期徒刑在減刑、假釋方面沒有什么區別,致使中國的死緩,實際上相當于14年以上24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人被判處死緩的,一般實際關押18年左右,死緩成為變相的期限不是很長的有期徒刑。③陳興良:《刑罰改革論綱》,載《法學家》2006年第1期。這種情況不僅導致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空檔過寬、落差過大而難以銜接,更使得民眾對死刑立即執行產生深深的依賴。公眾有時之所以要求對嚴重的犯罪分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正是因為死緩過輕。只有強化死緩的懲罰力度,才能讓公眾真切認識到死緩的嚴厲性,降低對死刑立即執行的依賴,在情感上接受死刑的大幅度減少。因而,嚴格掌控死緩減為無期徒刑后減刑假釋適用規格能為死緩的擴大適用減少來自公眾的抵制,為死緩適用率的持續提升提供群眾基礎。正是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創設了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并提高了普通死緩犯實際執行的刑期,《刑法修正案(九)》針對貪污賄賂犯罪設置了終身監禁型死緩。上述立法舉措促進了死緩和死刑立即執行在嚴厲性方面的銜接,為司法機關多適用死緩、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修訂后的死緩畢竟適用時間不長,缺乏限制減刑或終身監禁的司法數據,其實際懲罰效果尚待檢驗。司法機關在減刑假釋適用中,稍有不慎可能會引發公眾對死緩嚴厲性的質疑。司法機關要嚴格執行和把握上述規定,實踐中對于普通死緩犯減刑假釋規格的掌握應當有別于判處其他刑罰的罪犯,提高減刑標準,減少減刑頻率,縮小減刑幅度,而且必須實際執行相當長年限才能準予假釋。
上述兩個嚴格中,第一個嚴格確保死緩犯盡量不死,第二個嚴格強化對死緩犯懲治力度。二者一個限制“死”刑,一個加重“生”刑,相互配合,融為一體,契合了公眾“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的報應心理。更為重要的是,立法機關要通過立法活動鞏固司法限制死刑的成果,在刑法典中對死緩的地位作出明確規定,廓清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的主次關系,將死緩規定為死刑的主要執行制度,扶正其通例地位。其實,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研擬過程中,曾有方案提出要對死緩地位作更進一步的規定,即將《刑法》第48條第1款后半段的規定獨立出來,作為單獨一款,并將其修改為:“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除必須立即執行的以外,應當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②趙秉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74-75頁。在死緩地位的規定上,立法機關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作出上述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