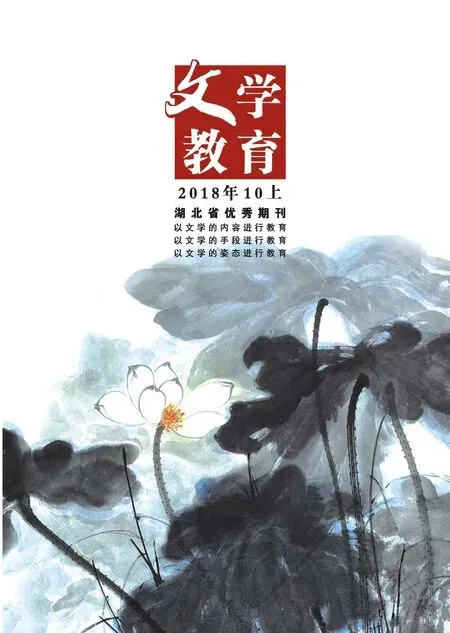淺談巴金創作思想的形成與轉換
張存根
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熱情、有進步思想、有獨特藝術風格的文學巨匠之一。縱觀巴金一生的創作,巴金的創作思想一直是較為苦悶甚至是郁悒的,雖然他努力戰勝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內心時時呼叫著法國悲劇革命家丹東的名句“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來激勵自己,但是他不能擺脫封建社會與家庭投給他心靈的沉重陰影,他無法廉價地樂觀與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劇的調子,如他自述:“一個黑影來掩蓋了我們的靈魂,于是憂郁在我們心上產生了。這個黑影漸漸地擴大起來,跟著他就來了種種的事情。一個打擊上又加第二個,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最后是悲劇的結局。
他創作思想的形成,是和以下這幾方面的因素分不開的:
一.家庭的影響:“愛”與“恨”的交織,形成生命的激情
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有著深刻的爾虞我詐、掙扎者、奮斗者的家庭體驗。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他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待人寬厚,疼愛孩子,體諒下人。在母親的教導下,巴金從小就懂得去愛一切人,去幫助處于艱難處境中的人們。巴金曾經說:“因為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享給別人,才想對自已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系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他在《我的幼年》中回憶說,“是什么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我常常拿這個問題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先在我的腦子里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巴金和“仆人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說:“我生在一個古老的家庭里,有將近二十個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仆人。”“我從小就愛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間長大的。”目睹仆人們的種種生活慘境,巴金說:“當這一切在我的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含著眼淚,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說我不要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助他們的人。”巴金幼年失去父母后,在家庭中受到長輩們的欺壓,他深刻體驗到了世態炎涼,真切感受到了冷酷、殘忍的封建家庭專制對人性發展的壓制和對年輕人身心的摧殘,逐步對專制制度產生了深惡痛絕的憎恨,“這個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眼前成了一個專制王國”。“許多可愛青年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囚籠里掙扎、受苦、呻吟以至于滅亡”。“憎恨的苗于是在我心上發芽了。接著‘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反抗的思想鼓舞著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鳥用力往上面飛,要沖破那個鐵絲網。”巴金從“愛”到“恨”的思想轉換以及叛逆思想的形成,對他后來的文學創造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詩禮傳家的封建家庭的虛偽和丑惡,使巴金由對下等人的同情轉而對上層人的憎惡,正如《家》所描繪的,許多可愛的、年輕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下受難、掙扎、死亡,他“開始覺得現在社會制度的不合理了”。
二.中外思想的影響:“新”與“舊”的斗爭,形成新的思想火花
“五四運動”后的巴金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追求民主、光明的人生理想使他堅決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巴金經常與大哥傳看《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新思潮刊物,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新文化、新思想,并奔突在暴殄人性的封建樊籠里。為遭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廣大青年尋找自由和光明。1925年巴金從南京東南大學畢業,開始研究和翻譯無政府主義,對法國人克魯泡特金具有強烈的反叛精神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曾和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通過信,對這位“為了信仰而坐過牢,希望革命建立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者十分崇拜,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政府主義顯然不可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盡管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在吶喊呼吁,但巴金看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仍然日益深重,整個民族仍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由于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巴金沒有看到現實生活中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新人的力量,因此雖然沖出了家庭的牢籠走上了社會,但是沒有得到真正心靈的解脫。前進的路究竟在何方,他不清楚。1927在大哥的資助下,他赴法留學,廣泛閱讀了盧梭、伏爾泰等作家的著作,對俄國民主派、民意黨人的傳記特別感興趣,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極大影響。無政府主義主張用對人的尊敬和愛去代替對神的信仰和迷信,憑借人的理性和良心來創建正義的、自由的人類秩序,廢除階級、等級、特權和任何差別。巴金試圖把無政府主義當作反對強權主義和封建專制、揭露現實黑暗、追求光明未來的思想武器。一方面,無政府主義并不是一種科學的社會理想,它不可能使人從根本上尋找到中國的出路,因此巴金逐步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失望情緒。另一方面,由于身處異鄉的孤獨和思親的苦悶,同國內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相碰撞,促使巴金奮筆疾書,去抒寫內心深藏的理想、激情與苦悶,發表了處女作小說《滅亡》,并第一次使用“巴金”這個筆名。小說塑造了一個受到五四思潮鼓舞,充滿矛盾、具有憂郁病態性格的青年杜大心,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無畏的獻身精神,渴望平等與博愛,憎恨專制與暴政,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滅亡”的基本含義是“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這也是小說的主題,它彌漫著熾熱的反抗激情、濃郁的悲劇氣氛和悲壯的進取精神,顯示了巴金的青春激情所燃燒著的生命之火,也開啟了他的文學創作道路。同時,小說以樸素、自然、流暢的語言風格為巴金小說的藝術風格定下了基調。
1928年,巴金離開法國返回上海,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無政府主義越來越充分地表現出自身的弊端和局限,巴金把這種絕望與憤怒的情緒化為文學創作的激情,在積極探索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上,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文學創作中來,1931年以后逐步進入小說創作的豐收時期。巴金小說創作主要表現為兩大創作主題:一是以《新生》、《萌芽》、《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為代表,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道路;二是以《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為代表,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弊害與專制制度的罪惡。
三.特殊歷史的影響:“生”與“死”的考驗,愛國主義激情的展現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在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從此,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抗戰爆發后,巴金滿懷愛國激情投身到抗日救亡文化活動之中,編輯《吶喊》(后改名《烽火》)和《救亡日報》。創作了短篇小說《莫娜·麗莎》,表現了前仆后繼、堅持抗戰的主題以及對侵略者的激憤之情,洋溢著時代的氣息,具有鮮明的戰斗色彩。這期間在完成《家》的續集《春》、《秋》的同時,完成長篇小說《抗戰三部曲》(又名《火》),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還魂草》、《小人小事》等。抗戰后期和抗戰結束后,巴金的創作轉向對國統區黑暗現象的批判,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長篇小說《寒夜》是這一時期富有藝術特色的力作,表現出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翻過一九四九年這歷史性的一頁,五、六十年代巴金的創作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于三、四十年代創作的階段性特征最明顯的變化是此前那種滲透于字里行間的憂郁的筆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熱烈明快,充滿樂觀情緒的創作基調。而四九年之后,他在作品中則完全改變了自我的形象,變成了一個熱情的歌手。他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時代,歌頌工農兵英雄,同時也歌頌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
縱觀巴金的小說創作,從內容上看,雖然受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學”中“革命+戀愛”的公式化創作的影響,但巴金的小說創作充滿了渴望變革的亢奮焦灼的激情,更注重對當時青年靈魂深處復雜變幻的思想情緒進行剖析。因此,同剛剛興起的“革命文學”相比,巴金的小說更能引起當時進步青年的共鳴,更能激起他們反封建的叛逆情緒。從創作風格看,巴金小說經歷了一個發展和轉變的過程,情緒由早期的外泄轉向后期的內蘊,藝術上由粗獷趨于精美。早期長篇小說《滅亡》和《愛情三部》等,初步顯現了巴金小說善于描寫家庭題材以及充滿微情的特點。30年代問世的《激流三部曲》,在內容上著重揭露封建專制制度對青年一代的殘害與扼殺。在小說的基調上,從《家》到《秋》體現了從高昂轉向低沉的轉化,在敘述方式上,體現了由主觀的傾訴轉向客觀的敘述,尤其注重生活細節的描寫,雖然顯得瑣碎、沉悶和冗長,但卻具有更加逼近生活的藝水效果。到了40年代發表的中篇小說《憩園》和長篇小說《寒夜》,既保持著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風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現,形成了一種定型的敘事風格,藝術技巧更加圓熟。《憩園》主要通過封建專制體制本身致使人格墮落和人性扭曲的過程描寫,進一步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罪惡本質。《寒夜》主要描寫了自由戀愛的知識分子家庭在各種生活重壓下的破裂,通過賦有時代特征的小人物的悲劇命運來揭露病態社會的黑暗與腐朽。兩部作品都以沉重的心情表現了時代的痛苦和悲哀,英雄主義色彩逐漸黯淡,對舊社會與舊制度的揭露更加深沉含蓄,反抗的激情和幻想的色彩逐浙收斂,深沉的控訴取代了激憤的吶喊,愛國三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得到了有力的彰顯,現實主義特色得到了進一步凸顯,小說的情感旋律與時代主潮的脈搏契合達到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