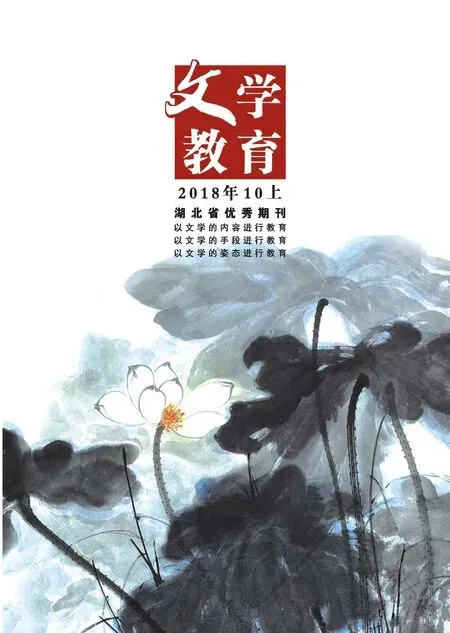從《弗蘭肯斯坦》看瑪麗·雪萊的同情觀
景先平 馬 艷
瑪麗·雪萊是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時期重要的小說家,其小說《弗蘭肯斯坦》作為“第一部現代意義的科幻小說”自1818年出版后,被翻譯成一百多種語言,并改編為多個版本的戲劇和電影。《弗蘭肯斯坦》廣泛涉及到19世紀英國社會倫理道德、哲學、科學、文學和教育等重要領域。自問世以來,《弗蘭肯斯坦》一直備受國外研究學者的關注,而國內自1982年有了中文譯本后,學者們逐漸開始了對它的研究。從創作背景到創作意圖、文本到體裁歸屬、文學理論等的研究層出不窮,但對瑪麗·雪萊的同情觀鮮有論證。本文以《弗蘭肯斯坦》的敘事視角和英雄人物為中心,圍繞“同情”這一主題,揭示作家獨特的同情觀
一.視角同情
英文中的sympathy一詞源自希臘文,其拉丁文為sumpathes,意為同情或相互同情。所謂“視角同情”,就是通過某個主要人物的視角進行的敘事,使得閱讀者對持有這個視角的人物產生的道德同情……一般而言,視角同情現象在第一人稱敘事中十分鮮明。”[1](51)
《弗蘭肯斯坦》采用了套盒式的敘事結構,第一人稱敘事的三個男性敘述者,航海家沃爾頓、弗蘭肯斯坦及他制造出的無名的怪物。小說的敘述者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對自己、家人、朋友及社會的同情。
小說開端,讀者通過沃爾頓寫給薩維爾夫人的信件,了解到他立志獻身航海探險事業的決心,當讀到“我孤身一人連個朋友也沒有,當我因成功的激情而容光煥發時,無人來分享我的喜悅,倘若失望向我襲來,也不會有人在沮喪中給我支持,替我解憂...我希望有個可以得到共鳴的知己,他的目光可以回應我。”【2】(5)讀者心中頓生同情感。也正是通過沃爾頓的敘事,讀者和沃爾頓幾乎同時認識并逐步了解弗蘭肯斯坦。“他的四肢幾乎已經凍僵了,身子因備受勞累和苦難的折磨已經極端地衰弱了。我從未見過有誰的境遇有如此凄慘。”弗蘭肯斯坦的英明博學和高雅教養讓讀者和沃爾頓對他充滿了同情和憐憫。“看到一個心地如此高尚的人被苦難毀滅,多么令人難受啊。[2](15)然而,沃爾頓的同情被拒之門外,“對你的同情,我深表感激,但這已無濟于事。”[2](19)小說結尾處,沃爾頓與怪物的交談中,怪物的自責和悔恨加深了讀者對他的同情。
怪物的敘事是故事的核心。當讀者走進怪物的內心世界后,對他產生了更多的憐憫和同情。他內心渴求同情和愛。他自詡“生來情深心慈”[2](195),造物主無情的拋棄、村民們厭惡毆打等等痛苦的經歷并沒有泯滅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學會了人類的語言文字,了解了人類地理、歷史、文化、法律等。任何有靈性的人都想變成高尚的人。怪物在成長過程中傾心愛戴和想要結交的也是一個沒落的受到冤屈的貴族之家。當他目睹德拉賽一家“相敬相愛,彼此呵護同情”,他發自內心對他們的不幸表示同情。但他的出現并沒贏得德拉賽一家的同情,“他們見到我時那種驚恐萬狀的表情,有誰能加以描繪?阿加莎立即暈倒了,莎菲也顧不上照看女友,自己轉身沖出了屋子。只有費利克斯...暴跳如雷,猛然把我推到在地,并且用手杖狠命地抽打我。”[2](109)“我發覺周圍沒有誰會對我表示同情,心里真是恨不得把林子里的樹木統統連根拔起,把周圍的一切全都摧毀踏平,然后再坐下來欣賞這一片廢墟。”[2](110-111)在極度絕望時刻,怪物在急流中救起一位少女,然而人類對他以怨報德。渴望獲得人類愛和同情的怪物要求弗蘭肯斯坦為他創造一個同他一樣的伴侶,“只要我和一個同類兩情相悅地一起生活,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來身上的美德”[2](122)。怪物與他的交易并未成功,因為弗蘭肯斯坦表明為了人類的利益“不能同情他”[2](122)在弗蘭肯斯坦死后,怪物徹悟“我決不會博得同情...而我卻是孤苦伶仃”[2](196-197)。
《弗蘭肯斯坦》中怪物被創造者拋棄、被社會唾棄,故事情節戲劇性地展示了社會同情的失敗,然而,從浪漫主義時期到今天的讀者都對怪物產生了同情和憐憫。在小說中,沃爾頓的北極探險失敗了,弗蘭肯斯坦的醫學冒險失敗了,他創造的怪物的人間體驗也失敗了,就好比在現實創作中,拜倫和雪萊都放棄了,失敗了,而唯有瑪麗·雪萊將鬼怪故事寫出來,成為后世所推的第一部科幻小說。
小說中沃爾頓、弗蘭肯斯坦及怪物所面臨的困境是女性在父權社會無聲的反抗,他們所渴求的同情和關愛,也正是瑪麗·雪萊對親情、友情和幸福生活的憧憬。母親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是著名的女權主義者,而其父親威廉·葛德文則是著名的政治學家與作家。母親離世,父親另娶。自己與已婚詩人珀西·比希·雪萊私奔,父親為此斷絕了往來,她不得不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復仇的幻想,以及離開父親的家與另一個女人的丈夫私奔的罪惡感使她自認為是一個怪物。”[4](54)私奔之后,瑪麗·雪萊猶如其筆下的得不到人類承認的科學怪物一樣,居無定所、四處漂泊,飽受各種來自英國主流社會的非議。多蘿西·胡布勒與托馬斯·胡布勒在《怪物: 瑪麗·雪萊與弗蘭肯斯坦的詛咒》中指出,《弗蘭肯斯坦》中的科學怪物實際上就是瑪麗·雪萊本人的寫照。“在這部小說的寫作中,她遇到了許多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她經歷過艱難困苦的時候……但是去詬病這兩個高大的形象(父親和丈夫),這兩個名義上幾乎是她生命中的上帝的人,她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一個怪物。”[5](220-221)
二.傾聽式同情
細讀《弗蘭肯斯坦》,不難發現英語一詞“sympathy”頻頻出現在小說中。瑪麗·雪萊讓男性敘事者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判斷,不試圖去推斷對方的意圖,和讀者一道以真誠的態度去聆聽、體會他們的真實感受。“傾聽”就是一種同情,一種人性的美德。
小說中的怪物無法得到人類的同情和關愛,那是因為眼睛被致命的偏見蒙住了。弗蘭肯斯坦因怪物丑陋面目而拋棄了他。“他蠟黃的皮膚那樣的緊張,幾乎包不住皮下的肌肉和血管,缺乏彈性下垂的頭發烏黑油亮,牙齒則像珍珠一樣煞白,可是黑發、白齒還有眼睛、嘴巴湊到一起的樣子更加讓人可憎:眼睛水汪汪,可是眼窩也是一樣水汪汪的顏色,黃得發白,臉色就像已經枯萎的黃色樹葉,兩片嘴唇像一條筆直的黑線。”[2](28)當他邁入人類社會之初,他渴望的是人與人之間平等、親密的交流,然而得到的是蠻橫的歧視、拋棄和摧殘,不得不在荒野中漂泊。
當怪物觀察德拉賽一家的生活時,他“發現老人雙目失明了,可是兩個青年對他的尊敬,世界上再也難以找到。他們對老人非常體貼,非常孝順,而老人對他們則總是在慈祥地微笑。”[2](83)德拉賽一家相敬相愛,彼此呵護同情的生活給了他勇氣和希望。他希望通過老人的努力,也會被年輕人包容。當怪物向這位失明老人傾述時,他得到了老人的同情和理解。“雖然我眼睛瞎了,不能對您的面容作出評判,但聽您的出言談吐,我在心里相信您是真心誠意的。”[2](108)而當德拉賽家人見到他時的表情再次向他證明他仍然是不被接納的“怪物”。
弗蘭肯斯坦與怪物在蒙坦弗特山相見時,瑪麗·雪萊足足用了兩頁來表達怪物對他的乞求,即傾聽他的故事。“那就讓我減輕你的痛苦吧...我可以讓你不看到你所討厭的東西,你還能聽我說話,對我抱有同情。”[2](73)弗蘭肯斯坦的傾聽讓他萌發了憐憫之心,甚至打動了他。”他的話對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影響。我同情他,有時甚至想寬慰他幾句,但是我的眼光一接觸到他,看到那堆不堪入目、能張口說話的行尸走肉,就直惡心,憐憫之情馬上變成嫌惡和憎恨。”[2](121)當他用心傾聽時,心生同情;但當他用雙眼望著他時,心生恐懼。
瑪麗·雪萊在描寫小威廉遇見怪物時也用到了“捂住眼睛的手”。“他一看見我的容貌,馬上用雙手捂住眼睛”,而怪物認為孩子未染上任何社會偏見,想把他培養成為朋友,本能地拉開了他的雙手,乞求:“聽我的話,我不會傷害你。”[2](116)而小威廉沒法拋棄社會的偏見,強烈的憎惡感讓他成為第一個犧牲品。
當沃爾頓發現怪物在弗蘭肯斯坦尸體旁悲嚎時,他“不由得閉上眼睛”[2](194),“不敢再正視他。他那副丑陋的面容讓人感到說不出的恐怖。”[2](195)怪物的自省讓沃爾頓幾乎忘記了朋友的臨終囑托,而沃爾頓的傾聽讓怪物完成了自焚前痛苦的表白。
在《弗蘭肯斯坦》結尾,沃爾頓北極探險失敗,弗蘭肯斯坦復仇路上猝死以及怪物自焚。讀者既為他們的命運表示同情,又由衷感嘆瑪麗·雪萊對社會倫理的探討。
三.結論
在文本解讀時,解讀者和讀者只能懷著與文本作者進行同情性的溝通的思想,盡可能拋卻自身的偏見,以寬容、興趣、關注的態度沉浸在文本中,體會作家所要表達的意思。瑪麗·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通過同情視角和英雄人物悲劇的設置打破了浪漫主義時期的英雄中心主義,喚起了人們對他者的認同和接受。當我們根據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框架對他人進行判斷和評價時,其實早已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筑建了厚厚的壁壘,將彼此永遠阻隔在自己的心門之外,而無法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更談不上對彼此的信任、互助。航海家沃爾頓最終放棄了繼續冒險,一意孤行的弗蘭肯斯坦在疲憊的復仇路上死去,罪孽深重的怪物自焚,他們從唯我、孤獨的世界中帶出,走向與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中。瑪麗·雪萊的同情觀是建立在與他者共在的世界,通過與他者心靈、情感、意義的交往、交流,表達同情和認同,達到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