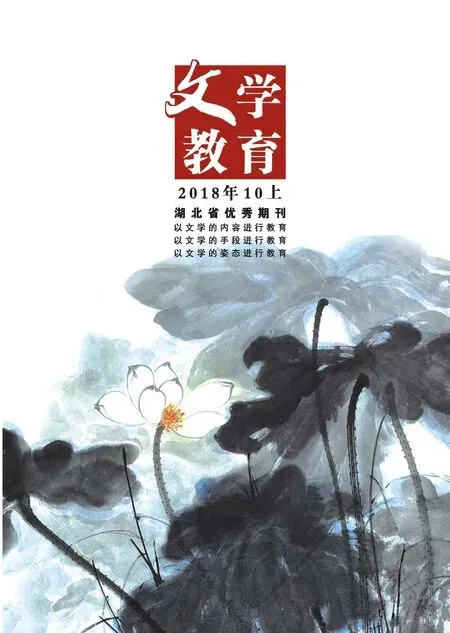評柴紅梅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
劉 偉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顧和總結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百年歷程意義重大,有許多值得重新思考和再次探討的課題。二十世紀日本文學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滲透著深刻的戰爭記憶和殖民體驗。
日本評論家川村湊犀利地指出:“極端一點地說,在日本的近代文學中,不可能存在與‘戰爭’和‘殖民地’無緣的作品。‘戰爭’與‘殖民地’成為文學作品的主題、素材、舞臺和背景。”[1]605二十世紀日本文學不僅有根據戰場體驗創作的紀實性和記錄性的“戰記文學”,也有大批“筆部隊”作家根據戰爭體驗或戰地采訪炮制的鼓吹軍國主義的“戰爭文學”,以及戰時和戰后根據殖民地生活體驗創作的“殖民地體驗文學”、“返遷體驗文學”,還包括很多作家創作的“紀行文學”,也包括戰后眾多戰爭體驗者和曾經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創作的回憶錄、再訪記,以及與那段“戰爭和殖民”的歷史相關的詩歌、戲劇、隨筆等各類文學作品。除此之外,即便一直生活在日本本土、從未有過戰場體驗和殖民地體驗的作家們,也不可能脫離近代以來近80年的日本侵略與殖民歷史的大背景,他們的文學都會以各種不同的表現與戰爭和殖民關聯。
而柴紅梅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正是從城市化進程中的大連都市空間與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密切關系入手,運用文化研究理論以及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在戰爭與文學、都市文化與文學、殖民地空間與文學等諸多相互關聯的語境中,再現和還原了大連的日本文學創作的歷史情境,管窺和透視了日本文學者在大連時的生活狀況、文學活動與內心世界,揭示了長期被遺忘和被遮蔽的日本近現代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深入地挖掘、整理、研究和宏觀把握了歷經近百年的被塵封的大連日本文學,為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二十世紀日本文學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從而促進和推動了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
著名學者王向遠教授這樣評述這部專著:柴紅梅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是“關于日本對華殖民侵略時期中日文學關系的一部重要著作”。“研究日本文學與中國都市之關系,可以從日本文學的中國都市題材中發掘其史學價值、發現其文化價值,彌補傳統史料描寫記載的不足,促使文學與史學的互溶互滲。同時,矯正一般文學史只記載和分析所謂‘名家名作’的偏頗與不足,將那些用純文藝學的角度看可以忽略、而用文化學的眼光看卻頗為重要的作品,納入文學研究及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因而也有重要的文藝學與美學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說,《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具有方法論意義。”[2]87全書從不同角度,通過塵封已久的史料與文本的發現與挖掘,全面揭示了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的復雜關聯,呈現了中日文學關系中的特殊的一面,產生了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
柴紅梅在《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中這樣描述大連:“大連,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背景和文化積淀的城市,她雖只有百年歷史,但卻飽經風霜,歷盡滄桑,很多地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歲月印記和精神遺存,在其本土文化之中浸透著外來殖民統治的歷史與文化。一方面她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活生生的‘見證人’,是在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下,開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并與東亞共同走過二十世紀百年史的都市;另一方面,它又是在沙俄、日本外來殖民統治和中外文化的交互撞擊和融合中生成和興盛起來的現代摩登都市。由于殖民統治者和殖民文化不同,也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和都市形成歷史的差別,與同樣遭受了外來殖民統治的上海、天津、青島、香港和澳門以及東北的其它城市相比,大連這座城市被賦予了迥異于這些城市的特殊性。”[3]39
正是由于大連這座都市具有其他城市所沒有的獨特性,因此也凸顯了其在研究日本近現代文學與中國都市關系時的歷史與文化的價值所在,內在規定了考察日本作家文字所描述的言語都市和這座城市所孕育出的文學現象,以及對戰后日本文學格局影響的重要性。正如專著中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的關系研究可以使我們揭開塵封在歷史彼岸里無數的記憶,這種記憶并不是政治家、外交家陳述的外交辭令,而是隱藏在教科書和歷史學家所闡述的公共認識背后沉睡著的個人體驗記憶。脫離這些鮮活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將會漸漸地模糊、消失、被遺忘的親歷者‘個’的體驗,歷史將不會體現出一個真實的全貌,日本近代文學也將不會是一個完整的文學組成。”[4]39
柴紅梅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把日本文學創作與曾經的日本殖民地都市大連的關系,置于整個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宏大框架之中加以考量,穿越時光的隧道,深入解讀了中國東北都市大連的文化空間中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挖掘出許多極為珍貴的史料,探究了那些能夠反映日本近現代文學、抑或說具有二十世紀日本文學本質屬性的問題,再現和還原了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殖民地都市空間中“摩登與落后”、“浮華與破落”、“富貴與貧賤”、“剝削與被剝削”、“幸福與痛苦”、“生存與死亡”等各種矛盾糾纏的真實面影,并深入細致地探究了以這樣的矛盾對立的大連都市為舞臺和背景創作的日本文學與都市密不可分的關系。如日本現代主義詩歌的發生、充滿“國際野趣”的偵探小說、風格迥異的返遷體驗文學、滿含故鄉與異鄉悖論的戰后大連“追憶文學”等等。
其次,這部專著緊緊圍繞近代城市化進程中的都市大連與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密切關系,不僅把日本文學置放于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縱向的精神辨析與歷史把握,而且將其納入大連這座都市空間和聲光電化世界之中,從眾多方面,全景的筆觸構建了一個言語的大連都市,展現了一個多維、立體的大連,挖掘出日本作家文學創作和大連記憶的情感基礎與這座城市割舍不斷的精神聯系,揭示了日本作家的孕育與成長的風土根基。與此同時,還特別強調指出,在燈紅酒綠、光怪陸離的現代摩登背后中國人的生活困境和悲慘命運,透視出繁華背后的壓迫、剝削、死亡和痛苦,這無疑也是日本作家作品批判意識的來源。不僅如此,作者深入解析、扣問日本作家個人的情感體驗和痛苦記憶與民族罪惡的歷史反省糾纏在一起的精神苦痛和多重復雜心理表現,將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和殖民統治緊密相連,使這一時空中產生的日本文學呈現出更加復雜、深刻與沉重的一面,這一充滿“心靈辯證法”的挖掘,無疑深化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除此之外,柴紅梅還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恰如其分地運用了政治地理學和都市空間理論,客觀審視和深入探究地緣政治、空間生產、權利博弈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揭示出在二十世紀殖民擴張的背景下,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和殖民統治對大連地理空間的擴張和城市空間的生產,從而構建起充滿浮華的幻影都市空間。然而,空間虛像的背后,顯現出的卻是民族壓迫與殖民統治的殘酷。在這種極富穿透力的目光下,作者以犀利的筆觸勾勒出一幅都市空間中殖民者的天堂與被殖民者的地獄并存的真實圖景。而這一交織著社會性、歷史性、政治性、現代性、殖民性的殖民地都市空間,以及內存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對立中的與生俱來的矛盾沖突,給日本作家帶來了銘心刻骨的體驗,催生了日本作家自我的發現、空間的發現和民族的發現,激發了日本作家政治地理學式的文學想象。而日本作家們滲透著濃厚的殖民主義思想的文學書寫又破譯、再生、重構了殖民地政治地理空間。然而,隨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些一向以“高等民族”自居并愉快地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人,頃刻間,作為殖民者的一切權威和特權全部喪失,同時作為歷史的罪人被生他養他的那塊土地拒絕和放逐。空間的喪失和精神家園的喪失,致使這些日本人飽嘗了漂泊與流浪的哀痛,雙重喪失的苦惱和自我身份否定的無奈與悲憤都化作了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進行猛烈批判的原動力和文學創作的驅動,從而創作出了大量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經典之作和集大成之作,在戰后日本文學史上占有無法撼動的重要地位。而這些文學都不約而同地傾訴著“故鄉與異鄉”的迷茫、“身份認同”的糾葛、“精神家園”的喪失、“生與死”的拷問、“懷疑一切”的思想主題,這其中就包括了眾多大連題材的日本文學。
柴紅梅的《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從都市空間、都市文化、政治地理學視角探究其與文學創作的關聯,揭示了日本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罪惡,追問曾為日本殖民地的都市大連對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影響,確立了大連題材的日本文學在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賦予了“二十世紀日本文學與大連”的關系研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切實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