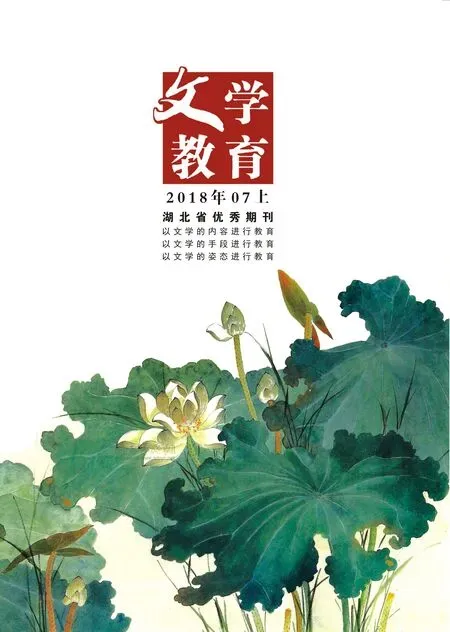阿城《棋王》人物形象的塑造
章佳文
小說《棋王》,是阿城的成名作也是新時期“文化尋根”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尋根文學將“根”界定為民族傳統文化,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兩大主流——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能在尋根作品中找到備受認同和推崇的痕跡。阿城自稱《棋王》為“半文化小說”,道出了這部小說的重要特色。小說浸入了作者所感知的中國文化,注重揭示民族文化心理和個性意識,這使他的小說放在新時期乃至整個當代文學中均不失其獨特性。
在《棋王》中,王一生的形象,可以說是儒道合一、文化浸染的精神造型。《棋王》主要魅力來自于主人公王一生,這是一個在歷史漩渦中具有獨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作者將自己的精神理想賦予王一生形象的刻畫,使他的整個人格都富有無限生機的文化精神,他雖以一己的單薄存在,卻顯現出了無可比擬的頑強精神和文化魅力。阿城筆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王一生體現著民族文化精神的試金石,他使一切染上了世俗色彩的人物和行為都黯然失色。
一.《棋王》王一生形象所體現的儒家文化
阿城在王一生這一形象中,凝聚和概括了民族精神最深層最內在的現實關系。《棋王》中展現的是王一生對母親的“孝”與“信”,對朋友的“誠”,對對手的“恕”,還有保持自身內心和諧、寧靜的“義”,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從不同角度讀《棋王》,可以看出濃濃的儒家文化氣息。從《棋王》中我們可以解讀到孔子的“仁”,王一生對母親給他的無字棋“一直性命一樣存著”,所以,他對倪斌將父親的烏木棋送人的行為難以理解;從《棋王》中我們還可以解讀到儒家的“義”,即孟子所倡導的充塞天地間的浩然之氣。他認為“東西好壞不說,是個信物,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自己被用一副棋作了交易,于是拒絕參加比賽;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也在《棋王》中有所表現,比如小說中描寫王一生與人下棋,通常在能預測勝負時即重擺重來,給對方留足面子,不至于輸得很慘。即便是對待區賽的冠軍也是如此。從《棋王》中我們還可以解讀到儒家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朋友真情,比如阿城對來看望自己的僅有一面之緣的王一生盛情款待,將自己一個月的幾錢油全部提出,甘愿一個月只領生菜,不領熟食。著實讓人體味到那種不夾雜任何虛偽、功利的熱情;王一生癡迷下棋,但當他知道“腳卵”為了讓他參加象棋比賽,送給書記一副家傳的名貴象棋時,他立刻決定不參賽了:“這樣賽,被人戳脊梁骨。”可見,他是一個看重自己脊梁骨的人。王一生的呆癡、淡泊并非對現實的不屑一顧,他除了在棋中追求精神自由和自身理想、人格的實現之外,并不排除人格和自身價值在現實之中的實現。關鍵時刻,他的執著、頑勇就表現了出來。在九局連環、車輪大戰時,他下棋已經不僅僅是尋“異人”,求“養性”了。他仍然那么安然,“把手放在兩條腿上,眼睛虛望著”,但卻已經擺開決戰的架式“拼了”,其正把命放在棋里搏,這時的“安然”里,有火,有鐵,成為“鐵鑄一個細樹樁”。這行為是作品里王一生惟一的一次壯烈,也是一次必然的壯烈。在九戰九捷之后,他終于喊出:“媽,兒今天明白事了。人還要有點東西,才叫活著。”這是他潛在的創造欲、實現欲的升騰和發現。車輪大戰中,他力戰九雄:“孤身一人坐在大屋中央,瞪眼看著我們,雙手支在膝上,鐵鑄一個細樹樁,似無所見,似無所聞,高高的一盞電燈,暗暗地照在他的臉上,眼睛深陷下去,黑黑的俯視著大千世界,茫茫宇宙。”[1]他意志集中,如癡如醉,堅韌沉著。為比賽,王一生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智慧、謀略和精力。從王一生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歷史上一些儒者的影子,在現實生活中,王一生絕少實際的功利目的,在物質條件極端匱乏的狀態下仍能滿足,自得其樂,頗有幾分“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室而不改其樂”的君子氣度,就像那“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為棋不為生”,只要得到最低生理欲求,就一個身心地沉浸在象棋的精神世界里。可見,王一生的形象,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原型”人物形象,這種“原型”形象,暗示了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景仰尊奉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圖樣——在惡劣的外界環境和身不由己的物役交迫中,不合作,不隨俗,出污泥而不染,在更高的精神世界中尋求活潑靈動的生活力量和生命意趣。
認真品讀阿城的小說,可以感受他所推崇的儒家文化所建立的社會基本規則、道德理想和倫理,譬如“信用”、“助人”、“尊重隱私”、做人“最起碼的教養”等,都是文化傳承中的“常識”,作者信手拈來,加入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這些也是他讀雜書所形成的“知識結構”的價值核心,進而成為小說文本的價值核心。
二.《棋王》王一生形象所體現的道家文化
在《棋王》中,我們還可以解讀到作者力圖通過人物的形象來展示的一種文化精神,即中華民族傳統的道文化精神。阿城是一位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作家,這在他的作品《棋王》里尤為明顯,王一生是阿城在作品中著力刻畫的人物,是一個深刻體現了道家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作者通過這一形象表明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思考。王一生身上的道家文化特點主要體現在他的人生態度上。
在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的形象里,我們看到了道文化的“易于滿足”以及“虛靜恬淡”的心境。由于中國人長期受“民以食為天”的觀念的影響,所以對吃飯問題特別重視。《棋王》中有大量的筆墨來寫王一生的吃。下棋是王一生的精神寄托,而吃飯則是他的物質追求。但王一生追求的吃,并非“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在他看來只要有東西填飽肚子,吃的問題就可圓滿解決。農場里生活很苦,每人每月只有五錢油,幾乎頓頓都吃清水南瓜和清水茄子,這是一般人難以忍受的。但因頓頓有米飯可吃,王一生覺得很滿足:“不錯,真的不錯。”“我挺知足,還要什么呢?……人要知足,頓頓飽就是福。”他認為有飯吃就是福,就該知足。在作者筆下,王一生的吃和吃相都被描繪得相當精細:“有時你會可憐那些飯被他吃得一個渣兒都不剩,真有點慘無人道”。他“吃得很快,喉節一縮一縮的,臉上繃滿了筋”。阿城津津樂道地寫王一生的吃,吃為身體的必需,棋為精神之必需,二者都是對自身的一種修煉。《棋王》里,人物的生存需要往往與客觀社會環境處于不協調狀態,在他身上,一個“吃”,一個“下棋”,一個物質生活,一個精神生活,二者的統一象征著整個人生。無論社會歷史條件何等荒謬,它終歸抹殺不了人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基本要求,對王一生來說,只要有飯吃,有棋下,他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就完全得到了滿足。《老子·儉欲第四十六章》中曾寫道:“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說:禍患沒有大過不知滿足的了;過失沒有大過貪得無厭的了,所以知道滿足的人,永遠是滿足的。可見,王一生對吃的容易滿足,是受到了佛道文化的影響。
在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的形象里,我們還看到了道家文化的“曠達、通脫”。王一生天生柔弱,象棋成了他平衡自我的憑借,他近乎癡呆,在生活艱難之中,在神州大亂之時,他不問世事,卻癡迷于象棋,被稱為“棋呆子”。他對棋外的世界漠不關心,象棋是他的靈魂,下棋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外在對應物。“何以解憂,唯有象棋”“長日唯銷一局棋”,他在棋盤里消磨時光、解脫痛苦、超然物外。他的棋“匯道禪于一爐,神機妙算,先聲有勢,后發制人,潛龍治水,氣貫陰陽”,可謂高超。他“為棋不為生”。像王一生這樣的小人物在“文革”浩劫中只能像狂風中的砂粒,下棋在他,只是排憂解悶,以求心靈清凈和精神自由的手段。“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借助象棋,他超越世俗,超越痛苦。他在動亂年月中保持著安命處順的人生態度,享受常人所沒有的心靈自由,他不為外在的貧窮富貴、成敗榮譽而苦思冥想,惡劣的生存環境也不能影響他在心靈自由的天地里追求棋道的提高。在向撿爛紙的老頭兒學棋時,老人的指點使王一生茅塞頓開,領悟到下棋之道的精髓“陰陽之氣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則折……太弱則瀉……若對手盛,則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時,造成克勢。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讓對手入你的勢。這勢要你造,需無為而無不為。無為即是道,也就是棋運之大不可變,你想變,就不是象棋,輸不用說了,連棋邊兒都沾不上。棋運不可悖,但每局的勢要自己造。棋運和勢既有,那可就無所不為了。”[2]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領悟了神秘的拾垃圾的老頭傳授給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義,把棋道和人格融為一體,使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卻能以“吸納百川”的姿態,在無為的日常生活中,不斷提升著自己:他看似陰柔孱弱,其實是在無所作為中靜靜地積蓄了內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為時,內力鵲起,陰極而陽復,他便迸發出了強大的生命能量。最突出的表現是王一生在同九個高手之間的“車輪大戰”中,把全部潛能都發揮出來,取得大勝,在這九局連環大戰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盤托出,與茫茫宇宙氣息相貫通,實現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傳統文化精神在個體身上的再造和復活。
在《棋王》中,作者還寫出了王一生特有的一種徹悟生道的優越感,在火車上,王一生對“我”說:“你哪兒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怎么回事!你們這些人好日子過慣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兒多著呢!”這也使我們看到:王一生身上的道家味是很濃的。這就是《棋王》所寫出的人生真諦。
三.《棋王》人物形象塑造的意義
《棋王》里的王一生是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在阿城的筆下,王一生下棋,棋走道家,在小說文本里,象棋“是一種很高級的文化”,它成了傳達豐厚文化內涵的模具。同時,在儒家積極入世精神支持下,他又精益求精,慘淡研摩,遍求高手以提高棋藝,最后“以一對九”進行車輪大戰來博取“棋王”的美譽,讓我們感受到這個如“鐵鑄的一根細樹樁”的“瘦小黑魂”,身上閃現出一種懾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觸到了被吃制約、壓迫得“很不痛快”的王一生的另一精神層面:生存、溫飽后要求發展,要求生命有燦爛表現和執著的堅毅。而這正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這種精神,在這個窮孩子的精神內核中,爆發出了青春、創造的綠芽,于是才有了一人同時對弈九人的車輪大戰的壯烈場面,這顯然不僅是道家思想,而是儒道文化互滲、互補現象在王一生身上的燦爛呈現。
細讀作品,可以發現阿城筆下的棋王王一生,既有道家的超脫,又有儒家的執著,正如郝銳(2007)所說:“阿城的創作裹著‘道’的外衣,卻有著‘儒’的筋骨。”[3]淡泊與頑勇高度和諧地統一在王一生的生命形態里。在那貌似超脫曠達內里,卻隱藏著儒家的進取精神。《棋王》中的王一生,是傳統民族文化精神的造型。在作者的基本創作動機中,這一形象體現著他的精神理想。所以,王一生有了輝煌的性格歷程。他從一個寒窘無依的“棋呆子”,和棋這種“高級文化”溝通了生命的聯系,由消愁散懷,到凝神忘我,參禪入道,在車輪戰中力勝九名高手,終于由棋呆子而為“棋魂”,致使中華棋道不衰。他以自身的力量,步入精神的高峰,蕩氣回腸,令人震嘆。這作為一種文化理想,一種感情追求,是作者力求實現在作品中的主要內容。阿城寄寓于《棋王》的感情很難分清究竟是現實色彩多,還是理想色彩多。但是作為文化價值觀念的體現,《棋王》無疑是更多地突出著阿城的理想追求。“文學之根應該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4]阿城正是用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來觀照、理解和表現世界的。
在《棋王》中,阿城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鑄造了一代“棋王”,使“棋王”蘊涵了對特定時代個體生命的反思。“棋王”于亂世中的淡定與成功對現實世界個體生命的生存狀態來說,既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啟發。用“棋王”的人生態度反觀現實世界,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的殘缺與生命價值的缺失,也可以感受到阿城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尋求重鑄現代中國國民靈魂的努力。
[1]阿城.棋王[M].作家出版社,1998年.
[2]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N].文藝報.1985-07-06.
[3]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丁帆.中國新文學史: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5]譚解之.文學尋根綜論[J].中國文學研究.1988(1).
[6]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21.
[7]郝銳.天人合一——阿城小說審美世界的文化解讀[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3).
[8]王曉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下卷)[C].東方出版中心,1997.
注 釋
[1]阿城《棋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阿城《棋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郝銳.天人合一——阿城小說審美世界的文化解讀[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3).
[4]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