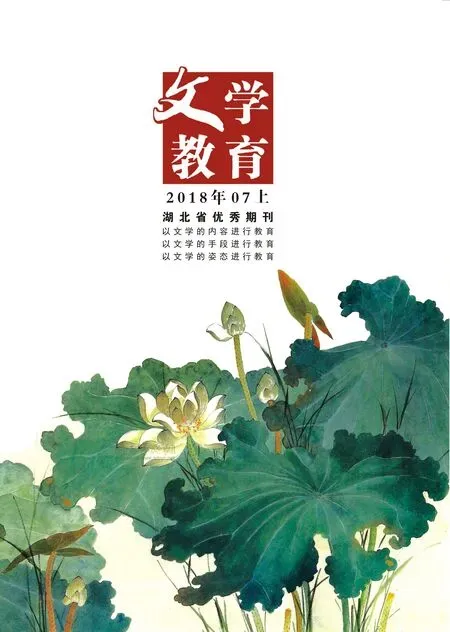試以香草美人意象分析《離騷》的審美價(jià)值
洪馨怡
《離騷》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以其真摯的情感表達(dá)、深沉的思想以及獨(dú)特的浪漫主義審美特征流傳百世。“香草”“美人”意象的出色運(yùn)用是屈原作品的典型特征,詩(shī)篇中以“香草”喻美德、以“夫妻”喻君臣的手法,給人帶來(lái)獨(dú)特的審美感受。
而“審美價(jià)值”是指文學(xué)藝術(shù)滿足人們審美需要的獨(dú)特屬性。本文將從對(duì)《離騷》中“香草”“美人”意象的分析入手,嘗試論述《離騷》的審美價(jià)值。
一.“香草”與美德
《離騷》開(kāi)篇是屈原對(duì)自己生平的自述,講述自己擁有高貴的出身和天賦的良好素質(zhì),同時(shí)又注重后天的修養(yǎng);“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他把江離和辟芷披在身上,把秋蘭結(jié)成佩掛在身邊。江離、辟芷、秋蘭都是香草,帶有芬芳?xì)庀⒌牟菽荆麄€(gè)詩(shī)篇中這樣的香草頻繁出現(xiàn),種類繁多,使得詩(shī)篇仿佛是先秦時(shí)期草木的百科全書(shū)。
為什么屈原要特意強(qiáng)調(diào)佩戴、種植香草的事呢?佩戴香草,使得周身攜帶草木的芬芳,被認(rèn)為是十分風(fēng)雅的;臣子佩戴香草面見(jiàn)君王,也是一種禮節(jié),發(fā)展至后世,便以熏香代之。這與屈原前文所說(shuō)的出身、素質(zhì)與修養(yǎng)相呼應(yīng)。當(dāng)然,“香草”作為一個(gè)典型意象,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讓人不由想起伯夷、叔齊采薇而食的高風(fēng)亮節(jié)。《離騷》中的“香草”,用以喻指高尚的品德與純潔的志趣。王逸的《章句》注說(shuō):“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裳;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屈原在“香草”的意象中寄托了自己美好的愿望,表達(dá)了對(duì)自己的嚴(yán)格要求,他以身外的修飾來(lái)襯托心靈的純潔美好,給人以浪漫主義的“溫”和“雅”的審美體驗(yàn)。
二.“美人”與君臣
“美人”的意象在《離騷》中有兩層喻義,一是喻指君王,二是喻指屈原自己。比起“香草”,“美人”的意象更多地、有意無(wú)意地展現(xiàn)了屈原個(gè)人情感的流露。比如這句,“日月忽其不掩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人遲暮,朱顏辭鏡,恐怕是世上最令人遺憾與悲傷的事。屈原感嘆時(shí)光飛逝,年華老去,自己從與懷王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再到因小人讒言而受猜忌,致使現(xiàn)在漂泊無(wú)依、壯志未竟,以美人遲暮喻自己“英雄末路”,自傷身世之意溢于言表。“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將朝政中的暗流洶涌比作眾女子因嫉妒而中傷美人,隱晦而強(qiáng)烈地表達(dá)了屈原心中對(duì)于小人離間、君臣離心的憤懣與無(wú)可奈何。
在《離騷》中,“美人”還用以喻指君王。《離騷》富于瑰麗而壯闊的想象,引入神話故事,以天馬行空的筆法,將浪漫的想象和懇切的抒情結(jié)合起來(lái);將君王比作神話中的神女,以“求女”喻指求君,表達(dá)自己渴望求得賢明君主的心情。
無(wú)論是以美人喻君還是以美人喻己,屈原將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比作男女之間的求愛(ài)、吸引或是背棄、不忠,不可不謂之精妙。這樣的比喻十分獨(dú)特,也對(duì)后世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典型的例子是朱慶馀的那句“妝罷低聲問(wèn)夫婿,畫(huà)眉深淺入時(shí)無(wú)”,雖無(wú)關(guān)君臣,可其以女子自喻的手法,含蓄而巧妙地傳達(dá)了信息。
三.《離騷》的優(yōu)美與崇高
《離騷》是一部抒情長(zhǎng)詩(shī),給人的第一感受是其遣詞造句的優(yōu)美感。詩(shī)篇中大量運(yùn)用草木鳥(niǎo)獸的意象,以“香草”最為突出,生動(dòng)地塑造了佩戴香草、風(fēng)姿飄逸的“美人”形象。這些意象給人帶來(lái)優(yōu)美的審美感受。“香草”與“美人”,他們的外在表現(xiàn)都是平靜的、和諧的、統(tǒng)一的,屈原描繪出的,是一幅寧?kù)o而壯闊的圖景,他沒(méi)有用激烈的語(yǔ)氣控訴、指責(zé),而是通過(guò)描寫(xiě)優(yōu)美的意象,含蓄地、幽怨地傾訴斷腸之痛。
而在這些優(yōu)美的意象背后,則蘊(yùn)含著崇高的情感與思想。這情感之中,有關(guān)乎個(gè)人命運(yùn)的,被小人陷害、被君主猜忌的痛苦,被流放的孤寂,壯志未酬的不甘;也有關(guān)乎國(guó)家安危的,推行美政的期盼,渴求賢君的愿望。“乘騏驥以馳騁兮,來(lái)吾道夫先路!”“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多么地豪邁而氣勢(shì)磅礴!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屈原遼闊的胸襟與高尚的品德。
“香草美人”的意象與深沉濃烈的情感遙相呼應(yīng),優(yōu)美感與崇高感的碰撞,令人回味無(wú)窮。這也正是《離騷》的審美價(jià)值所在。
《離騷》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yàn)樗且粋€(gè)優(yōu)美的悲劇,是一個(gè)崇高的悲劇。它是屈原用優(yōu)美的語(yǔ)言、崇高的情感所講述的一個(gè)徹頭徹尾的悲劇,也正是這悲劇的力量,使得整個(gè)詩(shī)篇渾然天成、震撼人心。其堅(jiān)實(shí)的理性基礎(chǔ)、豐富的情感內(nèi)涵以及奇幻的想象特征,在文學(xu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郭杰.《離騷》審美價(jià)值的層次分析[J].延邊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2,(80):46-53.
2.袁行霈.中國(guó)文學(xué)史[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