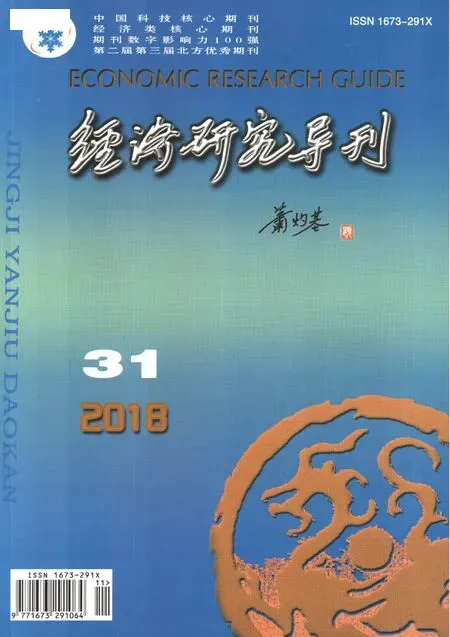農業補貼政策及其實施效果研究綜述
鄧 晨,賓幕容
(湖南農業大學,長沙 410128)
中國的農業補貼政策最早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但政府早期的農業補貼遠遠低于對農業剩余的剝奪。1950—1993年,政府為了發展工業,通過“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領域取走上萬億,農業因此長時間處于“負保護”的狀態[1]。1994—2003年,政府實行保護價全面收購農民余糧的政策,出臺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此時,農業補貼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糧食安全[2]。2004年以來,政府直接補貼的類別逐漸增多,中央也多次通過“一號文件”加大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力度[3]。由農業補貼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央對農業補貼的重視程度正在不斷提高,投入的資金也呈增長態勢。為確保政府支出的質量和效率,學界對農業補貼實施效果的研究也變得豐富起來。
根據已有文獻資料,有關農業補貼的界定、農業補貼政策的劃分、農業補貼政策整體以及良種補貼、糧食直補等具體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將從以上方面對農業補貼政策及其實施效果的研究概況進行綜述,以期對今后我國農業補貼政策及其實施效果的研究做出展望。
一、農業補貼及其分類
(一)農業補貼的界定
有關農業補貼,學界普遍將其界定為政府為了保證糧食等農作物的持續穩定供給而提供給農民的各種形式的支持,包括資金、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大多數學者指出,農業補貼是政府通過財政手段向某些農民以及某種農產品的生產、流通或者銷售環節提供的轉移支付[1~3],是政府及有關公共機構提供給農業生產者的資金援助或者政策支持,主要表現為價格和收入兩種,同時包括其他形式的價格支持或收入補貼等[4]。通常,農業補貼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補貼是政府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所有農業部門的支持及投資,類似于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中的“綠箱”政策;狹義的補貼主要指價格補貼等保護性的補貼[5]。
(二)農業補貼政策的分類
有關農業補貼政策的分類,學界并無統一標準,主要有以下分類。
首先,依據是否直接支付給農民的標準,分為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直接補貼是指按照事先制定的標準直接對農民進行的轉移支付。計算依據多種多樣,主要包括銷售量、產量、價格和以前的面積等。間接補貼即農民間接受益的農業補貼政策,主要用于農產品流通的中間環節,如價格補貼等[6]。
其次,根據世界貿易組織關于農業補貼的相關規定,學者們將農業補貼政策分為“黃箱”“綠箱”“藍箱”政策和出口補貼政策等。其中,“黃箱”政策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措施,包括牲畜數量補貼、農產品價格支持以及種植面積補貼等;“綠箱”政策是指符合“不會對生產或貿易產生扭曲作用”“不屬于價格支持”“由公共基金建立的政府計劃提供”等條件且不會干擾消費價格的財政支出,包括農業的培訓、研究和咨詢等;“藍箱”政策是政府為了限制農產品生產者的過度生產而提供的補貼;出口補貼政策是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提供給本國生產者或出口經營商的資金或者其他財政上的支持[7]。
最后,根據補貼對象的不同將農業補貼分為“五大補貼”和其他補貼。“五大補貼”分別為以優良大豆或小麥品種為主要對象的良種補貼、以湖南等糧食主產區為主要對象的糧食直接補貼、幫助農民購置大型農業機械的農機購置補貼、鼓勵農戶采用環境保護型和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提供的農業技術補貼以及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8~9];其他補貼包括農業稅減免、最低收購價政策等,這類補貼相對于“五大補貼”而言,所占資金規模較小,學者們在研究中也較少提及。
上述研究表明,學者們對農業補貼政策的分類所依據的基礎各不相同,其中主流的分類方法是以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的箱型政策為基礎和以我國政府文件中出現的不同補貼類別為基礎。對于前者,學者們研究重點是在“綠箱政策”的范圍內加大補貼的力度;對于后者,學者們的研究重點是如何提高農業補貼的效率。為了更好地把握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的研究動態,本文將選擇后一種分類方式來進行綜述。
二、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
(一)農業補貼政策整體實施效果
以農業補貼政策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實施效果進行評價,學者們主要從定量、定性兩方面展開。研究結論普遍認為,我國農業補貼政策整體實施效果欠理想。
在定性研究方面,穆月英等(2010)通過理論分析闡述了農業補貼對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提升農業經營者的收入,完善農業經營結構等發揮的積極作用[10]。王玉帥等(2013)通過對補貼數據的橫向和縱向分析發現,我國的農業補貼不僅在實施水平上落后于發達國家,且實施效力也不高[11]。
在定量研究方面,眾多學者從實證的角度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進行了評價,生產函數模型、數據包絡法等被納入進來。錢克明(2003)所構建的生產函數模型,從農民生產成本的降低和農業GDP的增長這兩個角度來衡量“綠箱”政策的實施效果,發現政府通過增加對農村和農業的公共投入,尤其是增加教育和農業科技的投資,可顯著降低農民生產成本并提高農民收入。而在實踐中,政府投入的重心卻是基礎設施建設,這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政府投入的效果[12]。馬愛慧等(2012)通過灰色關聯度評價了2004—2008年間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結果表明,相比于化肥、農藥施用量以及耕地面積,農業補貼與糧食總產量和農民收入的關聯度最低,補貼效果不容樂觀[13]。楊林(2013)采用數據包絡的方法,從規模效益和制度效率兩個層面定量評價了我國30個省的農業補貼效果。結果顯示,16個省有效,14個省無效,補貼效果較好[14]。此外,黃德林等(2010)構建的農業一般均衡模型(CGE)發現,提高農業補貼的力度,增強農業補貼實際的效用對糧食安全至關重要[15]。李維林(2010)構建的一般生產函數發現,近幾年的中國農業補貼與農業發展成正相關[16]。
(二)具體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
有關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農業技術補貼和以及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等具體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學界展開了多樣化的探討,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糧食直補屬于直接補貼的一種,是政府為種糧的農民提供的直接的資金支持。學者們通過模擬分析糧食直補和最低收購價政策對各部門產生的影響,發現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實施會增加糧食和其他農業部門的總產出和最終需求,而對農業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的影響相對較弱[17~18];良種是推動未來糧食產量,改善糧食品質的重要突破口,與糧食主產區相比,糧食作物的良種補貼政策對糧食非主產區的增產有更明顯的貢獻[19];農機購置補貼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可以推進市場的繁榮并間接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對于糧食主產區和非主產區,農機購置補貼的影響在統計上是顯著的[20~21];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是直接向農民提供的政策支持,這一補貼政策提升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確保了糧食種植面積和供給的持久增長、改善了糧食種植結構,總體實施效果較好,但也存在信息采集不準、補貼標準低等問題[22]。農業技術的應用不僅可以保護耕地,還具有增加糧食的產量,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鄧祥宏(2011)等以較大范圍的測土配方施肥補貼政策為切入點,以糧食主產區之一——河南省的四種糧食作物為研究對象,利用DEA模型對農業技術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測土配方施肥補貼在河南省取得了一定成效,該補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23]。
三、簡要評價與展望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直接補貼政策的研究比較豐富,對間接補貼政策少有提及。研究結論普遍表明,我國農業補貼政策的整體實施效果欠理想,但具體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較好。
以上研究成果對提升我國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有關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現有研究成果留下了以下值得探究的空間:在研究視角上,現有研究主要以經濟學為基礎展開,很少涉及其他學科,農業補貼政策涉及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個領域,加強多學科之間的融合研究,拓展出更為多元的研究視角,有助于更科學、更全面地評價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在研究內容上,現有研究主要將農業補貼政策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實施效果展開討論,對具體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的研究相對較少;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偏愛定性研究,采取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比較少。即使采用定量研究,數據來源多半是政府門戶網站提供的數據,使用調研數據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就研究結論而言,采用定量研究的學者們對于農業補貼的整體實施效果持有的態度并不統一,這種不統一可能是由于數據來源、模型選取和數據處理方式的不同而產生的。然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不夠顯著,容易受到研究方法的影響而使研究結果產生巨大出入。因此,有關農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這一領域的研究,無論是在研究視角,還是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仍有較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