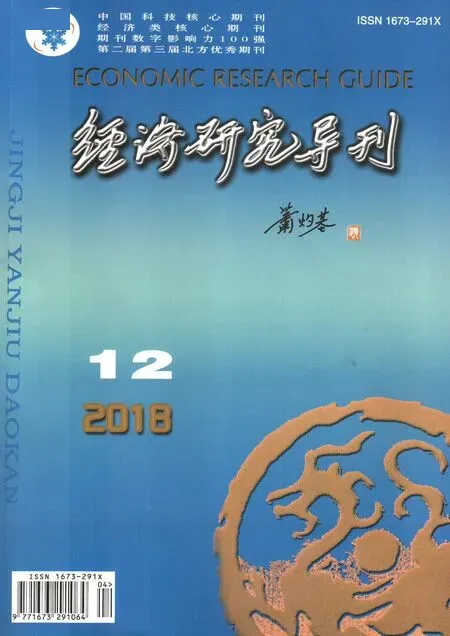中國政府治理的社會資本之維
呂 娟
(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太原 030006)
現代政府治理的本質就是民主協商治理,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關,也是我國政府治理過程中重點關注的問題。目前,我國政府行為法治化和職能市場化均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政府的權力也開始向多中心的自主治理轉變。然而,我國正處于改革的攻堅期,利益格局急劇變化,社會交往過程中誠信、責任、規則意識缺乏,社會信任度低;貧富差距懸殊、腐敗、不公等問題加劇,我國政府的治理水平還有待提高。社會資本是20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跨學科的理論,被西方國家學者看成是解決社會矛盾的“第三條道路”。實踐證明,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與人力資本的個體素質相關,社會資本的質量也影響著國家發展的快慢。社會資本存量豐富的國家,社會發展比較迅速,反之,則比較遲緩。
一、社會資本:政府治理的一種新的理解維度
(一)社會資本的理論演進
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開始于近幾十年,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1980年發表了題為《社會資本隨筆》的一篇短文。在文中,他首次系統地論述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從個體的微觀層面闡釋了社會資本的關系網絡。繼布爾迪厄之后,詹姆斯·科爾曼在其《社會理論的基礎》中,從社會結構的功能出發定義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從微觀層面提升到了中觀層面。
美國社會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將社會資本的概念首次引入到政治領域。在他的代表作《是民主運轉起來》中,他從社會資本與政治生活和民主治理的聯系出發,從宏觀集體的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更為細致的研究,進一步加深拓展了對社會資本的研究。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可利用可再生的社會資源,信任、參與網絡和互惠規范是其主要構成。本書經過帕特南在意大利長期的實踐調研,最終提出引起意大利南北方績效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資本的差異這個重要論斷,社會資本的存量決定著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二)社會資本的構成
本文更傾向于使用帕特南對社會資本的宏觀定義,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由信任、公民參與網絡和互惠規范所構成。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大量的信任存量能夠降低行政成本,最有效地推進政府政策和社會行動的實現;公民參與網絡是社會資本的基礎,它是在人們的相互交往中,為了實現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平等自由的關系網絡;互惠互利的規范迫使人們履行義務,保證人際間的信任,維持社會秩序和發展,是社會資本的保障。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普遍的互惠互利的規范可以減少社會中機會主義的行為,促進信任的加強,而緊密的關系網絡則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提高社會信任的存量,而信任存量的提高反過來又對互惠規范的實現和公民參與網絡的擴大產生積極作用。
二、社會資本與政府治理契合性:相互影響、互補融合
(一)社會資本——保障政府治理順利進行
社會資本的信任、互惠互利的規范及公民參與網絡的積累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地區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對政府治理的參與,社會資本存量的豐富性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政府良好有效治理的順利進行,提高了政府行政治理的效率與人民的滿意度。
1.信任是資本政府治理的基礎。首先,信任可以增強集體行動。當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信任時,就會增強社會合作,基于良好的心理基礎,促進公共目標的實現,增強集體行動和共同利益的實現。其次,信任可以簡化交換關系的復雜性。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社會,非人格的種種程序或制度構成整個社會的基本框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整個社會體系內的復雜性也不斷隨之增加,高度的社會信任可以降低社會風險,減少社會運行的不確定性,保證社會的平穩運行。
2.互惠互利的規范是政府治理的基礎。個體間的人際規范和集體規范是中國社會規范的兩種重要組成部分。人際規范,即人們在交往中所遵從的行為準則,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共同利益而在交往過程中經過反復博弈所形成的規范。集體規范,它是由國家正式制度強制履行的或者是社會文化灌輸的行為準則。這兩種規范的產生與對這兩種規范的遵守都可以既可以加強對正式規則的認可與遵守,也可以促進互惠的非正式的規范的產生,從而擴大社會資本的存量,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
3.公民參與網絡有助于政府治理行為的優化。公民參與網絡可以傳遞信息,降低社會交往的成本,加深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了解,開闊公民對公共領域的視野,促進集體行動與公民的政治參與。
(二)政府治理——社會資本積累的持續動力
良好的政府治理為社會資本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信任的積累、互惠規范的培育,以及擴展公民的網絡參與。現代政府治理就是多中心的協商治理,是公民的自主治理。在協商治理過程中,行政人員可以更加了解民意,公民也可以更好地監督行政人員,保證行政人員和公民之間的有效溝通。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民的積極參與,提高了行政效率,也積累了社會資本。
綜上,良好有效的社會資本存量可以為政府治理產生不同層面的積極作用,而政府治理的順利推進反過來又為社會資本的有效積累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依存。
三、以現代社會資本推進良好的政府治理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它的各個要素都與社會發展和政府治理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資本存量的多少直接影響著一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民主政治的順利推進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改革的攻堅時期,我國的社會資本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階段,現代社會資本的存量不足,有待繼續發展,主要表現為:
首先,社會信任資本程度低。我國的社會資本鑲嵌在一種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的小團體、小規模的結構內部,表現為一種“差序格局”,決定了團體或家族內部的成員表現出對公共精神的一種排他性與狹隘性。“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特點也決定了人與人交往的排他與封閉性,對家族團體之外的成員表現出極度不信任。
其次,公民參與網絡的社會資本不發達。我國由于封建統治長時間存在,傳統社會所形成的垂直網絡還很普遍,與之相應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還很封閉,而現階段我國提倡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二者表現得不協調與不相容。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現階段我國已經出現了一批新的社會組織,但是大部分社會組織還處于初級階段,官辦明顯、資費不足、組織程度低等問題還大量存在,公民參與的關系網絡還有待提高。
最后,互惠互利的非正式規范缺失。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所延續下來的非正式的傳統規范都是為了維護封建階層的統治和利益,不適合現代社會。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這種傳統規范正受到沖擊,但新的適應現代社會的互惠互利的規范還未完全形成,對政府治理和民主政治的建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由此可見,改造傳統的社會資本,培育現代社會資本,使社會資本發揮積極作用,才能提升我國政府治理能力。第一,明確公民權利,培育公民意識,樹立公民精神,使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增加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資本,擴大公民參與網絡。第二,推動公民社會的發育,給予民間組織更大的自主性,擴大民間組織的廣泛性和行動的有效性。第三,加強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設,促進互惠互利的非正式規范的形成,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促使社會資本的均衡性與協調性。
總之,通過市場、民主、法治等現代要素的培育,強化制度教育,規范權力的使用,降低人治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干預,淘汰傳統資本主義中的消極部分,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加強現代社會資本的建設,為我國政府治理的高效運行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動力。
參考文獻:
[1]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李惠斌,楊雪冬.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黃曉東.社會資本與政府治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5]樸長莉.社會資本與社會和諧[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 陳家剛.協商民主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