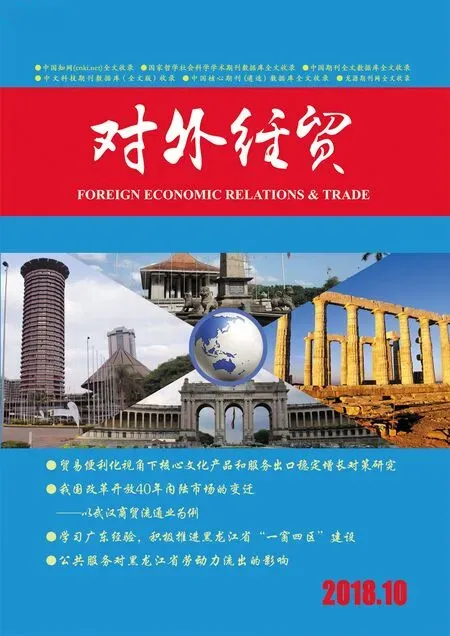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機制研究綜述
朱 琳
(山西大學 商務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一、引言
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指依托一定數量的科技人員從事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活動,取得自主知識產權并將其轉化為高新技術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小企業。2017年,我國政府部門頒布了《科技型中小企業評價辦法》,從而統一了全國科技型中小企業標準。科技型中小企業應符合“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注冊的居民企業,職工總數不超過500人,年銷售收入不超過2億元,資產總額不超過2億元。對于科技人員比例、研發投入、科技成果三項評價指標達到相應要求或持相應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證書,獲得國家級科技獎勵的企業”。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關于傳統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相關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科技型企業因其輕資產、技術轉化不確定性高等特點導致其獲得貸款的途徑匱乏,這一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發結果無法落地,阻礙了其更高實際價值的創造。
二、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機制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在對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及其成因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趙曉雷(1999)指出科技型中小企業難以獲得有效融資的共性原因在于其資本和抵押品不足。王競天等(2001)與秦漢峰、黃國平(2001)的觀點相一致,均認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限制因素有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整體融資體系不完善、融資渠道單調且機制不健全。劉瑞波(2006)則通過對國內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進行研究,認為企業融資觀念落后及融資方式單一導致其融資效果不盡如人意。馬平(2008)指出雖然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性很強,但其研發成果具體估值較難,從而降低了其從商業銀行獲取貸款支持的可能性。黃孟復(2010),韓剛(2012)以及張秋東,李惠青(2016)均認為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更傾向于投向大企業。石慧(2010)在其研究中指出銀行鮮少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的主要原因使風險收益錯配。馬潤菲(2014)與奚賓(2016)從政府角度出發,指出政府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的支持力度還不夠,已有政策支持體系不夠豐富且實際運用效果不理想。尚慶軍(2014),王美彥(2015)等學者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的信貸配給不合理,也加劇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模式創新對策,費騰(2012)提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科研技術優勢,拓展質押信貸融資模式,加之擔保租賃等模式來豐富間接股權融資市場。金晟(2012)進一步提出商業銀行可以建立專門開展科技型中小企業相關業務的科技支行。趙雅敬(2014)從互聯網金融角度指出,較為成熟的個人網絡借貸的發展經驗,可以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豐富融資渠道所借鑒。張爭美(2015)認為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創新微型信貸服務品種與流程、風險管理、信用評估體系及信貸服務政策來緩解融資現狀。張秋東,李惠青(2016)認為可以加快完善科技型中小企業知識產權評估與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激勵這些企業在產學研相結合的基礎上更大程實現技術的實際應用。陳燕萍(2017)建議科技型中小企業可以綜合運用股權融資、債權融資以及政府相關支持政策等模式實現高效率的融資效果。董建忠、張濤、于麗華(2017)強調了民間資本的重要性,政府可通過規范民間資本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廣闊的選擇范圍,同時指出該類企業也應積極與相關科研院校共同合作,提升科技產品轉化為實踐應用的效率。宋光輝等(2016)、肖蘭華和徐信艷(2017)、藺鵬等(2017)提出了緩解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新路徑,即互助聯合擔保與投貸聯動等。齊岳等(2017)也認為完善投貸聯動模式能夠更加有效地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葉莉等(2017)創新地提出了復合聯保融資模式解決融資困境。李瑞瑞(2018)指出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意愿強烈,可融資模式相對較單一,企業應結合自身所處的不同階段選擇相匹配的融資模式。徐海龍(2018)則主要從建立覆蓋科技型中小企業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政策支持機制角度進行研究。朱媛(2018)在其研究中提出可通過建立知識產權融資服務系統來創新融資機制,同時強調了企業自身融資能力發展與完善的重要性。高曉燕(2018)則從保險服務角度提出創新保險資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幫助其更好地管理各類融資風險。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研究學者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早于國內,通過相關的實證分析,形成了具有應用價值的企業融資理論,其中對企業的融資順序和融資方式的分析也較為豐富。
Weston和Brigham(1981)將企業的生命周期分為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其中又將成長期細分為三個階段。他們指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企業應采取不同的融資模式。Udell(1998)在其研究中提出一個企業資本結構的優化需要根據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來進行匹配,其并不是一成不變的。Myers and Majluf(1984)認為企業一般會按照內部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融資順序來進行融資,這在其啄食順序理論里有所體現。Liu J.Y.(2008)同樣認為企業融資的優先順序首先是內源性融資、其次是銀行信貸、最后是股權融資。Weston and Brighan(1981)與Kazanjian(1988)的觀點一致,認為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模式也會隨著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更新,每一階段都應選擇最佳的融資方式來匹配其需求。企業生命周期這一概念的應用在Adize(1989)關于企業融資模式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并將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發展與衰退兩大階段。Mallick and Chakrabory(2002)則認為融資需求的差異主要是由于其所處行業、企業發展階段和組織形式不同。
Stiglitz and Weiss 等(1981)認為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劇了其融資窘境。大型銀行因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不易獲取,因而更傾向于給大型企業提供信貸服務。Latimer Asch(1985)則指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因邊際成本高而難以滿足其融資需要。Latimer(1995)則主要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指出其由于輕資產、規模不大、科技產品估值困難等原因導致難以從商業銀行獲得足夠融資。Berger and Udell(1998)在其研究中發現個人投資、銀行貸款及商譽質押是美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Thorsten Beck(2003)分析指出擔保、租賃等模式可以促進企業外部融資渠道更加豐富,從而更大程度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Laconic(2007)提出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能夠更好地服務于企業融資需求。Miguel Meuleman,Wouter De Maeseneire(2012)從政府補貼角度分析了科技型小企業的融資狀況。其研究指出許多國家將大量的公共資金用于研發,以緩解小企業創新項目的債務和股權缺口。同時,能夠獲得政府的研發補貼對于創新型中小企業來說體現其公司價值與良好信譽的窗口,因此更容易獲得長期融資。Neil Lee,Hiba Sameen,Marc Cowling(2015)重點研究了英國中小企業在不同經濟周期的融資狀況,研究結果指出科技型企業本身很難獲得融資,在經濟危機時期,這一難度顯著提升,尤其是絕對信貸配給狀況堪憂。三者認為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的結構不夠合理,從而很大程度限制了科技型企業的融資獲取。Ibidunni和Kehinde(2018)以尼日利亞科技型中小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了融資策略、創業能力和業務增長之間的關系。通過定性與定量分析,指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可以通過風險資本與企業捐贈的融資方式有效提升其公司收入。同時,這些企業還可以依靠創業能力的提升來增加獲取融資的機會。
三、總結及研究展望
綜合國內外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模式的相關探討,可以看出大多數研究都主要側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原因及解決途徑、融資方式及效果、信貸融資影響因素及融資建議及對策方面。在我國,由于金融市場體系不夠完善,政府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制約以及科技型中小企業自身因素等原因導致其融資渠道不通暢。在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過程中,關于中小企業生命周期對融資機制選擇的指導與影響的相關研究甚少,大多側重于內源融資、外源融資的分析,因而使其融資困境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因此,更為細致地根據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來創新符合其每一階段特點的融資模式變得尤為重要,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顯得更為迫切,以豐富現階段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從而更有效地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助力我國經濟更加高質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