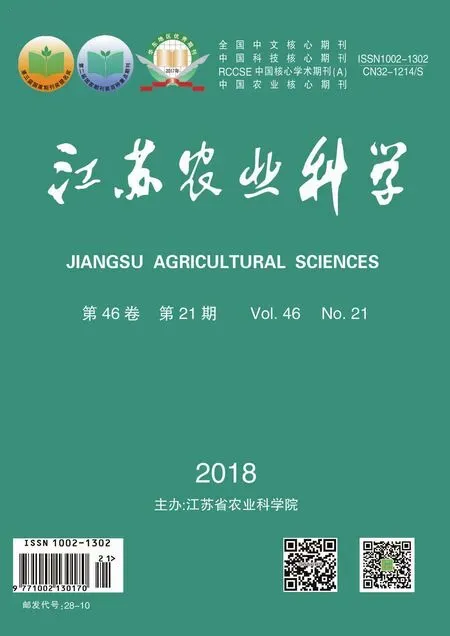太湖流域湖蕩濕地有色溶解有機物特征分布與來源解析
王 青, 潘繼征, 吳曉東, 馬書占, 陳丙法
(1.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湖泊與環境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南京 210008; 2.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3.湖北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湖北黃石 435002)
有色溶解有機物(CDOM)是水中含有腐殖酸、富里酸、氨基酸和芳香烴聚合物等物質的一類可溶性有機物,是水體中溶解有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1]。由于有色溶解有機物在可見光和紫外光區有吸收作用,其濃度和成分變化對水下光強及初級生產力有重要影響。一方面有色溶解有機物能吸收有害紫外輻射,保護水生生物并通過光漂白作用將有機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物質給水生生物利用;另一方面,水體中CDOM含量過高不利于陽光穿透水體,降低水體初級生產力[2-3]。同時,CDOM還影響著化學反應物的形成和金屬物質的遷移[4]。近年來,新興的三維熒光光譜(EEMs)熒光分析技術以操作簡單、靈敏度高和選擇性好等優點被廣泛應用于CDOM的研究分析中。平行因子法(PARAFAC)因具有解析CDOM的EEMs圖譜,定性、定量描述CDOM的組分特征等優勢,已被廣泛運用到水環境CDOM熒光特性描述、來源解析等研究中[5-6]。程慶霖等利用平行因子法揭示了滇池有色溶解有機物組分分布特征[7]。Kowalczuk等采用PARAFAC解析了南大西洋海域CDOM組分,鑒別出3種陸源類腐殖質、1種海源類腐殖質和2種類蛋白物質[8]。
太湖流域是長三角的核心區域,流域內湖蕩濕地密布。湖蕩濕地作為河-湖水系聯接的關鍵節點,不僅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對太湖流域污染物攔截、凈化水質和維護太湖生態系統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是太湖流域控源減負、“一湖四圈”生態修復的重要一環[9]。Dong等對長江中下游16個湖泊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湖泊尺度與有機碳的累積速率成反比,小型湖蕩濕地在水質改善方面的作用應當得到重視[10]。目前太湖流域多數湖蕩濕地面臨許多生態問題,例如水體污染負荷水平較高,富營養化趨勢加劇和生態退化嚴重。CDOM是影響湖蕩濕地水體光照的重要因子之一。近年來,張運林等通過野外和室內試驗研究了藻類降解對太湖CDOM的貢獻,同時對中營養湖泊天目湖進行了研究,識別出類腐殖質及類蛋白質組分[11-12]。劉明亮等研究了2007年夏季太湖入湖河口和大太湖開敞區CDOM濃度及來源[13]。黃昌春等基于三維熒光和平行因子法研究了太湖水體CDOM組分光學特征[14]。王書航等研究了蠡湖CDOM的分布及來源,發現水體中CDOM主要是類色氨酸和類腐殖質2個熒光組分[15]。綜上所述,對太湖流域水體中CDOM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礎,但對湖蕩CDOM整體分布及來源解析還缺乏系統研究。因此,本研究選取太湖流域不同營養水平的代表性湖蕩作為研究對象,運用PARAFAC解析EEMs圖譜,結合水質參數分布情況,揭示太湖流域湖蕩濕地CDOM的分布特征及來源,以期為太湖流域湖蕩濕地的污染生態修復提供基礎資料和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太湖流域湖蕩濕地(30°28′~32°15′N、119°11′~121°53′E)位于長江三角洲南緣,整個流域三面瀕江臨海。太湖流域水網縱橫,湖蕩眾多。整個流域總面積約為735 km2,大于 0.5 km2的湖蕩有189個,占流域平原面積的10.7%。太湖流域湖蕩濕地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歷來具有養殖、航運、灌溉等基本功能,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興起,湖蕩濕地周圍旅游資源也相繼得到開發。
1.2 采樣點設置
選取不同區域、不同營養水平的10個湖蕩,分別為滆湖、長蕩湖、尚湖、昆承湖、陽澄湖、傀儡湖、澄湖、淀山湖、元蕩和宜興三氿,共設置41個采樣點。采樣點位分布見圖1、表1。


表1 湖蕩面積、平均水深和采樣點編號
1.3 樣品采集與分析
1.3.1 水質指標分析 于2015年秋季對太湖流域代表性湖蕩41個樣點進行采集,用有機玻璃采水器采集表層(水下 0.5 m)樣品,裝入1 L聚乙烯塑料瓶中,置于帶有冰盒的保溫箱中立即運回實驗室進行各項指標的分析測定。透明度(SD)用塞式透明度盤測定,水深(h)用水深測度儀測定。總氮(TN)濃度、總磷(TP)濃度、高錳酸鹽指數(CODMn)及葉綠素a濃度測定方法均參照文獻[16]。
1.3.2 溶解性有機物指標分析
1.3.2.1 可溶性有機物(DOC)濃度測定 水樣經GF/F濾膜(玻璃纖維濾膜)(預先450 ℃灼燒4 h)過濾,濾液用總有機碳測定儀(TOC5000A,島津)測定DOC濃度,儀器檢測限為 0.004 mg/L,標準偏差<2%。
1.3.2.2 紫外可見光譜掃描及吸收系數計算 水樣經GF/F膜過濾后再經0.22 μm Millipore膜(混合纖維素酯微孔膜)過濾,用于測定CDOM吸收及三維熒光光譜。將過濾后水樣置于1 cm石英比色皿中,以Milli-Q超純水作為參考水樣,采用可見紫外分光光度計(UV2700,島津)于200~800 nm波長范圍進行光譜掃描,掃描間距0.5 nm。為了消除過濾清液中殘留細小顆粒物的散射,利用700~800 nm波段吸收系數的均值進行散射效應訂正,已校正反射效應以及儀器基線的漂移等因素。利用公式(1)計算CDOM各個吸收波段光譜吸收系數:
a(λ)=2.303×D(λ)/r。
(1)
式中:a(λ)為波長λ的吸收系數(m-1);D(λ)為吸光度;r為光程路徑(m)。
1.3.2.3 三維熒光光譜掃描 采用HitachiF-7000型熒光分光光度計測定三維熒光光譜,儀器光源為150 W氙燈,光電倍增管電壓700 V,激發(Ex)和發射(Em)單色器均為衍射光柵,波長誤差±2 nm,激發波長為350 nm時水的拉曼峰信躁比S/N>250(P-P)。激發和發射狹縫寬度均為5 nm,掃描波長范圍λEx為200~450 nm,λEm為250~600 nm,步長 5 nm,掃描速度2 400 nm/min。通過內置FL Sloutions 2.1軟件減去超純水消除水拉曼散射。
1.3.3 營養狀態指數 基于總氮(TN)濃度、總磷(TP)濃度、高錳酸鹽指數(CODMn)、葉綠素a濃度及透明度(SD)5個水質參數指標分別計算調查湖蕩綜合營養狀態(TLI)指數,計算公式:
TLI(∑)=∑Wj·TLI(j)。
(2)
式中:TLI(j)代表第j種參數的營養狀態指數。富營養化程度分級標準為TLI(∑)<30為貧營養、30≤TLI(∑)≤50為中營養、50
1.4 數據處理
運用Matlab2010a軟件和drEEM_010數據包對EEMs數據進行PARAFAC處理,采用ArcGis軟件對采樣點位分布圖進行繪制,采用SPSS 22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采用Origin 9.0軟件對數據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營養鹽水平
太湖流域湖蕩濕地營養鹽水平差異大。調查湖蕩中TP濃度最低為尚湖,其值為0.028±0.003 5 mg/L,最高為宜興三氿,其值為0.192±0.008 1 mg/L。TN濃度較低為尚湖和昆承湖,較高為宜興三氿和滆湖。而CODMn濃度較低的分別為尚湖[(3.78±0.17) mg/L]、滆湖[(3.83±0.42) mg/L]與傀儡湖[(3.88±0.08) mg/L];DOC較低的湖蕩分別為滆湖[(4.42±0.24) mg/L]、尚湖[(4.55±0.41) mg/L]和傀儡湖[(5.24±2.5) mg/L]。TP、TN、CODMn和DOC分布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P<0.05)(圖2)。

尚湖與傀儡湖水質較好,總體為Ⅱ~Ⅲ類,水生植物發育良好,綜合營養狀態指數均為46,屬于中營養水平;昆承湖、元蕩、陽澄湖、長蕩湖TLI指數分別為56、54、56、57,屬于輕度富營養,水質屬于Ⅳ~Ⅴ類水平;澄湖、淀山湖、宜興三氿和滆湖TLI指數分別是61、61、64和61,屬于中度富營養,其中淀山湖為Ⅴ類水平,其余湖蕩為劣Ⅴ類水平且均是由于TN含量超標(圖2-e)。與已有研究結果相比,長蕩湖水質狀態有較大提升,總體由中度富營養化轉變為輕度富營養,說明對長蕩湖近年來采取的圍網拆除、污染控制、生態修復等一系列治理措施對水質有顯著改善,其余湖蕩整體富營養水平并無太大波動[17-20]。
2.2 CDOM吸收特征與空間分布
CDOM結構較為復雜,通常以a(350)表征其濃度,也有用a(280)表征[21]。調查湖蕩CDOM吸收系數a(280)、a(350)均值分別為(14.26±3.04)、(3.38±0.81) m-1,變化范圍為(9.00~18.80)、(1.76~4.49) m-1(表2)。與已有文獻報道的太湖[22]、天目湖[23]、東平湖[24]等相比,調查湖蕩的CDOM吸收系數處于正常的淡水湖泊CDOM吸收系數范圍內,尚湖與傀儡湖CDOM吸收系數與水質較好的中營養湖泊天目湖[18]、梁子湖[25]取值范圍相近,其余湖蕩CDOM吸收系數與水質較差的洪湖、東湖[25]相似,低于太湖梅梁灣地區[22]。吸收系數a(350)與TLI指數相關性顯著(P<0.05),CDOM吸收系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湖蕩的營養狀況。

表2 太湖流域湖蕩CDOM吸收系數
太湖流域湖蕩濕地CDOM的吸收系數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P<0.05),a(350)較低的湖蕩為尚湖與傀儡湖,吸收系數值分別為(1.76±0.53)、(2.52±0.95) m-1,顯著低于其他湖蕩(P<0.05)。尚湖和傀儡湖水質較好,水生植物發育良好,處于中營養狀態。a(350)最高的湖蕩為宜興三氿,均值為 (4.49±0.17) m-1,可能與宜興三氿是城市湖蕩,水質較差,水生植被較少有關。從單一湖蕩吸收系數空間分布上看,長蕩湖高值分布在西北部湖區和東北部湖區,峰值 3.561 m-1出現在位于西北部34#點。滆湖呈現出明顯由北向南遞減趨勢,其峰值出現在北部湖區25#點(圖3)。輕度富營養湖蕩與中度富營養湖蕩間a(350)并無差異性(P>0.05)。通過點繪a(280)與a(350)的關系,兩者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2=0.902,P<0.001)。
研究表明,CDOM吸收系數與DOC濃度呈正相關關系,利用CDOM的吸收系數可以示蹤DOC濃度的變化[26]。CDOM吸收系數與CODMn、DOC分布規律相似。對調查湖蕩a(350)與CODMn、DOC濃度進行回歸分析,由式(3)(4)可知它們之間存在顯著性正相關關系(P<0.01),說明三者均可作為反映水體有機污染程度的參數。
CODMn=0.794(±0.141)a(350)+2.199(±0.487)(r2=0.46,P<0.001,n=41);
(3)
DOC=0.939(±0.131)a(350)+2.437±(0.450)(r2=0.59,P<0.001,n=41)。
(4)
2.3 CDOM三維熒光特征分析
運用PARAFAC,將41個樣品三維熒光數據(EEMs)分解,得到3個熒光組分(圖4)。組分C1激發波長為250 nm,發射波長為430 nm,對應類腐殖質A峰(230~260、380~460 nm)[27],對比其他研究結果可確定為紫外光類腐殖質,反映的是腐殖質和富里酸形成的熒光峰[21]。組分C2與組分C3較為接近,似內源類蛋白物質,組分C2激發波長與發射波長分別為265、305 nm,對應類蛋白B峰(275、305~310 nm)[27],結合已有研究結果將組分C2確定為類酪氨酸[6,28-29]。組分C3激發波長為280 nm,發射波長為330 nm,對應T峰(280、320~350 nm),反映的是類色氨酸物質所形成的熒光峰,主要是受浮游植物或水生細菌等生物降解的影響[5,30-31](表3)。



表3 三維熒光組分特征
從不同湖蕩之間比較來看,3個組分的CDOM熒光強度之和Fmax值有顯著差異性,尚湖、昆承湖、長蕩湖、陽澄湖、淀山湖Fmax值高于其他湖蕩,分別為(20.48±2.28)、8.88、(5.17±5.28)、(4.53±3.77)、(2.87±0.88) RU。其他湖蕩Fmax均小于 2 RU(圖5-a)。
太湖流域典型湖蕩外源(C1)與內源(C2、C3)對CDOM貢獻率具有差異性,尚湖外源和內源貢獻率分別為2.53%和97.47%,可能是與調查期間尚湖湖區內苦草過多,人工清理過程中造成大量苦草斷裂腐爛降解有關。其余湖蕩內源貢獻率分別為昆承湖(95.77%)>陽澄湖(88.62%)>澄湖(86.96%)>宜興三氿(81.34%)>長蕩湖(80.77%)>淀山湖(79.51%)>傀儡湖(77.43%)>元蕩(75.81%)>滆湖(68.44%)(圖5-b)。由此可知,調查湖蕩CDOM組成內源物質占主導地位。而滆湖和長蕩湖湖區外源和內源對CDOM貢獻率有所差異,滆湖南部湖區采樣點外源物質對CDOM貢獻率接近50%,大多數湖泊CDOM外源輸入以地表徑流為主,滆湖入湖河流西進東出,類腐殖質熒光組分C1由西向東表現出降低趨勢,內源組分熒光強度變化規律則相反,使得湖區西部外源輸入對CDOM組成影響較大,總體而言,滆湖CDOM組成偏內源物質主導。長蕩湖外源物質C1對CDOM貢獻率范圍在2.93%~40.24%之間,各采樣點組分C1熒光強度并無差異性。長蕩湖依賴地表徑流和降雨補水,主要入湖河流為西側的蛋金溧漕河和北河,東部為出湖河流[18]。入湖區域營養鹽水平略高于其他區域,氮、磷輸入使得水體生物代謝迅速,微生物或藻類代謝產物增多,湖區南部和東部內源物質熒光強度高于入湖區域,進一步說明熒光組分C2和C3主要來源于自生微生物、藻類的自生源,而對CDOM貢獻較少的C1可能是入湖河流及兩岸的陸源輸入。通過點繪組分C2與組分C3熒光強度關系,發現二者為極顯著正相關關系(r2=0.996,P<0.001),說明湖蕩內源蛋白物質組成相似,來源一致(圖5-c)。
對CDOM貢獻率較大的熒光組分C2、C3均與TP濃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CDOM與P元素的遷移轉化密切相關,這與蠡湖結論[15]一致。熒光組分C1與葉綠素a濃度呈負相關(P<0.05),代表內源輸入的組分C2與C3與之均未達到顯著水平。而將滆湖單獨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熒光組分C2、C3均與葉綠素濃度顯示出極好的相關性。這可能是由于秋季是水生植物衰亡時期,內源組分受水生植物腐爛影響,尤其是水生植物發育良好的尚湖和傀儡湖;而滆湖水生植被蓋度低,2009年沉水植物覆蓋度不足全湖的1%[32],2010年后,通過滆湖生態修復的開展,水生植被覆蓋度略有提高,但沉水植被覆蓋度依然不足1%,滆湖熒光組分C2與C3可能主要受浮游植物影響。
2.4 CDOM來源的辨識
CDOM來源可按陸源和生物源進行區分。陸源多表現為類腐殖質占主要優勢;生物源表現為類蛋白物質峰占優勢。生物指數(BIX)是指在激發波長為310 nm時,發射波長 380 nm 和430 nm處熒光強度的比值,可用于估計內源物質對水體中CDOM的相對貢獻,反映內源生物活性,在0.8~1.0 之間時,具有較強自生源特征;大于1.0時是生物細菌活動產生[33]。本次調查湖蕩中長蕩湖BIX范圍為0.94~0.99,具有較強的自生源特征,其余湖蕩BIX指數均大于1.0(圖6),說明湖蕩CDOM由生物細菌活動產生。腐殖化指數(HIX)是指在激發波長為254 nm時,發射波長在435~480 nm 與300~345 nm 波段內的熒光強度平均值的比率,該指數可用于估算有機質的腐殖化程度或成熟度[33]。本次調查中采樣點HIX指數范圍在0.10~2.02之間,除長蕩湖外各湖蕩腐殖化指數均小于1.5,長蕩湖HIX指數均值為1.71(圖6)。按Huguet等提出的HIX溯源指標體系評判,所有湖蕩CDOM主要由生物活動產生,腐殖化程度較弱(HIX<4)[33];而Zhang等提出的標準則是1.5 熒光指數(FI)是在激發光波長為370 nm時,熒光發射光譜強度在450、500 nm處的比值,該指數可用來研究和表征CDOM中腐殖質的來源,大于1.9說明主要來源于微生物代謝過程,小于1.4說明陸源占主要貢獻[34]。本次研究中熒光指數均在1.4左右(圖6),與BIX、HIX表征CDOM熒光特性得到的結果不一致,有研究指出熒光指數對腐殖質來源的指示不太敏感[35]。除了以上3個指標可以表征CDOM熒光特性外,還可以用CDOM中類蛋白組分的熒光強度與類腐殖質的熒光強度的比值來判斷水體中CDOM的來源[36-37]。一般認為,比值大于1說明自身源占主要優勢。本次調查湖蕩中,C2、C3與C1的比值在1.07~42.14之間,均值為9.89±1.84,進一步說明調查湖蕩CDOM以內源為主。 太湖流域湖蕩濕地有色溶解有機物(CDOM)光譜吸收系數a(350)在空間分布上差異顯著,且與高錳酸鹽指數(CODMn)和溶解性有機物(DOC)存在相似的分布規律。 利用PARAFAC分析三維熒光圖譜,解析出3種組分,即紫外光類腐殖質熒光組分C1(250 nm/430 nm)、類酪氨酸熒光組分C2(265 nm/305 nm)以及類色氨酸熒光組分C3(280 nm/330 nm)。太湖流域湖蕩外源(C1)與內源(C2、C3)對CDOM貢獻率具有顯著差異性,各湖蕩內源物質(C2、C3)對CDOM熒光強度貢獻率分別為尚湖(97.47%)>昆承湖(95.77%)>陽澄湖(88.62%)>澄湖(86.96%)>宜興三氿(81.34%)>長蕩湖(80.77%)>淀山湖(79.51%)>傀儡湖(77.43%)>元蕩(75.81%)>滆湖(68.44%)。 太湖流域湖蕩CDOM主要以內源生物降解貢獻為主,熒光指數BIX、HIX及類蛋白組分與類腐殖質的熒光強度的比值也顯示相同的結果。

3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