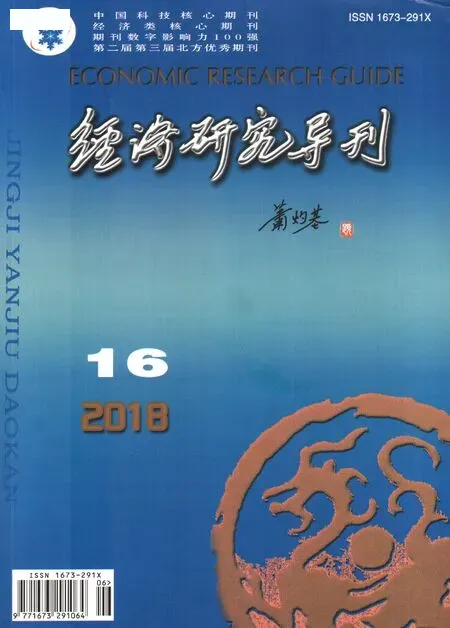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問題與對策
方素清
(西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蘭州730124)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把推動農村地區的繁榮和穩定擺在全黨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農村深化改革穩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成績斐然,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農村發展也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尤其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存的邊疆民族地區農村,這些問題和困難更加復雜,這無疑給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主要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眾所周知,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政府、市場、社會等各個層面的治理,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和協同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社會治理。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黨和政府將社會治理視為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要求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實現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2]邊疆民族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輻射中心和重要的安全屏障,其長期處于西方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和攻擊之下,而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是邊疆民族地區環境較為封閉,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地方,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反滲透、反分裂的前沿陣地,加之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問題的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問題錯綜復雜。與之相聯系,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
1.系統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不是雜亂無章的、支離破碎的“碎片化”治理,而是一項結構嚴密的系統工程,其中經濟、文化、宗教、生態環境等各個要素是緊密聯系和相互影響的。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也不是孤立的區域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一個重要因素,必須以系統優化為前提,結合國家治理體系下的其他治理,共同發揮作用,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2.整體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不是針對某一民族、某一區域,而是整個農村。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性就體現在,從全局的高度來審視和解決問題,在總的規劃下,將局部層面的社會治理統籌起來,使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由分散走向集中,從而全面推進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
3.差異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差異性主要是由文化的多樣性而致的。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少數民族眾多,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或宗教文化。在多樣性思想文化的長期影響下,不同的民族對于一些問題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存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因而也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因此,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在統領全局的前提下,必須要差別化對待,靶向治療,提高社會治理的效率。
4.協同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雖然存在著多樣化的利益主體和利益追求,但是無論是政府、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或個人的治理行為,都是從同一問題的不同角度出發。所以,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必須要善于調和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達成長遠的利益共識,實現政府、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和個人之間的良性互動,凝聚各方力量,擰成一股繩,協同推動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
5.漸進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獨特的地理和歷史,決定了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治理過程。而且,其面臨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牽扯了許多方面,要解決好并非一朝一夕。因而,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是一場持久戰,不能急于求成,畢其功于一役,必須要善于總結經驗和教訓,一步一個腳印,在實踐中不斷摸索,漸進性地推進,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當前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邊疆民族地區農村一些基層黨組織社會治理能力不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基層基礎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每個基層黨組織和每個共產黨員都有強烈的宗旨意識和責任意識,都能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先鋒模范作用,我們黨就會很有力量,我們國家就會很有力量,我們人民就會很有力量,黨的執政基礎就能堅如磐石。”[3]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與其他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相比,任務更重、責任更大,不僅承擔著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主體責任,還要團結各民族群眾反對分裂,維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穩定。然而,邊疆民族地區農村一些基層黨組織社會治理能力較弱,影響了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推進。首先,部分黨員干部先進性不強。一些黨員干部由于長期生活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貧困、封閉的環境里,“等、靠、要”思想嚴重,缺乏創新意識,工作方法生搬硬套,沒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難以取得實效。其次,有些基層黨組織組織生活不規范。由于經費相對匱乏,有些基層黨組織組織生活要么打“折扣”,沒有全部貫徹落實;要么流于形式、走走過場,“大呼隆”“一鍋燴”現象嚴重,組織生活質量不高,黨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最后,一些基層黨組織服務功能弱化。一些基層黨組織對服務型黨組織認識和理解存在偏差,服務意識淡薄,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方式方法傳統滯后,不能及時傾聽農村群眾的合法利益訴求,社會矛盾和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
2.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意識不強。我國邊疆民族地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建立了村民委員會,開始實施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邊疆民族地區農村部分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意識不強,影響了村民自治制度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的實效性。邊疆民族地區農村部分群眾長期居住在封閉的環境里,生活自給自足,思想保守陳舊,對除生產生活以外的事物缺乏參與熱情。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邊疆民族地區農村越來越多的文化水平較高的青壯年選擇離開家鄉,外出打工、就業,導致邊疆民族地區“三留守”“空心村”現象十分普遍。留守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婦女、兒童和老人,他們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一部分是文盲,對村民自治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缺乏了解和認識,對村里的相關管理程序和規章制度不熟悉,不確切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權利和應該履行哪些義務。這就導致部分群眾對村里事務漠不關心,認為社會治理與自己毫無關系,只有在涉及自身經濟利益時,才會關心和重視。此外,由于歷史原因,邊疆民族地區農村過去大多是“人治”社會,“人治”思想在一些群眾心里根深蒂固,他們認為法治對于“種地人”而言只是形式,參與社會治理也是枉然。
3.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宗教消極因素的影響。“宗教是與人類社會相生相伴至今的特有文化現象,尤其在中國少數民族聚居的陸地邊疆地區,普遍的宗教信仰堪稱其基本特征之一,部分少數民族全民信教的現象隨處可見。”[4]而在邊疆民族地區偏遠落后的農村,大部分群眾更是將宗教信仰視為自己的精神食糧,在遇到任何問題和困難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向神靈祈福。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村民群眾正常的宗教信仰和需求,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建設和發展是并行不悖的。許多宗教教義中都蘊含著積極向上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價值,引導宗教信徒不斷追求“真、善、美”,對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當前宗教的某些消極因素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有時“暗流洶涌”,給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長期以來,境內外敵對勢力,披著宗教的外衣,通過QQ、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傳播宗教消極思想,鼓吹宗教自由,甚至煽動群眾進行非法集會和其它活動。由于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加之對宗教信仰極其虔誠,在境內外敵對勢力的蠱惑、煽動和蒙騙下,一些農村群眾淪為他們制造事端的代理人。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絕大多數信教群眾都是愛國愛教的純潔善良的人,境內外敵對勢力的種種行為很難得逞,但長期以往宗教消極因素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傳播和滲透,或多或少都會影響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國家、民族的認同,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
4.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服務水平較低。“社會組織是指政府以外的向社會領域提供服務的公共組織,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兩種類型,社會組織作為政府和人民群眾有序互動的紐帶和理性溝通的橋梁,在解決社會問題和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起到了潤滑劑的效用。”[5]近年來,社會組織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從無到有,并逐漸豐富發展,為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力量。但與我國其他地區農村相比,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在服務水平上相對較低。
究其原因,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撐。社會組織的資金主要來源于當地政府撥款和個人或團體的捐贈,而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政府財政收入較低,難以給眾多社會組織提供充足的經費。個人和團體的捐贈有限,并不能長期維持社會組織的運轉。因此,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硬件和高素質人才稀缺,服務能力和水平有限;另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管理體系不健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成員,主要是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社會組織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專業知識和技能欠缺,經驗明顯不足,社會組織的管理和運行主要依靠當地政府的支持和指導,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一些社會組織內部管理松散,沒有細化權責“清單”,各職能部門分工交叉、運行混亂,阻礙了其服務能力和水平的充分發揮。
三、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對策建議
1.切實提高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社會治理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絲毫不能放松。要重點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全面提高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6]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必須切實提高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首先,要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要“完善‘兩推一選’管理辦法,真正把那些‘雙帶’能力強、作風正、品德好、群眾擁護的優秀黨員選拔到村黨支部書記崗位上來”[7]。要依托黨校、互聯網等渠道,建立農村基層黨組織黨員干部培訓教育長效機制,深入開展“群眾路線”“三嚴三實”“兩學一做”等教育實踐活動,提升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其次,要嚴格規范組織生活。要確保“三會一課”制度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確保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認真參加學習。要堅持問題導向,將組織生活內容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有機結合,提高組織生活的“含金量”,增強黨員干部的工作能力;最后,要建設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基層黨組織要強化服務意識,密切與農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心農村群眾的生產、生活。切實改進服務方式方法,提高服務水平,“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2],精準有效地為農村群眾提供服務。
2.充分激發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主觀能動性。“基層社會治理是治理者和治理對象共同參與的雙邊交互活動,其基本模式是‘主體—客體—主體’的實踐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治理者發揮其治理的主導性,治理對象也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治理,而要發揮其自覺能動性。”[8]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既是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的治理對象,也是治理主體。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必須充分激發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方面,要改善農村群眾生活。改善民生是激發農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物質基礎,能夠增強農村群眾對社會治理的認同感和信心。因此,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立足于當地的特色優勢資源,走特色產業發展道路,增加農村群眾收入。要重視“三留守”和“空心村”問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緩解農村群眾就業壓力。要加強學校、醫院、活動中心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解決農村群眾上學難、看病難等問題,保障農村群眾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要轉變農村群眾的思想觀念。要加強對農村群眾的法治宣傳和教育,使他們充分了解村民自治制度和相關的法律、法規,提高法治意識。要拓寬農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力、表達訴求、解決糾紛。”[2]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讓農村群眾深刻認識到社會治理是與其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從而激發他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堅決抵制和預防宗教消極因素對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的不良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系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系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9]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必須要處理好宗教問題,尤其是要堅決抵制和預防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宗教消極因素或極端思想的傳播和滲透。一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抵御和反擊宗教消極思想最強有力的武器。為此,我們要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農村干部群眾頭腦,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使農村干部群眾認清宗教消極因素或極端思想的嚴重危害性,自覺抵制和預防這些思想的侵蝕。二要加強對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宗教事務的管理。要嚴格按照《宗教事務條例》,以“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2]為原則,依法對宗教各項事務進行監管,保護宗教活動的正常開展,打擊各種非法活動和不良行為。三要凈化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的網絡環境。互聯網作為新興媒體,其隱蔽性較高,是宗教消極因素或極端思想傳播和滲透的主要渠道之一。為此,我們必須加大對互聯網媒體的監管,構建全面、嚴密的網絡監控體系,做到及時發現,立刻堵截,嚴厲懲處。同時,要加強官方網絡宣傳教育平臺建設,傳遞正能量,弘揚主旋律,占領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網絡高地。
4.不斷提高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服務水平。社會組織是服務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群眾的重要平臺和載體,是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治理,必須要全面提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服務水平。一方面,要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資金和人才支撐。充足的資金和優秀的人才,是全面提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服務水平的基礎。必須加大對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財政扶持力度,設立專項資金,用于社會組織采購設備、引進人才等自身建設。要建立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人才培訓長效機制,加強對社會組織成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技能培訓等,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和服務能力。同時,鼓勵和號召社會力量參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進一步拓展社會組織的資金和人才來源渠道。另一方面,要健全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的管理體系。完善的管理體系,是全面提升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服務水平的關鍵。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要有效嵌入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中,加強對社會組織的領導和監督,確保社會組織健康發展。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組織自身要改革管理制度,優化內部結構,協調部門分工,明確責任“清單”,激發組織活力,充分發揮其服務功能。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5.
[2]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81-225.
[3]習近平.在河北省調研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07-12.
[4]方盛舉,呂朝輝.宗教信仰與中國陸地邊疆治理[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1):5-12.
[5]史欣.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知與行,2017,(2):40-44.
[6]習近平.在貴州調研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6-19.
[7]孫玉梅,劉誠,范玟均.黨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以玉溪市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為例[J].創造,2015,(5):54-57.
[8]方素清.論邊疆民族地區基層社會治理創新[J].黑河學刊,2015,(5):128-130.
[9]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