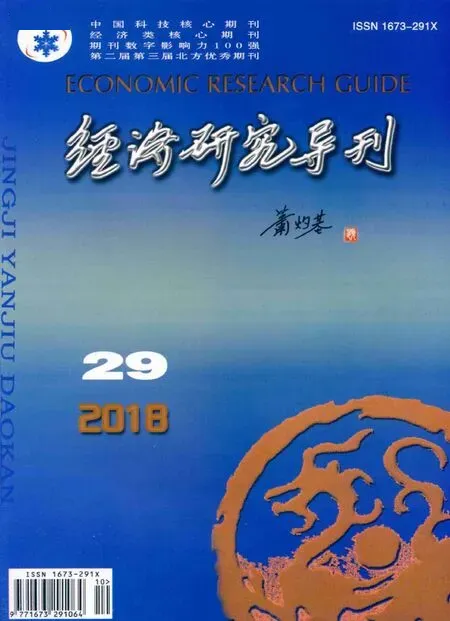經濟因素對南昌、泉州、西安等城市方言的影響
張一林,徐小青,陳 婷,馬瑞喧
(上饒師范學院歷史地理與旅游學院,江西上饒334000)
一、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對南昌話的影響
經濟的繁榮發展,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廣泛交流,也促進了語言的融合發展。唐代景德鎮瓷器比較有名,與南昌陶瓷貿易頻繁,促進了兩地的交流,兩地的方言也因此大體相同。再加上大運河和大庾嶺道的暢通,江西省成為長江中游地區南北東西的交通樞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西省與北方和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加強了江西省與北方和嶺南地區的交流,豐富了南昌方言。作為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對外貿易,在唐代有了重大發展:中國船隊可以直航西亞東非;對外貿易的傳統優勢產品除絲綢外,還加上了“瓷器”與“茶葉”。絲、瓷、茶三大名品從中國走向全世界,陸、海絲綢之路變成絲瓷之路。魏征曾這樣寫道:“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驛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于中國之所以好也。”[1]絲瓷之路向他國展示了唐朝的繁榮,促進了唐代與他國的經濟交流,也為南昌方言的發展創造語言環境。
兩宋時期,出現了很多商業性農業生產,甚至出現了日益專業化的各種生產區域。農產品、瓷器、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和紙張、書籍、硯臺等文化用品一方面從鄱陽湖出發,經過長江流域、京杭大運河,進行沿途貿易,最后到達北方,進行江西與北方地區的交易;另一方面,通過大庾嶺輸出,并由嶺南輸入香料,與官紳富家進行交易。農業、手工業生產全盛,嶺路開拓,航道暢通,加上位于四通八達的沖要區域,為商業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使得南北方語言間有了接觸的機會,促進了南昌方言區、粵語方言區與北方方言地區的再融合。
(二)對泉州話的影響
泉州瀕臨太平洋。福建省境內有閩江、木蘭溪、汀江、晉江和九龍江,河網發達,水上交通方便,經濟貿易的發展以海上貿易為主。唐初,社會發展穩定,在福州至泉州一線的沿海地區,人們圍海造田,舉辦了很多工程。中原和江東地區的移民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促進了福建經濟發展,同時,也使閩南方言增加了漢語詞和吳語詞,豐富著閩南方言。唐末五代時期建立的閩國政權,甚至留從效、陳洪進執政期間,都在在泉州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泉州境內的縣級官員努力安撫百姓、鼓勵生產,泉州經濟快速恢復[2]。泉州和平安定的環境吸引了內地移民的來居,“蕃客”(外國商人)由廣州移向泉州,都加速了泉州的經濟發展,給閩南方言添加了部分新的元素。北宋時期是泉州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北宋初期的泉州港已躋身于三大海港之列,大量外商來到泉州貿易。靖康之變后,北宋皇室被迫南移定居杭州,并在此建立南宋政權。南宋王朝財政問題日趨嚴重,而海上貿易利潤巨大,泉州又十分靠近杭州。因此,統治者更加精心的經營泉州,泉州港成為當時的第一大港。
元朝時期,泉州比廣州在距離上更加接近大都(今北京市),發展趨勢也優于廣州,并且在蒲壽庚的影響下,保存完好。更重要的是,統治者考慮經濟利益的需要,繼續發展泉州港。因此,泉州港極盛于元代,與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商貿交往密切,影響力可與亞力山大港匹敵。國內外商賈從泉州運載絲綢、瓷器、茶葉等貨物往他國銷售,從他國運來香料、藥材、珠寶到中國貿易,泉州港呈現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3]。宋元時期,泉州港經濟發展,尤其是與海外商賈的交往融合,給閩南方言添加了大量帶有異國特色的新元素。后來,泉州港因為戰亂和“禁海令”的影響,經濟地位下降,又因為貿易中心向福州轉移而日漸蕭條。因此,經濟因素對閩南方言的影響減弱。
(三)對西安話的影響
西安的農業經濟興起較早,到秦漢時代,整個關中平原已經成為全國最富庶的經濟地區之一,號稱“天府”。又因為得天獨厚的交通位置,使得關中平原自古以來又成為連接東西方的貿易中心。秦漢時期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的高峰,還是陜西歷史的高峰時期。西漢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東西方經濟交流的通路——絲綢之路,從此西漢王朝不斷派使者分赴西域各國進行貿易活動。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擴大,促進中原地區與西域、中亞以及西亞的經濟和語言交流。繼張騫通西域之后,班超、班勇父子經營西域,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進一步加強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4],同時,進一步促進了西安方言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地方言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隋唐時期,突厥、吐谷渾等少數民族受降,與唐朝交往密切,為西安方言添加了異域特色。元朝時期,經濟大致上以農業為主,其整體生產力雖然不如宋朝,但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
二、經濟政策的影響
(一)對南昌話的影響
三國時期,農業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重視農業和充實農業勞動力。當時戰亂紛飛、兵馬不停,統治者為了發展農業生產,采取了增加農業勞動力的政策。一是招撫流民,安輯流亡;二是采用諸種手段對敵區人民進行招誘或劫掠或逼遷;三是勸課弄桑,發展農業。農業經濟政策的實施,使人民穩定,扎根于土地,專心從事農業,給方言提供一個穩定的沉淀環境。
隋唐時期,政府注重發展經濟,采取獎勵農桑、開發礦產、發展手工業、招徠商旅等政策,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無論是黃河流域的關中地區,還是三河地區與長江流域的荊楊地帶,都是在繼續利用前代生產技術措施及管理經驗的基礎上,把北方的一些經驗技術向南方推廣[5]。注重發展經濟,采取獎勵農桑、開發礦產、發展手工業、招徠商旅等政策。北宋時期,戰亂結束,政府實行安輯流亡、給予田地、減賦輕役、獎勵墾殖、興修水利、發放農貸、勸課農桑等一系列農業發展政策,所以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積極的農業發展政策,如推廣生產技術、降低稅收、減輕農業生產壓力、增加農作物的產量等,為當地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商品基礎,也為方言交流提供物質基礎。
根據以上分析,原始贛方言的語音系統在東漢末年已經大致形成,而語音是方言的區別性特征,就此意義說,原始贛方言應大致形成于東漢中后期,衍生于唐五代,其人文格局卻一直延續到兩宋之際才得以確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種方言的確立并不僅僅取決于自身的語音特點,還取決于使用人口的多寡和文化影響力的強弱。而贛地區直到兩宋之際才具備以上條件,南宋以后贛方言的語音系統基本穩定。
(二)對泉州話的影響
隋唐以前,泉州地區人多地少,當地居民以耕田為生十分艱難,主要以打漁為生。后因中原漢人南下帶來先進的造船技術,泉州大規模發展海上貿易。下海貿易成為當時泉州人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隋唐時期,泉州港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統治者為鼓勵貿易,專門頒發敕令、詔書,讓番客自由貿易,不得重稅。于是,大量番商來到泉州,泉州方言第一次與歐亞各國語言發生大規模的融合。宋代設立泉州市舶司和建造番坊。市舶司監管海上貿易,征收貿易稅。市舶司的設立,標志著泉州進入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的行列;番坊的建立,吸引了外國商客來泉州貿易,甚至是定居泉州。番客的到來,豐富了泉州方言的內容。元隨宋制,依舊沿用市舶司,免除了出海的中國海商各類雜役,降低抽解比例,給予商客更大的自由權,泉州港的繁盛到達頂峰,與歐亞語言的交流亦達到頂峰。
閩南方言在漢昭帝設置冶縣時產生萌芽,唐代基本形成。宋元時期,國家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大量外商來到泉州貿易,給閩南方言注入新的血液,閩南方言定型成熟[6,7]。在泉州,由于沒有出現漢人與土著爭戰的記錄或其他有重大影響的戰事,來源不同、時代不同、自然聚居點不同的入閩漢人所帶來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漢語方言特色,被很好地保留下來。
(三)對西安話的影響
歷史上經濟政策的變化導致陜西人口數量的三起二落。較好的經濟政策使外來人口的不斷涌入,反之,則相反。陜西歷史文化不僅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而且在每一個歷史層面都有截然不同的特點[8]。凡峰值均是社會安定時期,人口自然增長與機械增長同時進行,此時亦是陜西經濟方言大發展、大規模接受外來語言的時期;而人口落至谷底時期,則是陜西經濟崩潰之際,同時也是陜西方言衰落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