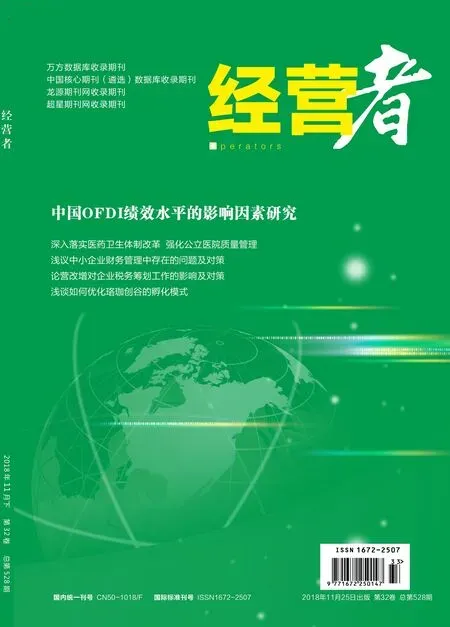淺析合伙人越權擔保的效力
陳儒敏 岑冬玲
一、前言
人合是合伙企業成立的基礎,合伙人共同經營合伙企業,并對合伙企業的債務共擔風險,因此有關決議需經合伙人多數乃至一致同意。但部分合伙人擅自以合伙企業之名對外行事的現象屢見不鮮,且越權擔保最為常見。雖然法律確立了合伙企業對外擔保的一致同意規則,但對于越權擔保的效力認定問題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本文以探究民法邏輯與商法思維的不同思維路徑的分析方法入手,著眼于商事秩序,對論題進行細致嚴謹的探究。
二、設例
被告趙某因資金周轉困難,向原告盧某提出借款人民幣8萬元。盧某同意但要求擔保。為此,某合伙企業的合伙人秦某私自為趙某向盧某出具擔保。上述借款到期后,盧某向趙某催要借款本金及利息未果,遂將趙某、秦某以及該合伙企業一并告上法庭。經查,該合伙企業現有合伙人4人,且并無證據表明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秦某以企業名義為趙某提供擔保。其他合伙人認為秦某未經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該擔保協議應為無效,由此引發爭議。
三、民法邏輯與商法思維的分析路徑
“除合伙協議另有約定外,合伙企業的下列事項應當經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業名義為他人提供擔保”《合伙企業法》如是規定。這一規定確立了合伙企業對外擔保的一致同意規則,但對于合伙企業未經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而對外擔保的效力認定問題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主流觀點主張優先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認為合伙企業的利益已經通過其他相關制度得以保護,因此主張應當優先保護擔保權人的利益;而反對派則傾向于優先保護合伙企業和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其往往直接從規范的目的出發,認為對外擔保規則是效力強制性規范,直接對外發生效力,違反者擔保合同無效。
縱觀以上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分歧的產生源于民法邏輯與商法思維的差異。不難看出,主流觀點的理論基礎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公平原則。民法邏輯著重保護的是交易中雙方主體實體性的公平和平等,特征是通過尋求個體的“絕對公平”來實現社會的“整體公平”。民法以合同法、擔保法為中心,目的是保護交易相對方的利益、提高效率和保障安全,自然傾向于排除內部決議的直接對外效力,甚至“運用合同法第48、49、50、52條的過濾機制切斷決議效力的對外影響力和決議被撤銷時的溯及力”。[1]而反對派主張《合伙企業法》的立法目的是通過規范有關主體的商事活動,維持整個商事社會的秩序。商法以整個商業社會的整體交易規則為保護對象,其特征是通過尋求商業社會的“整體公平”來實現個體的“相對公平”。[2]商法思維主導下的學者通常以商事組織法為中心,以保護合伙企業和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此在價值衡量的過程中通常偏向于企業相關者的利益保護,主張企業內部決議具有溢出效應,能夠約束第三方。
通過分析,筆者更加認同運用商法思維對商事主體的行為進行評價的分析路徑。商法與民法雖同為私法的組成部分,但商法思維與民法邏輯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在司法實踐當中,若簡單地以民法邏輯的方式處理商事案件會對商業活動的正常流轉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會造成“實際的不公平”,[3]破壞商事秩序。因此,商法在商業活動糾紛認定與解決機制上應有區別于民法的方式與路徑。
四、商法思維主導下的越權擔保行為效力分析
“逐利的驅動助長了商人的貪婪本性,商事風險隨時潛伏在商事交易活動過程中,保障交易安全又成為營利和效率之外商法所追求的另一重要目標。”[4]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自由經濟,自由是市場機制運作的核心要求,商主體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容易做出過度的利己行為,這些行為會導致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融入商業活動當中,給商事秩序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商法思維的重要內容便是通過商法維護商事秩序。
首先,《合伙企業法》的立法目的也正是為了規范合伙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使合伙企業得以健康持續地發展。基于此,我們認為,法律既已明文規定“合伙協議另有約定除外”,表明合伙企業可以通過自主協商制定合伙協議以破除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這無疑是立法者對商主體的意思自治的最大肯定。而在此情況下,如果仍認定違反法律相關規定的行為有效,允許債權人以“善意”為由向合伙企業主張權利,那么將間接架空合伙企業法就合伙企業的內部設計,導致合伙企業的合法財產得不到保障,正常的生產經營受到干擾,損害商事秩序。
其次,對比合伙人擅自以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出質,合伙人越權為他人提供擔保具有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合伙人以其財產份額出質,一旦出質人不能實際償付債務,合伙企業及其他合伙人就要承擔債權人占有或變賣出質財產份額,導致合伙人變化的后果。如此,雖然會破壞合伙企業的信賴基礎,但未對合伙企業以及合伙人的個人財產造成不利影響。而合伙人擅自以合伙企業名義為他人擔保,其實是以合伙企業的財產做擔保,甚至是以其他合伙人個人財產做擔保。若債務人到期無法履行債務,債權人有權以合伙企業的財產優先受償,這樣會使合伙企業的財產受到損害,甚至會導致其他合伙人產生連帶責任。其危害性顯然大于合伙人擅自出質。顯然,在擅自出質行為被認定為無效時,若比它更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越權擔保行為被認定有效,會有損市場經濟秩序。
五、結語
“如果在一個國家的司法中甚至連最低限度的有序規則也沒有,還是避免使用法律這一術語。”誠如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所言,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規則,若這一規定都被破壞,一國的法治將無從談起。因此,筆者認為,在合伙企業出現合伙人未經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以合伙企業的名義為他人提供擔保時,應認定合同無效,以保護合伙企業以及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權益,防止合伙企業制度被破壞,擾亂市場秩序,破壞公共利益。與此同時,立法機關應以司法解釋等方式明確指出違反該條款即無效,減少由于對法律理解不一致而導致法律適用結果不同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