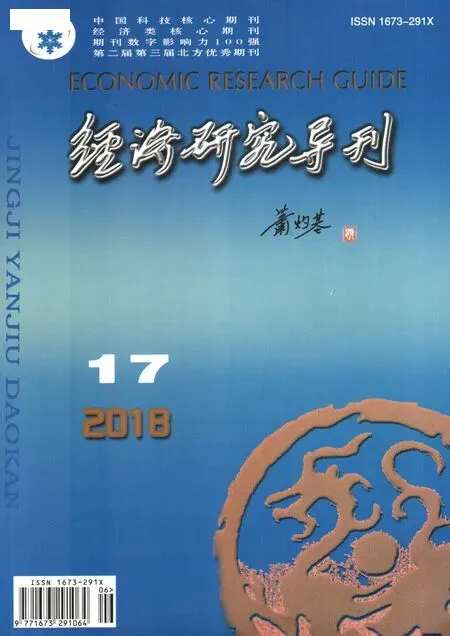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機構改革的認識與思考
喬立軍
(黑龍江科技大學,哈爾濱150010)
一、政府機構改革的演變過程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歷了八次較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分別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以及最近的2018年。
(一)20世紀80年代政府機構改革
1982年,政府機構改革是在“改革開放”政策提出的背景下進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崗”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于國家重心的轉移,機構的數量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峰,就國務院組成部門來看,數量就達到了100個。1982年1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機構數量龐大的問題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改革中,整合政府各個機構,其中國務院組成部門由之前的100個減少到61個,國務院各部委人員由5.1萬人減少到3萬人;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原則,打破了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制度,選拔了大批有志青年,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和活力。
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是由于1986年政府機構和人員數量出現回潮,國務院機構數量由精簡后的61個部門增加到70多個,各地的政府機構增加的數量比國務院機構更多,所以再一次的機構改革勢在必行。1988年3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通過了機構改革的議案。這次機構改革,首先要精簡機構數量,其次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和理順機構之間的關系,建立起一個結構合理和靈活高效的行政體制。改革中,國務院工作部門由73個減少到66個;在職能上弱化了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的職能,增強了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二)20世紀90年代政府機構改革
1993年,這次改革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進行的,現有的行政體制需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在這次改革中,其重要任務就是減少或合并一些工業專門經濟部門,減少政府的管理職能,推動政企分開,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但是,從改革的機構設置來看,在這次改革中工業專門經濟部門撤銷的少,而增加、保留的多,例如,1988年合并的能源部門,在這次改革中又撤銷,設立了電力工業部和煤炭工業部。總體來說,這次改革的目的初見成效,國務院工作部門減少到59個,人員編制也比之前減少20%。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目標,但是機構的改革任重道遠。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重點為實行政企分開,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在這次改革中,為盡快減少工業專門經濟部門對企業的直接管理,國家幾乎撤銷了所有的工業專門經濟機構,其體現為:國務院撤消了電力工業部門、煤炭工業部、林業部等10個工業專門經濟部門。通過對工業專門經濟部門的撤銷,進一步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打破了政企不分的組織堡壘,加強了企業在微觀經濟上主體地位,更好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
(三)21世紀以來的政府機構改革
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是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做出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這次的政府機構改革不僅要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要與國際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相協調,使中國盡快融入到國際環境的大潮里。在這次改革中,國務院組成部門不再保留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委,將其職能并入到新組建的商務部中,并且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金融體系,以減少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的沖擊,促使中國盡快融入到國際經濟環境中。
2008年和2013年,這兩次政府機構改革依舊是轉變政府職能,合理配置政府機構職能,減少了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減少審批項目,充分發揮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強化政企分開的觀念。其次,政府機構改革強化了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著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在這兩次改革中,政府積極轉變職能,由更多的“管理”向“服務”轉變,更多地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對政府的形象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
2018年,黨的十九大提出,“當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國家政府機構需要通過改革,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早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在這次改革中,機構的設置更多地與人民的需求相適應,著眼于解決人民群眾最急切的問題,例如:為解決人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組建國家醫療保障局。這次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的現代化,使政府機構在設置上更加能夠體現整體性、系統性和協調性。
二、政府機構改革的特點和問題
(一)特點
1.規模上: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變化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的大大小小的八次改革,都在不斷縮小政府規模,使國務院組成部門由1982年的100個減少到2018年的26個。在這個期間還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機構和人員數量的回潮,使得政府機構改革陷入到“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歷史怪圈,曾一度阻礙了政府機構改革的進程。雖然政府機構改革陷入歷史怪圈,但是不可抹殺改革帶來的成效,即使每次改革后都有回潮,但實際上回潮的幅度遠要小于改革的幅度。總體上,政府機構的數量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由“大政府”向“小政府”的一個轉變,適度控制政府的規模,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率。
2.職能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改革開放前期,我國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期,政府機構仍然以“管理”為主,設立多重機構對經濟和社會事務進行控制和管理,造成政企不分,難以發揮市場經濟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以及難以發揮企業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2004年,溫家寶首次提出“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并且在2005年的《政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在之后的政府機構改革中,多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目的,轉變政府職能,進行權力下放,打造“透明公開”的政府,由“管理”人民向“為人民服務”轉變。在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政府努力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一種常態,讓人民信任政府,依賴政府,努力將政府建設成服務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創新型政府。
(二)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1.法律制度建設與政府機構改革進程較為不匹配
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法律是機構改革的制度保障。1954年,我國頒布了《國務院組織法》,在之后的三十年里國家沒有對《國務院組織法》進行修改,直到1982年憲法修訂,《國務院組織法》才進行修改,在之后只進行了三次修改,分別為1986年、1995年和2015年,使得機構改革的法律制度建設相對滯后于政府機構改革的行政制度,政府只是簡單運用強硬的行政手段進行機構改革和職能劃分,從而忽略了法律對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放慢了政府機構改革的進程。
2.政府機構內部改革積極性不足
在改革過程中,勢必要對一些機構進行拆分或合并,對編制人員進行人事調動,損害一些機構人員的個人利益,從而導致機構改革的積極性不足,甚至會阻礙政府機構改革。當前,我國在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上級對下級監督、內部監督以及外部監督的力度不足,導致“上令不能下達”,“內部包庇”等現象,造成國家政府機構改革難以進行,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整體進程。
3.黨政部分職能交叉
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往往涉及到的為縱向改革,一般為政府機構部門之間,部門內部以及職責之間的改革,忽略了橫向的黨和政府機構之間的聯系。在我國黨和政府之間存在著部分職能的交叉,造成決策和執行混亂進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的領導作用,同時還降低了政府的執行力,阻礙辦理行政事務的效率,還會滋生政治腐敗行為,這也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反腐倡廉力度的原因之一。
三、國家政府機構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一)法律制度建設與政府機構改革齊頭并進
政府機構改革的法律制度建設要與機構改革的行政體制相結合,甚至要優先于機構改革,為政府機構改革提供一個系統化、程序化的法律框架,為機構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法制保障,從而規范政府機構改革的行為,防止機構對權利的濫用,使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呈現出整體性、協調性。
(二)加強機構改革的監管力度
改革過程中,政府機構內部容易出現改革積極性不高,甚至阻礙機構改革的進行,因此要加強機構改革的監管力度。從內部上,機構部門應該建立相應的績效制度和權力制衡機制,實行具體的獎賞制度,推動機構內部的改革積極性。從外部上,建立中央巡視監察小組以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來監督機構改革的進程。同時,也要配合媒體輿論監督。加強內部與外部的監督,使政府機構改革能夠更加深入進行。
(三)理順黨和政府、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系
政府機構改革,要注重兩方面的改革:一是橫向改革,理順黨和政府交叉的職能,將執政和行政區分清楚,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地位的同時,也要提高政府的執行能力;二是縱向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權力關系。加強中央的領導作用,給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權,進行權力下放,使地方能夠因地制宜地進行機構改革,使改革的結果更能夠與當地情況相適應。
(四)明確職能劃分,簡政放權
政府機構改革不僅要減少或合并政府部門,還要對政府機構的職能進行劃分。在職能劃分中要有邊界意識,首先要理順機構與機構之間的關系,機構與職能之間關系以及職能與職能之間的關系;其次明確機構所對應的職責,做到機構與職能設置的對應性和合理性。政府機構改革不僅能夠做到機構數量的“瘦身”,還能做到機構與職能相配合的“健身”,使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更加平穩,從而促進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