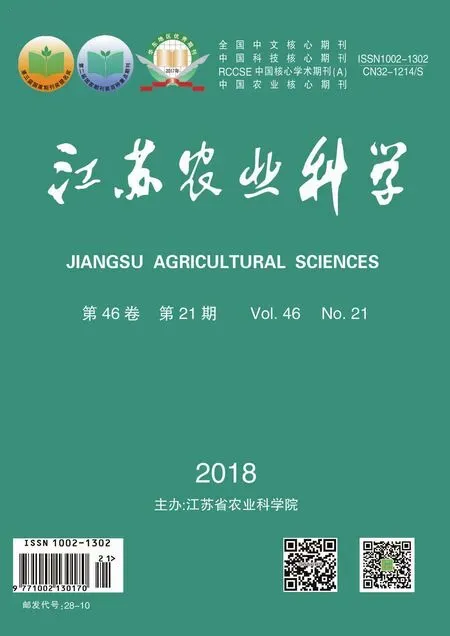馬鈴薯與蠶豆、蕎麥間作對土壤的影響
劉亞軍, 李 越, 馬 琨, 何文壽
(1.寧夏大學西北土地退化與生態恢復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寧夏銀川 750021; 2.寧夏大學農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3.商丘市農林科學院,河南商丘 476000)
馬鈴薯是西部地區的重要農作物,栽培歷史悠久,具有穩定的、較高的經濟效益[1]。近年來,馬鈴薯主糧化促進了寧夏南部山區馬鈴薯產業化發展,使得其栽培面積不斷擴大,致使馬鈴薯輪作倒茬困難。馬鈴薯多年連續不斷地種植導致馬鈴薯產量下降、土壤質量下降、病蟲害頻繁不斷地發生,而農作物間作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間作是一種集約化生產模式,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栽培歷史[2]。合理的間作模式不僅能夠利用作物對養分需求特性的不同而促進養分的有效吸收,也能夠通過其時間、空間等方面的互補性高效利用水肥氣熱等資源[3]。已有研究指出,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影響著土壤養分的吸收和轉化,土壤酶活性的降低與微生物結構的失衡是導致土壤質量下降、作物減產的主要原因[4]。而作物合理的間作不僅能夠提高土壤中的養分含量、改善土壤的微環境,還能夠增加作物的產量,改善作物的品質,提高作物的安全性[5]。傅佳等在重茬種植西洋參對土壤養分和微生物的研究中發現,土壤酶活性與根際微生物類群呈顯著正相關,可改善土壤中養分的轉化和吸收、根際微生物群落結構的組成和數量[6]。汪春明等在馬鈴薯間作蠶豆的研究中認為,間作模式有利于改善馬鈴薯連作栽培的根際微生態環境[7]。吳紅英等在沙地梨園間作研究中指出,間作可以增加梨樹各時期和各土層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數量,改變土壤微生物群落中細菌、放線菌和真菌的比例[8]。劉均霞等在對玉米間作大豆的體系研究認為,間作體系中玉米、大豆的土壤酶活性和根際土壤微生物數量顯著高于相應的單作對照組,間作大豆處理的脲酶活性和根際土壤細菌數量顯著高于單作大豆對照組[9]。Li等在間作玉米和蠶豆的研究中采用測定磷脂脂肪酸(PLFA)含量的方法,證實間作模式對玉米和豆科作物根際微生物群落的結構和功能有影響[10]。可見,合理的間作模式可以改善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結構組成,提升土壤質量,對作物的生長發育有著重要影響。本研究以單作馬鈴薯、蠶豆、蕎麥,馬鈴薯間作蠶豆、蕎麥為處理,通過研究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養分含量、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響,揭示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下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結構變化的特點,旨在為馬鈴薯合理間作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點概況
該試驗于2015年4—10月在寧夏農林科學院固原頭營科研基地徐河村進行,地處東經106°44′、北緯36°10′,海撥 2 341 m。初霜期9月上、中旬,終霜期5月上、中旬,無霜期140 d左右,降水291~415 mm,屬半干旱半濕潤地區。供試土壤為黃綿土,土壤基礎理化性狀為:有機質含量 10.63 g/kg,全氮含量0.258 g/kg,全磷含量0.645 g/kg,堿解氮含量20.51 mg/kg,速效磷含量45.5 mg/kg,速效鉀含量170.5 mg/kg,土壤pH值9.00。
1.2 試驗設計與樣品采集
試驗采用單因素區組設計,種植方式分為:處理1,馬鈴薯單作(MP);處理2,蠶豆單作(MF);處理3,蕎麥單作(MW);處理4,馬鈴薯+蠶豆(P+F);處理5,馬鈴薯+蕎麥(P+W)。小區面積為6 m×4 m,4次重復。供試馬鈴薯為青薯9號,蠶豆(faba bean)為青蠶11號,蕎麥(buckwhea)為寧蕎1號。種植2行馬鈴薯,間種2行蠶豆或蕎麥,馬鈴薯株行距為40 cm×60 cm,蕎麥行距為30 cm,蠶豆株行距為 20 cm×20 cm。馬鈴薯與蠶豆間距30 cm,馬鈴薯與蕎麥間距35 cm。
試驗地前茬作物為玉米,秋翻,返春后耙耱整地,播種前施用優質農家肥30 000 kg/hm2、尿素255 kg/hm2,磷酸二銨170 kg/hm2,磷酸二氫鉀90 kg/hm2,其中70%氮肥作基肥,30%氮肥作追肥。4月25日播種蠶豆、馬鈴薯,5月23日播種蕎麥,8月12日收獲蠶豆,9月20日收獲蕎麥、馬鈴薯。
在馬鈴薯花期,選擇毗鄰馬鈴薯的1行,通過土鉆利用五點取樣法隨機取五處土壤,把取到的土樣混合后放入冰盒中帶回實驗室。土壤樣品一部分存于4 ℃冰箱,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與生物量的測定;一部分自然風干,用于土壤理化性質和酶活性的分析。
1.3 測定指標及方法
1.3.1 土壤理化性狀 土壤有機質含量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外加熱法;全氮含量采用半微量凱氏法;堿解氮含量采用堿解擴散法;全磷含量采用HClO4-H2SO4法;速效磷含量采用0.5 mol/L NaHCO3法;速效鉀含量采用NH4OAc浸提火焰光度法;土壤pH值(1 ∶5土水比)的測定參照文獻[11]。
1.3.2 土壤酶活性測定方法 土壤脲酶活性采用苯酚鈉-次氯酸鈉比色法測定;土壤堿性磷酸酶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法測定;土壤過氧化氫酶活性采用高錳酸鉀滴定法測定[12]。
1.3.3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測定 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采用稀釋平板法測定。其中,細菌培養采用牛肉膏蛋白胨瓊脂培養基;真菌培養采用馬鈴薯-蔗糖瓊脂(PDA)培養基;放線菌培養采用改良高氏一號培養基[13]。
以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PLFA)含量反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其測定步驟為:稱取相當于4 g干土質量的新鮮土樣于棕色培養瓶中,加入磷酸緩沖液 30 mL 和甲醇 ∶三氯甲烷(2 ∶1)溶液105 mL后振蕩2 h,取出分別加入三氯甲烷和無菌超純水各36 mL,振蕩混勻,在黑暗中培養18~24 h;吸掉試劑瓶上層的水和甲醇,用無水硫酸鈉除去未吸凈的水,然后進行過濾、旋轉蒸發濃縮。其中利用固相萃取技術,通過SPE固相萃取小柱進行脂肪酸分離。最后加內標液(十九碳酸甲酯)0.5 mL,用GC-MS分析。經甲酯化后采用Agilent 6850型氣相色譜儀測定,在進樣口為 300 ℃、H2流量為 30 mL/min、色譜柱為Agilent HP-5MS,30 μm×250 μm×0.25 μm,二階程序升高柱溫(170 ℃時按照5 ℃/min升至260 ℃,而后40 ℃/min升至300 ℃,維持 2 min),測定標準樣品成功后再分析待檢樣品。
1.4 數據處理與分析
利用Microsoft Excel 2007進行數據處理,DPS 7.05進行方差分析(LSD法),Canoco 4.5進行多元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化學性狀的影響
由表1可知,馬鈴薯收獲期間作土壤養分含量與單作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馬鈴薯間作蠶豆土壤養分含量與單作馬鈴薯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全磷、堿解氮、有機質含量分別顯著增加9.10%、14.54%、17.87%(P<0.05);與單作蠶豆相比,除全氮、全磷含量顯著增加外,其余養分含量顯著下降。經分析,在茄科與豆科的間作中,由于豆科作物根瘤菌具有固定空氣氮素作用和地下根系交互作用,從而會促進氮素的轉化與吸收,蠶豆收獲后由于間作系統的恢復作用促進馬鈴薯對其他養分的吸收和轉化,較單作馬鈴薯可以提高土壤中的養分含量。

表1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化學性狀的影響
與單作馬鈴薯相比,馬鈴薯間作蕎麥土壤的全磷、有機質含量顯著提高,其余無顯著變化;與單作蕎麥相比,其土壤速效磷含量顯著增加,其余養分含量無顯著性變化,說明在茄科與蓼科的間作系統中由于根系之間的交互作用,增加了磷肥的吸收與轉化,并提高了磷的利用效率。馬鈴薯是喜鉀作物,2種作物間作時可促進對鉀的吸收,與單作蕎麥相比減少土壤速效鉀含量。而間作蠶豆、蕎麥的土壤pH值與單作馬鈴薯相比分別下降1.27%、1.39%。有研究認為,間作栽培會改變土壤的pH值,進而影響土壤中養分的轉化和吸收[14]。而本研究中間作模式下馬鈴薯土壤各養分含量較單作馬鈴薯處理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可見間作系統中由于根系交互作用以及蠶豆收獲后對馬鈴薯的恢復作用促進了土壤中的營養吸收以及養分的轉化,說明合理的間作可以影響土壤pH值以及改善土壤的養分質量。
2.2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土壤酶活性反映了土壤中各種生物化學過程的強度和方向,它與土壤肥力狀況、理化特性和農業措施有著較為顯著的相關性,是土壤肥力評價的關鍵指標之一[15]。由表2可知,與單作馬鈴薯相比,馬鈴薯間作蠶豆的土壤脲酶和堿性磷酸酶活性分別顯著增加22.05%、20.00%,過氧化氫酶無顯著變化;而與單作蠶豆相比,土壤脲酶活性顯著增加,堿性磷酸酶顯著下降,過氧化氫酶活性顯著性下降。經分析發現,脲酶對尿素的轉化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影響,堿性磷酸酶可加速有機磷的脫磷速度,磷酸酶的積累對有效磷具有重要的作用,豆科作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促進了其對氮素的吸收和利用,蠶豆根系可分泌磷酸酶,從而提高了土壤中磷酸酶的活性。在馬鈴薯間作蠶豆的模式中蠶豆收獲后,由于恢復作用后期馬鈴薯增加了對有效磷的吸收,從而提高了土壤中堿性磷酸酶的活性。

表2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馬鈴薯間作蕎麥與單作馬鈴薯相比土壤酶活性無顯著性變化;與單作蕎麥相比,土壤脲酶活性顯著下降19.54%,堿性磷酸酶和過氧化氫酶無顯著性變化。在茄科與蓼科的兼間作系統中增加了對土壤氮素的吸收,降低了脲酶的活性。過氧化氫酶是一種氧化還原酶,其作用在于破壞對生物體有毒的過氧化氫,該間作模式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因此,合理的間作模式可顯著提高土壤中的酶活性,對土壤中養分的吸收轉化起較大的影響。
2.3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
由表3可知,單作蠶豆的微生物總群落數最低,馬鈴薯間作蠶豆的微生物總群落數最高。馬鈴薯間作蠶豆、蕎麥較單作馬鈴薯的真菌、細菌數量上升,放線菌數量下降,其中馬鈴薯間作蕎麥處理中的放線菌數量顯著下降36.5%(P<0.05)。而從微生物各結構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馬鈴薯間作蠶豆、蕎麥處理中的細菌所占比例上升,放線菌所占比例下降。不同作物根際土壤都有其特定的微生物區系,而不同間作模式對探究根際土壤中微生物結構、研究馬鈴薯根際土壤養分的轉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16]。由以上結果可以推測,馬鈴薯與豆科、蓼科作物間作時細菌數量的累計增長會抑制放線菌的轉化,從而導致放線菌數量下降,對土壤中養分的轉化和吸收產生影響。

表3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的影響
磷脂脂肪酸(PLFA)是土壤經甲基化提取磷脂成分后得到的脂肪酸產物,其中磷脂是活細胞膜的基本成分,具有多樣性和生物學特異性,且脂肪酸只存在于活細胞中,因此PLFA適用于微生物群落的動態監測,常被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測定[17-18]。由表4可知,單作馬鈴薯土壤微生物主要類群的PLFA含量最高,單作蕎麥主要類群的PLFA含量最低,其中單作蕎麥革蘭氏陽性菌(G+)中的含量與單作馬鈴薯相比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間作模式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PLFA含量與單作馬鈴薯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間作蕎麥的菌根真菌(AMF)中的含量顯著下降55.6%(P<0.05)。

表4 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生物量的影響
2種間作模式中革蘭氏陽性菌(G+)和革蘭氏陰性菌(G-)的生物量以及細菌的生物量與單作馬鈴薯相比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馬鈴薯間作蕎麥的細菌生物量較單作蕎麥有所增加,但差異不顯著。馬鈴薯間作蕎麥的總生物量較單作蕎麥升高,其余間作模式中的土壤微生物總生物量均低于各自單作對應的總微生物量,但均無顯著性差異。馬鈴薯間作蕎麥中的G+生物量/G-生物量以及馬鈴薯間作蠶豆、間作蕎麥中的真菌生物量/細菌生物量較單作馬鈴薯有所降低,間作蠶豆的G+生物量/G-生物量的值升高,但均無顯著性差異。
由以上結果可知,茄科與豆科、蓼科間作會減少土壤中細菌、放線菌、真菌等微生物主要類群的生物量,說明茄科與豆科、蓼科間作改變了土壤微生態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馬鈴薯根際土壤微生物主要類群PLFA的生物量;而真菌生物量/細菌生物量的值降低和間作蠶豆中G+生物量/G-生物量的值升高,均表明間作有利于促進土壤向高肥效的“細菌型”土壤類型轉變。
2.4 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與土壤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
多元分析結果(圖1-A、圖1-B)顯示,各排序軸都能在超過56%的累計貢獻率上解釋土壤微生物結構及微生物生物量變化與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排序圖(圖1-A、圖1-B)反映了各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最適宜生活的土壤環境,各處理點分散較為明顯,說明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下形成了不同的土壤微生態環境,各處理間有差異。由圖1-A可知,排序軸累積解釋的信息量達70.1%。因此,基于特征向量載荷因子相聯系的排序軸1和軸2最大程度地解釋了不同處理之間土壤環境因子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土壤細菌、真菌數量除與全氮含量成銳角外,與其他環境因子都成鈍角;而放線菌數量與全磷含量、速效氮含量、pH值成銳角,與其他環境因子呈鈍角。由于圖1-A中2條射線代表其相關性,銳角代表呈正相關,其夾角越小,相關性越強,鈍角與之相反,鈍角越大負相關性越大。說明細菌、真菌數量與全氮含量呈正相關性,受全氮含量環境因子影響較大,與其他環境因子呈負相關性。放線菌數量與土壤全磷含量、速效氮含量、pH值呈正相關性,與其他環境因子呈負相關性。
圖1-B顯示了不同處理下微生物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的制約關系,土壤微生物生物量與環境因子也表現出一定的相關性。其中,菌根真菌生物量與全氮含量呈負相關性,而與其他環境因子都呈正相關性,原生動物、細菌、放線菌、真菌、G+、G-生物量與有機質、全磷、速效磷、速效鉀的含量有良好的相關關系,與其他環境因子呈負相關性。由圖1可以看出,5種種植模式分別位于不同的象限,說明種植模式不同,土壤微生物結構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不同,受環境因子的影響也不相同。綜合可知,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下土壤微生物結構和微生物生物量的變化與土壤環境因子有著密切聯系,受多種環境因子制約。

3 討論
3.1 不同間作模式對土壤理化與生物學性狀的影響
土壤養分是作物攝取養分的主要來源之一,在作物養分吸收總量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土壤養分含量的高低關系著植株能否健康生長或生存。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合理的間作可以提升土壤中的養分含量。郝艷如等在玉米、小麥間作的研究中表明,間作模式提高了土壤中的有效養分含量,改善了土壤根部供肥能力和養分吸收環境[19];代會會等在豆科間作試驗中發現,間作可以增加土壤中全氮、速效氮、速效鉀和速效磷含量,并且提高作物產量[20]。本研究結果表明,在茄科與蓼科、豆科的間作中,不同的間作模式與單作馬鈴薯相比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土壤中的養分含量,降低了pH值,其中間作蠶豆的堿解氮、有機質含量,間作蕎麥的速效磷、全氮、有機質含量增加較多,且差異達到顯著水平(P<0.05),這與代會會等的研究結果[20]較為一致。經分析發現,茄科在與豆科、蓼科的間作系統中由于空間、根系和生理等方面的需求差異以及互補性,使得土壤中的養分和自然資源得到最大的利用,從而提高土壤中的養分含量。
土壤酶是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和物質交換等生態過程中活躍的生物活性物質,且土壤堿性磷酸酶、過氧化氫酶、脲酶的活性能夠分別反映出土壤磷素供應狀況、有機質的轉化速度和土壤氮素水平狀況,對農作物的生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2]。柴強等在研究間甲酚對間作模式中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響中指出,通過玉米+蠶豆發現間作模式對土壤磷酸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具有極顯著影響[21];Zhou等在黃瓜間作洋蔥、大蒜的研究中表明,間作模式下土壤脲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高于黃瓜單作[22]。本研究結果表明,間作模式下磷酸酶、脲酶、過氧化氫酶活性升高,其中間作蠶豆的磷酸酶和脲酶活性與單作對照相比差異顯著,這與姜莉等的研究結果[23]較為一致。由于豆科作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以及收獲后馬鈴薯的恢復作用對間作馬鈴薯養分的吸收有較大影響,并且間作模式下作物之間對土壤養分的相互作用和利用促進了土壤酶活性的變化,使得酶活性與土壤環境因子聯系變化更為敏感。
3.2 不同間作模式下土壤理化性狀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參與土壤的物質交換和能量轉化,土壤酶參與土壤中許多重要的生物化學過程,二者共同成為評價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標[24]。而合理的間作可以改變土壤的微環境,由于根系分泌物、作物殘體和根系殘體在土壤中的累積,供給土壤微生物的營養物質增加,因此增強了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結構多樣性,進而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微生物區系[25]。很多研究結果表明,合理的間作可以提高作物根際土壤微生物的數量[26]。其中宋亞娜等對小麥+蠶豆、玉米+蠶豆和小麥+玉米間作體系進行研究時發現,間作能改變根際細菌群落結構的組成,且證明了間作體系地上部多樣性與地下部多樣性存在著緊密聯系[27];馬琨等在間作栽培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響中表明,間作栽培顯著地改變了根際土壤微生物主要功能群落的結構[28];吳娜等在馬鈴薯間作燕麥的研究中指出,馬鈴薯+燕麥(4 ∶2)的種植比例能改善根際土壤微生態環境,優化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29]。Artursson等研究認為,根系分泌物中某種物質促進了根際土壤中革蘭氏陽性細菌、AMF真菌的累積,從而相應地增加了微生物的生物量[30]。
本試驗結果表明,不同間作模式下間作處理增加了真菌、細菌的數量,減少了放線菌的數量,但差異均不顯著。真菌比例變化較小、細菌比例增加,使土壤向著更高效的細菌型土壤轉化,而微生物群落總數的增加增大了微生物環境的多樣性。間作處理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細菌、放線菌、真菌的生物量較對照組減少,但細菌中革蘭氏陽性菌生物量比例增加、真菌生物量/細菌生物量的值降低,表明間作模式能改變馬鈴薯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組成及環境的對應關系。
由以上結果說明間作條件下,茄科與豆科或蓼科作物之間的根系橫向交叉,其根系分泌物改變了間作模式下土壤微生物的區系結構,進而影響了馬鈴薯根際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改變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結構組成。由Canoco多元分析表明,土壤養分的轉化和吸收與微生物群落結構和微生物生物量的變化呈緊密的相關關系,說明間作模式不僅能提高土壤養分含量、酶活性,還能改變土壤中的微生態環境,產生與環境因子相適應的微生物區系。
4 結論
馬鈴薯間作蠶豆提高了土壤堿解氮、有機質的含量,間作蕎麥提高了土壤速效磷、全氮、有機質的含量,且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馬鈴薯間作蠶豆顯著地提高了土壤磷酸酶和脲酶活性,而馬鈴薯間作蕎麥土壤酶活性與對照相比無顯著差異;間作模式降低了土壤中放線菌的比例,提升了土壤中細菌的比例,并且改變了土壤中微生物主要類群的PLFA含量;馬鈴薯不同間作模式下土壤養分與微生物群落結構的變化較為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