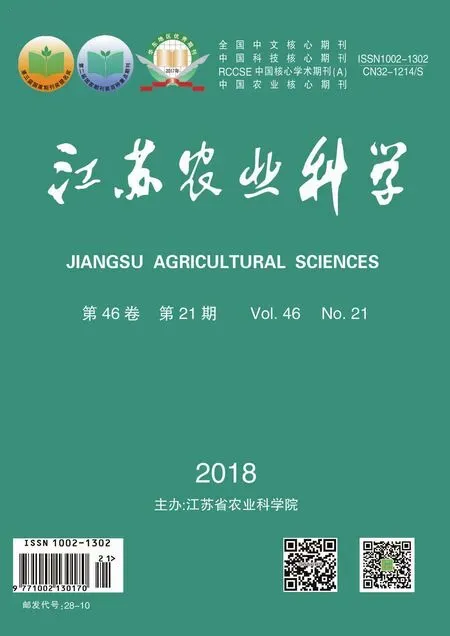中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評價
黃河東, 李 東
(1.賀州學院黨委辦公室,廣西賀州 542899; 2.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黑龍江哈爾濱 150006)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成為城市發展研究的重要問題,國內外學者從經濟學、生態學、環境學等不同學科領域進行了大量研究。從國外學者的研究看,Howard在《明日: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書中提出建設“田園城市”的設想,以應對當時城市面臨的貧困、擁擠和生活條件惡化等困境;Carson在《寂靜的春天》中揭露了工業化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問題,倡導工業發展應注重保護生態環境;Meadows的《增長的極限》和Goldsmith的《生命的藍圖》的發表,喚醒了人們對城鎮化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Pearce根據城市發展不同階段引起的資源環境問題,提出城市發展階段環境對策模型[1];Grossman等揭示了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質量呈倒“U”形的演變規律[2];Rork等提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關系的雙對數模型[3]。從國內學者的研究看,馬世駿等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開創了城市生態學的新理論[4];王如松認為,城市是在生態環境正負反饋因子交替作用下的成長過程,城市成長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反饋和限制性機理[5]。黃金川等認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交互耦合關系為一條雙指數曲線[6];喬標等認為,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各個方面與生態環境綜合協調、交互脅迫的耦合發展過程[7];劉耀彬分別對江蘇省及江西省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綜合測度分析[8-9]。王少劍等對京津冀地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10];張榮天等研究了中國省際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的空間演化規律[11];雷梅等研究了貴州少數民族地區46個縣(市、區)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12]。綜上關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的研究成果看,以省域、市域或縣域為研究單元的居多,以城市群為研究單元的較少。城市群作為城鎮化發展的高級空間組織形式,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地理單元和重要驅動力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本試驗以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到的19個城市群為研究單元,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模型,對各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為實現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范圍的界定及城鎮化、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1 研究范圍
根據2016年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提到的19個城市群,并參考最新公布的長三角、山東半島、長江中游、中原、哈長、北部灣、成渝、黔中、滇中等9個城市群發展規劃以及相關研究成果[13-15,10],確定各城市群的空間范圍(表1)。
1.2 評價指標體系
1.2.1 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 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包括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聚集、農業經濟向非農經濟的轉變、城鎮用地規模的擴張、農村生活方式向城鎮生活方式的轉變等4個方面的內容。因此,可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等4個方面對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評價。評價指標的選取遵循可比性、可獲得性、合理性等原則,共12項,全部為正向指標(表2)。
1.2.2 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生態環境是與人的生存發展直接相關的環境,主要包括大氣、水、土壤、礦產、動植物等要素。PSR(pressure-state-response)即“壓力-狀態-響應”模型,由Friend等學者于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于20世紀80年代末共同發展起來,是常用于研究生態環境問題的框架指標體系[16]。根據PSR模型,本研究將生態環境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分為壓力、狀態、響應3個層次共9項指標,指標選取遵循可比性、可獲得性、客觀性等原則,其中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業煙(粉)塵排放量等3項指標為逆向指標,其余為正向指標(表3)。

表1 中國19個城市群及其空間范圍

表2 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表3 生態環境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 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分析
2.1 數據來源及標準化處理
本研究各城市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6年);由于少部分城市的數據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沒有收集,所以數據采集于這些城市所在省份的統計年鑒或政府官網;對于極少數確實采集不到的城市數據,則用該城市所在省份數據的均值替代。各城市群相關指標的數據由其所包含城市的數據經計算所得。
考慮到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的單位不一致,不能統一計算,利用極差標準化公式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對于正向指標,公式為uij=xij=min(xij)/max(xij)-min(xij),對于逆向指標,公式為uij=max(xij)-xij/max(xij)-min(xij),其中,uij表示指標標準化值,取值在[0,1]范圍內;xij表示指標原始值;max(xij)表示指標最大原始值;min(xij)表示指標最小原始值。
2.2 城鎮化及生態環境水平的計算
城鎮化及生態環境是2個相互獨立、相互影響的子系統,可用以下公式計算兩者的發展水平指數:
(1)

為避免主觀因素造成計算誤差,本研究使用客觀賦權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考慮到每種客觀賦權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為了降低使用單一賦權法所帶來的差異性,分別使用熵值法、變異系數法、CRITIC法等3種方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再計算3種權重的算術平均值,得到綜合權重作為各指標的最終權重λj(表2、表3)。
2.3 分析模型
2.3.1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2個或2個以上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現象。耦合度是系統間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程度。耦合度模型為[10]:
Cn={(U1,U2,…,Un/[∏(Ui+Uj)]}1/n。
(2)
系統間的耦合關系具有較大的相似性,耦合度模型也可以用于衡量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交互耦合關系,即:
C={(U1·U2)/[(U1+U2)×(U1+U2)]}1/2。
(3)
式中:C表示耦合度;U1,U2分別表示城鎮化、生態環境的發展水平指數,由模型可知,0≤C≤1,耦合度數值越大,表示協調發展狀態越好;反之,耦合度數值越小,表示協調發展狀態越差。根據耦合度大小,可以將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分為以下階段[6,12](表4)。

表4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各耦合階段關系特征
2.3.2 協調發展度模型 當2個系統均處于較低發展水平時,運用耦合度模型計算可能會得到這2個系統協調發展度較高的結果,造成與實際情況不符[17-18]。為解決上述問題,采用協調發展度模型計算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度,即:
(4)
式中:H表示協調發展度;C表示耦合度;I表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數,I=aU1+bU2,a、b為權數,分別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貢獻程度。考慮到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同等重要程度,確定權數a、b均取值0.5。由模型可知,I的取值也在[0,1]范圍內。根據協調發展度H的大小以及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的比較,可將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類型分為4種類型,12個子類型[19-20](表5)。

表5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類型
2.4 結果分析
運用公式(3)和公式(4)計算中國19個城市群2015年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及協調發展度,并對照相應的耦合協調發展類型(表6)。可見中國19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介于0.347~0.500之間,均處于耦合發展的拮抗階段。該階段城鎮化發展迅速,需要大量的資源、能源、資金作為支撐,生態環境逐漸被破壞,承載能力不斷下降;其中10個城市群的耦合度超過4.9,說明一半以上的城市群已經偏向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良性耦合的磨合階段。從整體上看,19個城市群的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依然處于較低的水平,離良好的耦合階段仍有一定差距,遠沒有達到高水平的耦合階段。

表6 2015年中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類型
從協調發展度及對應的協調發展類型看,中國19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度介于0.302~0.611之間,3個城市群達到高度協調耦合,占15.79%,13個城市群為中度協調耦合,占68.42%,3個城市群為低度協調耦合,占 15.79%,沒有城市群達到極度協調耦合。首先,高度協調耦合類型方面,珠三角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的差距小于0.1,達到高度協調耦合,是19個城市群中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最好的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雖然也屬于高度協調耦合類型,但生態環境發展滯后于城鎮化發展,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要更加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天山北坡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均達到較高的發展水平,在19個城市群中排名前五,雖然生態環境發展相對滯后,也屬于高度協調耦合類型。原因可能在于城鎮化及生態環境發展水平的評價大多選用了人均指標,天山北坡城市群人口規模相對較小,2015年末人口僅為525萬人,與長三角1.3億的人口規模不能相提并論,盡管總量指標值不高,但人均指標值較高。事實上,天山北坡城市群整體經濟實力仍處于較低水平,今后既要加快城鎮化的發展,也要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3個高度協調耦合類型的城市群中,東部地區占2個,說明東部地區城市群城鎮化及生態環境均發展較成熟,兩者的協調耦合發展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其次,中度協調耦合類型方面,京津冀、長江中游、山西中部、關中平原、寧夏沿黃等5個城市群城鎮化及生態環境發展水平差距小于0.1,發展較均衡,達到中度協調耦合,在今后的發展中要保持這樣的均衡發展,爭取達到更高水平的協調耦合類型。海峽西岸、山東半島、中原、哈長、滇中、蘭西等6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為中度協調耦合-城鎮化滯后型,城鎮化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和提升空間,今后的發展應在生態環境的承載力范圍內,著力提高城鎮化水平。遼中南、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為中度協調耦合-生態環境滯后型,城鎮化發展超過了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在今后的發展中應更加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最后,低度協調耦合類型方面,北部灣、成渝、黔中等3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屬于低度協調耦合-城鎮化受阻類型,3個城市群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在19個城市群中排名最后3位,處于最低水平,城鎮化發展對生態環境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遠未達到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極限。在今后的發展中最主要的任務是利用好生態環境的優勢,加快城鎮化發展進程,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提高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水平。
3 結論與討論
本試驗以中國19個城市群為研究單元,通過建立評價指標體系以及耦合協調模型對2015年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19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介于0.347~0.500之間,均處于耦合發展的拮抗階段,仍然處于較低的協調發展水平;19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包括高度、中度、低度3種耦合協調發展類型,分別占15.79%、68.42%、15.79%,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19個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地區差異明顯,表現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該結論既可以為政府制定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參考依據,也可以為城市群各城市間加強合作,共同促進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決策指導。因數據獲取的限制,本研究在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方面還可以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在提高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的對策建議方面還可以更詳細、更具體,這有待今后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