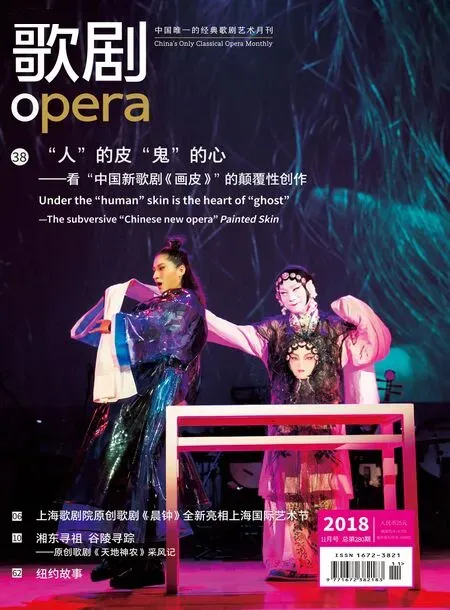青青太白山 皚皚太白雪
——觀原創民族歌劇《太白雪》
文:景作人 圖:黃定超
10月8日,我赴西安觀看了甘肅省歌劇院青年導演張程在陜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以下簡稱陜西師大音樂學院)執導的原創歌劇《太白雪》。來到陜西師大音樂學院后,我了解到這部歌劇的動力源自一批青年教師,他們都是陜西師大音樂學院近年來招募的有才青年。這些年輕教師有熱情、有實力、有經驗,更有一股無畏的闖勁兒。坦率地講,這樣大膽而又艱難的藝術實踐,無疑是一個令人欽佩和稱贊的壯舉。
歌劇《太白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抗戰時期,中共地下黨員馮竹卿與名醫馬明仁在太白山下相知相愛,他們在共產黨員程星的感化下,積極投身抗戰,與特務斗爭周旋,為陜北抗日武裝輸送藥品。馮竹卿為了民族大義壯烈犧牲,而馬明仁則以博大的胸懷和行醫準則,體現出中華兒女堅貞不屈,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這部歌劇的創演班底都是一批年輕教師。編劇尹相濤(外請),作曲侯玥彤、鞠波(外請),導演張程(外請),指揮嚴松波(外請),舞美周嘉宇(外請),燈光繆偉(外請),主演則有郝亮亮、侯玥彤、雷倩、王莉娜(外請)、馬俊、薛晨、鄒赫(外請)、董密、李騰(外請)等。合唱是陜西師大終南合唱團,樂團是陜西歌舞劇院有限公司交響樂團。
《太白雪》是一部民族性突出且中西結合的歌劇。說它民族性突出,是因為無論在戲劇上還是音樂上,它都有著深刻的民族乃至民俗烙印;說它中西結合,是因為它很好地借助了西洋正歌劇的形式,將具有民族風格的音樂及戲劇手法融入其中,呈現出了新穎的藝術效果。
歌劇《太白雪》的劇本生動,編劇尹相濤在創作上很大膽,他通過故事原型的啟發,很好地領悟了該劇的中心思想。在具體手法上,他合理地“組織”了全劇的戲劇結構,并以“鐘鼓樓前”“太白山下”“含光路上”“秦嶺山里”這四個地域為節點,構成了整部歌劇的四幕劃分,同時在這個“四幕”的框架中,展開了全劇的情節發展和戲劇進行。
《太白雪》在戲劇上的成功之處得益于原故事的真實。馬明仁出生于杏林之家,世代行醫,馬氏家族的醫學傳承現已是國家級“非遺”項目。抗戰時期,馬明仁一家深明大義,冒著生命危險,歷經艱難困苦,為抗日戰士輸送藥品,大大支援了抗戰事業,為祖國、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績。這個真實的故事為編劇打開了創作思路,他采用了開放式結構,以塑造人物為重點,借助電影的蒙太奇手法,使戲劇的展開得到了另類的“修飾”,起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

《太白雪》的人物塑造很有特點,劇中每一個角色都很吸引人(即使是次要的陪襯角色)。人們在劇中看到,無論是馬明仁、馮竹卿(馬明仁的妻子,國民黨師長的千金,中共地下黨員)、程星,還是小柱子、桃兒姐、高云達,每個人的個性都展示得很突出,且在關鍵時刻能夠發揮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太白雪》的戲劇優勢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那就是在情節上能夠做到環環相扣,在戲劇上能夠做到層層發展。人們看到,從第一幕“鐘鼓樓前”開始,一直到第四幕“秦嶺山里”為止,歌劇的情節展示與戲劇發展都是圍繞著道德線和愛情線這兩個方面進行的,而劇中主要人物馬明仁、馮竹卿,則是通過道德線而“搭”上愛情線的。他們結為夫妻后,又反過來通過愛情線來促進道德線的發展。如此一來,兩條情節主線便在劇中交替變化,產生了環環相扣和層層發展的效果,從而反襯與烘托了民族團結與民族勝利的中心主題。

歌劇《太白雪》的音樂寫作很有創意。作曲家侯玥彤(陜西師大音樂學院教師)與鞠波都是“80后”,都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值得一提的是,二人所學的第一專業都是聲樂,且有一定實踐經驗,之后又都經過專業作曲訓練。近年來,二人都創作過一些有價值、有影響的聲器樂作品。
2.4.2 多因素分析 以孕期有無UI為因變量(0=是,1=否),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相關因素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以下因素為孕期UI發生的危險因素:順產、BMI為24.0~ kg/m2、孕周≥28周、糖尿病、便秘為孕期UI的危險因素,見表5。
《太白雪》是他們合作的第一部民族歌劇,亦是他們二人在創作實踐方面的一次嘗試。8日晚我在現場觀看這部歌劇時,感受到了以下幾點音樂方面的突出特點。
一、音樂旋律美,可聽性強,且具有民族性。
《太白雪》的音樂是以民族性為基礎的,人們從第一幕中就可以聽出,歌劇中的許多主要唱段(包括合唱段落),都時隱時現地出現了地方戲曲因素(如秦腔)和民歌因素。
《太白雪》中的大多數詠嘆調都是帶有旋律性的,音調優美順耳,十分流暢,且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如第一幕中馬明仁的詠嘆調《心中的理想之花》,第三幕中程星被捕前的詠嘆調《有一種信仰》,第四幕中馮竹卿臨終前的詠嘆調《雪浸丹融》等,都是能夠觸及人們心靈的唱段,而主題歌《太白雪》則更是清純潔凈、深情滿滿。這首歌在音調和語調的結合上非常合轍押韻,風格上亦帶有自然的說唱氣息,顯得十分親切。
《太白雪》的合唱段落也寫得很有特色,唱段雖然不多,但卻并非普通的群眾合唱(晚會合唱)。像主題合唱《太白雪》,第四幕中的合唱《黑暗過去就是黎明》等,都是“有機性”的唱段,這些唱段從結構安排和技術運用(如轉調手法、復調技術等)方面來看具有歌劇化的特征,它們適當地出現在歌劇中,為情緒的烘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音樂“語氣感”突出,宣敘調“音律化”鮮明。
《太白雪》的音樂聽起來很通俗,一方面是因為它非常接近民間戲曲和民歌旋律,另一方面是因為它有著突出的“語氣感”。而這種語氣感就是作曲家所說的“詞由心中生,曲從詞中來”。《太白雪》雖是一部以民族風格為主的歌劇,但從形式上看,它無疑采用了西洋正歌劇的體裁。首演時人們看到,這部歌劇的道白不多(只占大概五分之一),大量的對話部分都采用了西方歌劇的宣敘調手法。然而,《太白雪》中的宣敘調卻寫得很順暢,它既沒有出現搞笑式的洋腔洋調,也沒有出現難受的“倒字”現象,反而使音樂得以連貫、戲劇得以延續、語調得以歸韻。
三、音樂的結構合理,樂隊部分色彩豐富。
《太白雪》是兩位青年作曲家的共同作品,由于他們兩人都是聲樂專業出身,故而對音樂中的聲樂特性要求甚嚴,對聲樂部分的結構安排、技巧運用、音效表現亦有著過細的研究。我看過這部歌劇后有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該劇中的唱段寫得很“聲樂化”,這些唱段在結構的安排、音樂的掌握、高音的處理等方面,都做到了適度和自然,沒有不合理的“強制聲音”(突兀的高音、連續的“吊”音等)出現。歌劇《太白雪》的主創人員雖大多數都是陜西師大音樂學院的教師,但導演卻是甘肅歌劇院的青年導演張程。執導這部歌劇,張程花費了很大心血,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不可想象的決心和毅力,完成了一個不可想象的任務(原本首演時采用音樂會形式,臨時改為實景歌劇形式)。張程在最短的時間里完成了他的一切舞臺調度方案,進行了很多角色演員“對手戲”的情節安排與情緒調動。實踐證明,這些調動和安排均在劇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從而為歌劇中心思想的表現打下了表演上的基礎。
歌劇《太白雪》的演員陣容是出色的。飾演馬明仁的青年演員郝亮亮,師從于著名歌唱家晁浩建、王宏偉,現為陜西師大音樂學院青年教師,碩士生導師,是一位頗有實踐經驗的年輕歌唱家。當晚郝亮亮的演唱可謂技驚四座,他的聲音明亮、清澈、富有穿透力,劇中數段重要的詠嘆調,他都演唱得充分、流暢,游刃自如。如第一幕中馬明仁首次亮相時的詠嘆調《心中的理想之花》,郝亮亮演唱得深情滿滿,充滿著內心的躊躇滿志和浪漫展望。曲中的高音,郝亮亮完成得很“漂亮”,應該說,當晚他一亮相,就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聲音上的震撼感。
飾演馮竹卿的雷倩也是陜西師大音樂學院的青年教師,碩士生導師,她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自2014年畢業后,先后在國內多次聲樂比賽中獲獎。雷倩還有一個身份,她是馬明仁的孫媳,屬于馬氏家族中的一員。馮竹卿在劇中是一個帶有特殊性的角色,作為女主角,她是國民黨師長的千金,留法歸來的闊小姐,卻又身為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因而身份十分復雜。馮竹卿在革命斗爭中與馬明仁相愛結婚,又多了一種戀人與妻子的身份,因此說,這個角色是整部歌劇中最具變化和“層次感”的人物。雷倩在演出時唱演俱佳,其內在氣質和外在做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飾演程星的王莉娜是西安音樂學院聲樂教師,當晚她的唱演亦給人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王莉娜的演唱聲音清澈,有亮度、有味道、有感覺,表演上亦有著很好的氣質。劇中程星被捕前演唱的詠嘆調《有一種信仰》非常感人,讓人深深地回味。
飾演高云達的馬俊是畢業于俄羅斯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男中音歌唱家,現為陜西師大音樂學院青年教師,碩士生導師。他飾演的角色高云達是劇中唯一一個反派人物,這個人物心思毒辣,思想反動,常有居心叵測之舉。馬俊當晚的唱演很有控制力,對于人物的性格把控分寸準確。
其他演員在演出中也都有著不錯的表現,飾演小柱子的薛晨和飾演桃兒姐的鄒赫表現突出,二人的角色都很有“戲”,他們的唱段亦有著連貫和串場的作用。
陜西師大終南合唱團在舞臺上的表現令人稱道,他們雖非專業人士,但在演唱時做到了專心致志,其整體的聲音效果令人刮目。
陜西歌舞劇院有限公司交響樂團在指揮家嚴松波的指揮下,演奏中基本做到了聲音嚴謹,層次分明。他們在現場與舞臺上演員們的配合,極大地促進了整部歌劇的順利進行,為歌劇的成功首演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歌劇《太白雪》自創作至今已經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就一部歌劇精品的形成來說,在首演后找出問題、發現不足、盡快修改,對于創作者來說是十分必要的。為此我開誠布公地談談對這部新作所存在的問題的看法。
第一,一部優秀的歌劇,從劇本上看,一定要擁有嚴謹的情節邏輯和戲劇邏輯,要有“環環相扣”和“高潮迭起”的緊湊劇情,否則歌劇中“戲”的成分就難有真實感,也就不能夠全方位地打動觀眾。


歌劇《太白雪》本身是依靠真實故事寫成的,按理說在情節邏輯和戲劇邏輯上應該是順暢的。然而現在的劇本在某些環節上卻出現了不太“通順”的現象,一些不合理的情節設計,最終導致了全劇戲劇效果的欠缺(如第一幕“接頭”時的情節設計)。
第二,劇本中還是沒有為音樂做足表現上的鋪墊,很多地方應該順其自然地為音樂“搭造”出平臺,以便歌唱家用音樂來盡情表現情節與戲劇。例如,第四幕馬馮二人在逃避特務追趕時,馮竹卿為了掩護馬明仁送藥,毅然決定走另一條路將敵人引開,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來換取丈夫的生命和正義之舉。此處是一對相愛夫妻的生死之別,情節已將感情的“洪流”推向了頂峰,按照歌劇的表現慣例,此處作曲家應該安排一段深情的二重唱來盡訴角色間的內心情感。遺憾的是,劇作者卻并沒有在此給作曲家留下表現的空間,而是采用話劇式的一般手法匆匆話別,由此給觀眾的心中留下了一絲情感與音樂方面的雙重缺憾。
第三,劇作家在創作劇本時,采用了很多姊妹藝術的表現手法,這原本是件有意義的好事。但若采用不當或采用過量,就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太白雪》一劇中采用了很多電影藝術思維,在舞臺上展示了蒙太奇式的手法,用以反襯和對接情節。然而,這樣的手法固然新穎,但其最大的缺點是分離了歌劇特有的音樂整體性,當這些手法被過多采用時,無論在音樂的銜接還是音響的共鳴上,都對歌劇的整體性產生了不利影響。
第四,《太白雪》的音樂寫得很有味道,很接地氣,一些主要唱段大膽吸收了中國抒情歌曲和民歌的雙重優點,為詠嘆調的寫作增加了鮮活的中國因素。然而,綜觀全劇的音樂(以唱段為主),大部分詠嘆調還帶有些許“歌曲化”的痕跡,而“歌劇化”(即富有動力感的“有機性”音樂)在唱段中的體現仍然很不夠。如此一來,歌劇的音樂就很容易陷于“停滯”,繼而影響了戲劇沖突和戲劇高潮的延續與推進。另外,本部歌劇中的重唱段落略顯薄弱,音樂中的角色個性沒有盡顯出來。
第五,《太白雪》的樂隊配器依然偏重,銅管及打擊樂的使用還應略加控制,而木管和弦樂的使用還應再細膩些、講究些,力爭使其與演員的唱段融為一體。
第六,導演在執導方面還應更加放開手腳,寫意手法的運用還要更揮灑大膽,既然用了,就要用徹底,用到位,不要既想用又畏縮,最終成了“四不像”。
以上是我觀看歌劇《太白雪》的感受與評論。《太白雪》是一部滿懷正能量的作品,它的創演有著很大的意義。第一,通過這部歌劇,使我們能夠緬懷先烈,伸張民族正義。第二,通過這部歌劇,使我們能夠宣傳和傳承我們的民族醫學,為百年傳承的國家非遺項目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