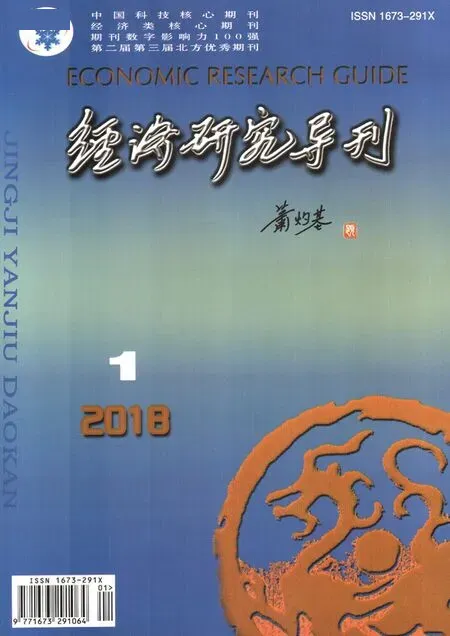GDP增速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是好事
王勤謨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離退休干部局,北京 100821)
引言
筆者在《從一些實際現象探討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一文中曾提出:“如果以工業化程度為標準,可以把國家分成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基本實現階段、工業化起飛階段三種類型,在政治穩定的國家中,在經濟周期景氣時期,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發展速度大體分別為:3%、6%、9%各加減1%。”[1]也就是說,GDP是隨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而逐步降低的。但這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說法,而且沒有分析其原因。當時,我國GDP的增長速度是9%加減1%左右,現在已下降到6%加減1%左右。會不會下降到現在經濟發達國家的3%加減1%左右?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而且是好事。當然,這是從長期的發展趨勢來看,因為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GDP的增長速度經常是波動的,甚至是大起大落的。因此,下面試做一些粗略的趨勢性的定性分析。
一、工業化起飛階段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
有人認為,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體量有關,體量小時,速度高;體量大了,增速不可避免要放緩,這也是一種客觀的分析。下面從另一角度,即經濟發展的因素上進行分析。
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從經濟本身來說,主要和要素投入(資本、勞動、技術)及其產出效率有關。工業化起飛階段,之所以能快速發展,主要和依靠要素大量的低成本投入,與低成本獲得技術進步有關。
具體到我國來說,主要得益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以及適逢和善于利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機遇。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國家之間的分工由產業和產品的分工進入產品中不同的經營環節,如研究、設計、制造、銷售、售后服務;不同的制造環節,如毛坯、零部件、裝配間分工。在這樣新的分工體系中,首先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把其中的低端部分,轉移到成本低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我國充分發揮低成本優勢,迅速發展為世界制造工廠。
具體地說,主要因素有:
1.充分發揮大量低成本的廉價勞動力的力量,主要是農民工。截至2016年底,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根據2013年《人民日報》報道,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2008年為1 340元,2009年為1 417元,2010年為1 690元,2011年為2 049元,2012年為2 290元。雖然每年都有增長,但總的來說還是很低的。當然,對農民工來說,仍高于其在農村的收入。
2.高積累率。2003—2014年的十二年間投資率由2003年的40.9%增長到48.3%,之后略有下降。近十二年來,投資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2.4%,平均拉動GDP增長5.4%。特別是,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我國于2008年推出4萬億元投資的強刺激措施,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87.6%,拉動GDP增長8.1%(孫曉華、李明珊,2016)。資金高度轉化為資本的主要途徑是:
(1)低消費率。高投資必然會反映在對消費的擠壓上。我國最終消費的比例一直處于下降中,到2005年,消費只占全部最終使用的39.7767%,而居民消費的份額更低,僅28.5570%。2007年后再也沒有超過50%(王文舉、向其鳳,2014)。
(2)高稅收。以稅收收入占GDP比重衡量的宏觀稅負水平,自1996年為9.75%之后持續上升,2012年之后,基本維持在18.8%左右的水平上;與此相應,自1996年起,中國稅收收入增長率持續高于同期的GDP增長率。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兩者的發展趨勢開始逐步接近(謝貞發,2016)。同時,在財政支出中用于經濟建設的比重高,用于社會文教的比重低。1978年,前者占總支出的64.08%,后者占13.1%,不過,發展的趨勢也是,前者逐步下降,后者逐步上升。如2006年,前者占總支出下降至26.56%,后者上升至26.83%。當然,由于經濟體制的改革,多種所有制并舉,經濟建設的投資,也由財政支出一個渠道,向財政支出、民間投資、外商投資等多種渠道并舉。
(3)舉債。如到2016年6月底,我國的總債務與GDP的比率已從2006年的155%上升到260%,債務總額從49萬億元上升到182萬億元。
(4)土地財政。自2003年以來,土地出讓的收入,成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以2011年為例,全國土地出讓收入3.1萬億元,占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60%。如果將土地出讓相關的其他稅費收入也納入土地財政的范疇,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更高(范子英,2015)。
(5)發行貨幣。截至2016年末,中國的M2和GDP分別為155萬億元和74萬億元人民幣,美國分別為13萬億美元和18萬億美元。中國的貨幣發行量是比較大的。貨幣發行量大的后果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作用相當于征稅。
3.低資源和能源價格,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也較低。如中國在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而同年中國的GDP為4.99萬億美元,是美國GDP14.42萬億元的34.6%。又如制造業中的基礎制造工藝,鑄造、鍛造、熱處理的噸能耗分別比國際先進高60%、70%和47%(余東華和孫婷,2017)。
4.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上,偏向放松環境保護。據有關研究結論,中國環境污染的經濟代價已經占到年均GDP的8%~15%(冉冉,2013)。又據2016年環境績效指數(EPI)顯示,中國戶外空氣質量位于最末的180位,室內空氣質量排名116位,綜合空氣質量指標排名倒數第二(179位)。空氣污染導致中國損失了10%的GDP(Hsu et al.,2016)。環境污染導致GDP的損失意味著節省了這筆治理污染的費用,降低了工廠的生產成本。
5.接受外商直接投資(FDI)。國家外匯管理局編制的中國投資頭寸表數據顯示,2016年9月中國直接投資負責凈頭寸已達29 61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國。
6.大力發展出口。利用低價格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和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等,出口額和貿易順差持續增加。舉一個典型例子,蘋果手機90%在中國加工,批發價為500美元的蘋果手機,蘋果公司獲得161美元,全球經銷商獲得160美元,零配件供應商獲得17.25美元,中國獲得6.5美元。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4.207億部,全球第一。這個例子說明,雖然中國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單位產品中所得少,但由于生產的總量大,總的所得也就很大。自1990年起,除1993年外,持續實現貿易順差。2014—2016年,出口額分別為14.39萬億元、14.12萬億元、13.85萬億元;貿易順差分別為2.35萬億元、3.68萬億元、3.35萬億元。
7.通過引進或模仿國外先進技術,提高技術水平。主要途徑:一是引進先進生產線和購買先進設備;二是吸引外資及其外溢的先進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前者始于1950年代蘇聯援助的156項建設,后者始于改革開放后。由于引進和模仿的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都是行之有效的成熟的技術,無需支出高昂的科研費用和冒失敗的風險,也是低成本。
8.國內市場大,生產規模大,工業門類齊全,城鎮化發展迅速,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并逐步完善。這些也都促進生產成本的降低,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9.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投資貿易協定,降低國際貿易成本。
綜上所述,在工業化起飛階段,我國老百姓勤勞節儉,以較高的積累投入經濟建設;盡力吸收國外資金;發展量大面廣的、在國內外大量銷售的低成本產品;在全國大力發展基礎設施、房地產、家電、汽車等支柱產業,實現高速增長。當然也難免會在某些方面有所犧牲。如,重資本、輕勞動,會拉大貧富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2008年達到最高為0.491,以后緩慢下降,2016年為0.465,仍高于0.4的警戒線);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會惡化環境;重引進和模仿先進技術、輕自主創新,會影響產業轉型升級;重粗放、輕集約,會過度消耗資源;重政府主導,輕市場機制,會影響效率等。但從總體來看,抓住了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這些犧牲畢竟處于次要地位。現在我國已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特別是在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就不能再繼續這種難以持久的不平衡的發展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或轉型期。
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GDP增速必然下降的因素
GDP高速增長的結果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一方面,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完善,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越來越合理,人的素質、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等越來越高,以及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等因素,都促進經濟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越來越提高。另一方面,也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使經濟的發展的目標由側重追求高速發展,轉向側重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水平、知識水平和修養水平,實現共同富裕和文明,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為人類做貢獻;同時,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動力——技術進步,也由側重引進、模仿,轉向側重科技的原始性自主創新。這些也是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的重要內涵,而這些因素都會促使GDP增速下降。具體表現為:
1.農村基本上已經沒有剩余勞動力可以向工業部門轉移,也就是發生了“劉易斯拐點”,從而推動工資成本上升。雖然中國是否已發生了“劉易斯拐點”,或在那年發生的,有不同意見,但這是遲早會發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月收入已達到3 274元,與2008年相比,無疑有了很大提高。其他職業收入的增速更高于農民工收入的增速。
2.生育率降低,人口增長趨緩,甚至減少,導致勞動力短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兒女生育和培養成本大幅提高,使生育意愿降低。與少子化同時存在的還有老齡化。如日本,截至2015年10月1日,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26.7%。意味著2.3個勞動力(15~64歲)要負擔一位老年人(謝澎,2017)。
3.消費率提高,積累率降低。現在經濟發達國家的消費率約為70%。消費率的提高也意味著消費水平升級,需要科技創新的支持。
4.新增積累資金中用于教育、醫療、扶貧、社會保障等支出的比重加大,用于經濟建設的比重相對減少。發達國家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20%~35%左右。經濟發達國家的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支出在5%~10%左右,社會服務的支出都在50%以上。當然,發達國家的建設主要依靠私人投資。中國發展趨勢也與此相同,如2013年中國財政資金中社會保障和福利的支出比2005年上升了18個百分點。
5.實現綠水青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為此,用于治理環境污染和保護環境費用的占比大幅提高。
6.企業留存利潤,由于加大了環境治理、勞工保護、公益事業等社會責任的支出,減少了再投資的比例,包括一些先富起來的人,設立以服務于社會公益事業的基金會等。
7.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期,資本投向產出效率高的東部地區的城市,拉大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進入“共同富裕”時期,實行均衡發展過程中,需要把資本投向產出效率較低的東北、中西部和鄉,降低了資本的產出率。
8.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抵消外商來華投資。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外匯管理局發布的數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2002—2015年,在流量上,從27億美元增加到1 456.7億美元;在存量上,從299億美元增加到10 978.6億美元。2015年,中國首次躍居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并且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外商來華投資,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王碧、肖河,2017)。
9.隨著低成本的優勢逐漸喪失,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和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等因素,進出口貿易的順差,可能趨于減少。
10.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中,效率較低的第三產業部門比重不斷提高,并超過效率較高的第二產業部門。
11.增加國防支出。國家的富和強是連在一起的。中國2010—2016年期間,國防費用占GDP的比重約在1.3%左右,不但與美國4%和俄羅斯4%~5%左右相比,而且和國際上通行標準相比,都存在增加的余地。
12.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本、勞動、技術的三因素中,越來越側重于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技術創新。經濟發達國家這一因素為70%以上(也有資料說是85%~90%)。事實是,發展中國家隨著技術水平逐漸和發達國家趨平,再要提高技術水平,也勢必要轉向原始性自主創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研究與發展(R&D)的費用占產值的比重,高技術產業在7%以上,中高技術產業2%~7%,中低技術產業0.5%~1%,低技術產業0.5%以下。然而科技創新雖然是第一生產力,但從成功率的角度看,卻是低效率的生產力。也就是科學研究、技術發明直至產業化,每個環節的支出都很大,但成功率卻很低。據斯坦福國際研究所統計,R&D項目在技術上能最終完成的約40%;而在技術上獲得成功的項目中約有45%沒能開發出產品;已經商品化的項目中,約有60%在經濟上不能獲利(周曉宏,2007)。如此算來,能在經濟上獲利的項目只有14.52%。又有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為454.4萬人,科技成果登記數為34 170項,平均每133人才有1項科技成果;按科技人員從事科技活動四十年計算,平均3名以上科技人員耗盡畢生精力才出1項科技成果,產出水平很低(董奮義,2009)。同時科技革命又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如有一個50—6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前25—30年為繁榮期,后25—30年微微衰退期。目前就處于這一輪長周期的下降波階段,即前一輪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科技革命導致的經濟繁榮已消退,新一輪以智能化等為主導的科技革命剛開始,尚未在經濟上大面積發揮作用。總之,科技創新,投入大,不確定性或風險性也大,效率低。其他方面的重大的原始性創新也是如此,如福特的流水作業大批量生產方式用了十二年時間,豐田的精益生產方式用了九年時間。
13.援助其他國家,增加國際公共產品支出。如2015年,聯合國規定發達國家每年至少將其GDP的0.7%用于對外援助。中國雖不是發達國家,也已開始對外援助。最近的例子,就是2017年5月14日,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宣布:“向絲路基金新增基金1 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 000億元人民幣。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 500億元和1 300億元等值人民幣貸款用于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
上述列舉的降低GDP增速的因數,并不完全,有些提法也可能不很確切。但就這些導致GDP增速降低的因素而論,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更側重于提高全體人民福祉水平,是好事。當然,在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階段時,需要注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關鍵還在于,經濟發展確實能惠及全體國民,縮小貧富差距,以及科技上確實能有自主性原始創新。而在進入高收入之后,隨著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又要注意防止養“懶人”。
以上,只是一個趨勢性的分析,未做定時、定量分析。而且定時、定量的分析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過,研究發展水平與GDP增速的關系,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只是拋磚引玉而已。
[1]王勤謨.從一些實際現象探討經濟與政治的關系[J].經濟研究導刊,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