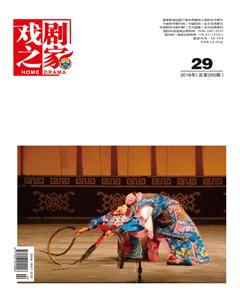吳經熊《道德經》英譯的文化資本重構
操萍
【摘 要】1939年,著名法學家吳經熊主動譯介并發表了老子的《道德經》。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國際知名的法學大師,吳經熊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活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借助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資本理論考察吳經熊英譯《道德經》活動,探討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譯者占有的文化資本對翻譯活動的推動和影響。
【關鍵詞】吳經熊;《道德經》;英譯;文化資本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29-0240-01
吳經熊是民國時期的法政要人,其經歷頗具傳奇色彩。這位蜚聲國際的法學大師曾被譽為“審判席上的所羅門王”,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突然撤離法律政治舞臺,轉而專注文化教育和精神修養,不僅潛心皈依天主教,還帶頭創辦了致力于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天下月刊》雜志,與一眾文化名流談經論典,譯介并發表了不少中國文學典籍。在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時期,吳經熊“跨界”英譯《道德經》的活動有著豐富內涵,值得深入研究。目前鮮有學者將吳經熊英譯《道德經》置于社會學范疇開展研究,從資本視角進行考察的更是不多。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將資本引入社會學研究,認為資本作為積累的勞動是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1]本文借助文化資本理論考察吳氏《道德經》英譯活動,探討文化資本對其翻譯活動的推動和影響。
一、文化資本與吳譯《道德經》的關聯
文化資本表現為內在和外在兩個層面。內在文化資本指個人在長期的文化教育過程中習得的“性情”,表現為語言能力、文化素養及審美情趣等,與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個人愛好乃至個人天資息息相關;外在文化資本涵蓋個人繼承或持有的財產形式的文化產品,如圖書、繪畫、器械以及個人的學術成就,如學術資格、著作、譯作等。[1] 吳經熊個人文化資本的積累和相應慣習的形成為他后期英譯《道德經》并出版發表奠定了穩固的內在基礎。
在《天下月刊》1940年3月第10卷第3期“雜錄”一文,吳經熊曾提及譯介《道德經》的緣由:偶然一日發現好友項美麗在文章中推崇他是“道教專家”,深感惶恐,儒家“仁、義、禮、信”的教養激勵他當夜即開譯老子的《道德經》 。[2]231然而,研究發現,吳經熊英譯《道德經》并非一時道義的沖動。吳氏1899年生于浙江寧波,家境殷實,天資聰慧,9歲開始學英文,對英語“一見即愛”,并因閱讀中國文學經典英譯本而對英語產生日益濃厚的興趣,“一開口說英語,人們就覺得我說的像本書。”[3]47青年時期留學美、法、德的經歷,更使他在多種語言文化間自由馳騁,“用英文思想,用中文感覺,有時也用法文唱歌,用德語開玩笑。”[3]48得天獨厚的教育和求學經歷為吳氏積累了扎實的語言和文化資本,為其后期英譯《道德經》提供了源動力。
此外,吳經熊6歲開始學習儒家經典,12歲曾有感于《論語》寫下“吾十有二而志于學”的勵志銘,青少年時期已熟諳孔孟老莊,“古圣哲言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成了心智結構的活組織。” [3]43孩童時期的儒道浸潤對其人生哲學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修養不僅僅來源于學堂,更形成于家庭,如他所言:“我母親的精神有助于我理解道家;我父親的精神有助于我欣賞儒家。”[3]48曾有神父評論吳氏在道德方面是孔夫子的門徒,卻更多地轉向老子來追求神秘真理。吳經熊本人認同這個說法,總結說:“也許我生性屬道家,木然的外表下隱藏著謹慎的智慧。”[3]192
綜合以上幾點審視附有大量注釋的《道德經》吳譯本不難發現:吳經熊的翻譯活動不能僅僅歸為單純的、目的性極強的翻譯工作,而是他本人文化資本積累的一種自然釋放。為便于西方讀者充分理解《道德經》關鍵詞之一“道”,吳經熊在注釋中引用西方不同時期哲學家、玄學家、文學家的文字進行闡釋,學識之廣令人望其項背。在1939年12月《天下月刊》登載的《道德經》英譯節選中,原文僅有21個字,但吳經熊所作注釋竟達千字,其中既有博古通今的佐證,又有中西對比的實例,語言學、文學、翻譯學多學科交叉運用。可以說,吳譯本《道德經》中注釋的魅力要遠超譯文本身,無論是譯者、文人,還是一般讀者,都會被譯者自由馳騁于中西文化的能力所折服。
二、結語
社會場域中,個體持有的文化資本可以通過持有者的文化能力、氣質、受教育程度及生活追求展現,當文化資本積累到一定的高度,可幫助持有者獲得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資本,表現為個體擁有的社會地位、頭銜以及關系。根據布迪厄的資本理論,吳氏占有的語言、文化、教育、審美等文化資本為其英譯《道德經》奠定了扎實的內在基礎。
參考文獻:
[1]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A].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tuart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46-58.
[2] John, C. H. Wu(吳經熊). 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 [J]. Tien Hsia Monthly, Vol. X, 1940(3):220-242.
[3] 吳經熊.超越東西方[M].周偉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